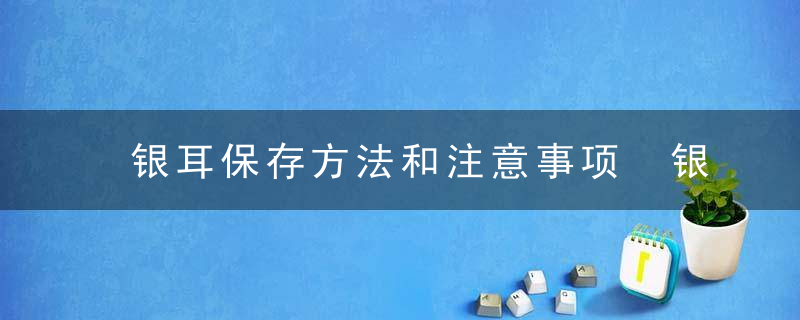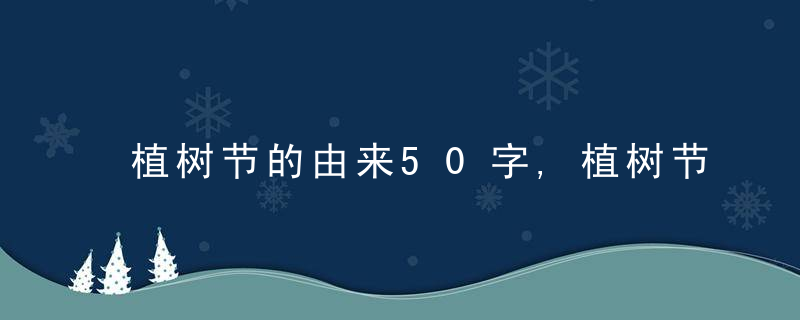从宋明时期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

从文化形态上来说,宋代是中国历史“近世”的开端。(注: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一文中详细论证了中国历史自宋代始向近世转变的事实,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1992年7月版,第一卷。)自宋代始,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农业形态向工商业形态转变的历史进程。明代中后期,这种进程开始加快。从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上探讨中国文化的转型,可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家庭经济活动既反映了文化的器物层面的情况,又反映了文化的行为层面的状态,同时也折射了文化的观念层面的律动。因此,对宋明时期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作一研究,可以更好地探明中国文化转型的历程和路向。
一
在中国古代家庭经济的经营管理中,家长居于中心地位,家长地位的变化,深刻反映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动向。宋明以前,家长在家庭经济的经营和管理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礼记·坊记》说:“家无二主。”荀子也称:“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注:《荀子·致仕》。)用礼制的形式,防止家庭其他成员对家长地位提出挑战。根据古代宗法制度,家长一般由年长的男人来担当。年长的男性家长不仅对财产有管理权,而且在礼制和法律上还规定其对财产有所有权,其他人不得私占擅用。
但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家中的事情一方面听命于家长,另一方面也贯彻协商的原则。赵鼎在其《家训笔录》中曾经指出:“诸位中以最长一人主管家事,及收支租课等事务,愿令己次人主管者听,须众议所同乃可。”到了明代,家长甚至不一定限定在父祖身上,也不限定在嫡子身上,诸子中有贤能者均可立为家长,如明广东南海人霍韬的《霍渭涯家训》规定:“凡立家长,惟视材贤,不拘年齿,若宗子贤即立宗子为家长,宗子不贤,别立家长,宗子只主祭祀。”这里显然已把家庭经济管理的权力与家庭象征性权力分开了,反映了自明代始,随着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和竞争的加剧,家庭经济管理的地位日益重要了。与此相适应,宋代以后家长的权力与义务紧密相联,对家长的要求也较以前更为严格。如宋代司马光指出:“凡为家长,必谨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注:宋·司马光:《涑水家仪》。)
然而,也应看到,宋明时期的家长地位并非一下子转变成适应商品经营要求的近世形态,传统的宗法色彩仍很鲜明,如宋代《郑氏规范》规定:“子孙倘有私置田业,私积货泉,事迹昭著,众得言之家长,家长率众告于祠堂,击鼓声罪而榜于壁,更邀其亲朋告与。所私即纳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论。”以此强化宗法家庭的统一性,消除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家庭内经济的不平衡性。这反映出中国文化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二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古代家庭一般都以重农观念为指导,注重农桑生产。由于农业是历代王朝立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历代政府都把农业视为立国之本,称之为“农本”,鼓励人们务农,甚至“驱之归农”。与此相反,历代政府把工商作为“末”,古代社会绝大多数的家庭,都将务农作为家产经营的主要方向,并将经商视为“不务正业”。古代许多学者也都强化了“重本抑末”的主题,并对务农中形成的封闭的家庭经济形态作了赞美,北齐颜之推指出:“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农,蔬果之蓄,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爱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卷1,《治家》。)宋明以后,经营农业仍是家庭投资主流,但已向多样化发展,不限于种植农桑等传统作物,也种植商品作物。
宋明社会经济转型之际,不少家庭尤其是城镇家庭,能够顺时之变,注重务工经商,使投资经营方向有了较大的变化,当时,家庭经营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往常人们重视的务农,在不少家庭的经营中降于次要地位,而往日被政府和社会所唾弃的经商末业,却上升到比较重要的高度,宋叶梦得尽管还抱着“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但已经把士农工商均作为家庭经营的四种正当职业:“治生不同:出作人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注:宋·叶梦得:《石林治生家训要略》。)当时,常住和暂住在北宋首都东京汴梁的市民,临街的住家家家户户开办店铺,不临街面的居民或外来人口,则在商业街上摆摊设点,在离皇城不远的地方,是政府各衙门,就在这里,竟出现了很多私人的商业店铺,出现了官民杂处,民生兴隆的状况。明代姚舜牧在其《药言》中,对士农工商四业的地位作了进一步的论定:“人须各务一职业,第一品格是读书,第一本等是务农,为此,为工为商,皆可以治生,可以定志,终身可免于祸患。”反映出家庭经营观念的过渡特征,既以农为本,又强调只要能谋生,农工商贾四者均可经营。赵南星则旗帜鲜明地把工商也视为本业,他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岂必仕进而后称贤乎?(注:明·赵南星:《赵志毅公文集》卷4,《寿仰西雷公七十序》。)当时安徽的徽州就是“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
中国古代家庭经营工商业多是从行商开始做起的。因为行商冒的风险大,相对来说利润较高。《初刻拍案惊奇》卷8记载了一位苏州百姓王生,为婶母杨氏养长大,他“商贾事体,是件伶俐。”杨氏对他说道:“我身边有的家资,并你父亲剩下的,尽勾营运。待我凑成千来两,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王生欣然道:“这个是我们本等。”后来王生被劫,只愿在近处经商,杨氏却说:“男子汉千里经商,怎说迷话!”同书卷29还讲述了一位“专一在湖广江西地方做生意”的浙江商人蒋生,追求马少卿的女儿,自报家门道:“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玷门风。”马少卿则说:“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反映人们对行商地位的看重。
宋明时的一般家庭等到积攒够一定的本钱,便开店设铺,经营各种工商业务,约略如下:第一,经营饮食业。古代家庭最普遍的是开设一些饭店酒楼,高级者如南宋杭州的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等,每楼各有“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奢华”。低级者如茶肆、饭馆、小酒店,饼店等。第二,经营旅馆业,北宋汴京州桥,“东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员商贾兵级,皆于此安泊。”(注:《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前州桥东街巷》。)大户人家也经营客店。赵普“广第宅,营邸店,奇民利”。(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条。)第三,经营零售业。《初刻拍案惊奇》卷8曾讲:景泰间,苏州府吴江县有个商民,复姓欧阳,“家道不富不贫,在门前开小小的一个杂货店铺,往来交易,(姐夫)陈大郎和小舅两人管理。他们翁婿、夫妻、郎舅之间,你敬我爱,做生意过日子。”是一幅和美的家庭营生图景。第四,经营租赁业。北宋首都开封不少的市民家庭都经营租赁业务,《东京梦华录》卷4《杂赁》载:“若凶事出殡,自上而下,凶肆各有体例,如方相、车辇、结络、彩帛,皆有定价,不须劳力,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以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南宋杭州的情况亦同:“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谓‘茶酒厨子’专任饮食请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虽广席盛设,亦可咄嗟办也。”(注: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6,《贷物》。)第五,经营典当资信业,明代家庭多开当铺或解铺,因其获利多而风险小。《恒言·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的高赞“年少惯走江湖,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开起两个解库,托有四个伙计掌管,自己只在家受用。”《恒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讲宋开封府“万万贯财主”张俊卿,此人“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质库。”第六,经营存诸业。南宋杭州“有慈元殿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于水次起造榻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货物,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便利。盖置塌房家,月月取索假赁者定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注:《梦梁录》卷19,《榻房》)第七,经营修理业。东京市民“其锢路、打铰、箍桶、修整动使、掌鞋、刷腰带、修幞头帽子、补角冠”(注:《东京梦华录》卷3,《诸色杂卖》)皆有人为。第八,经营手工业。唐以前,工商食官,工匠俱有匠籍,为官府所控制,没有经营自由,家庭手工业多以“女织”为主?规模难以扩大;宋明以后,尤其是明代实行“班匠银”以后,手工业者获得相对的自由,可以自主经营,并将所产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明人张瀚的祖先即“以机杼起”,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二十几张织机,“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注:明·张瀚:《松窗梦语》卷4,《商贾记》。)。据《万历野获编》卷28载,苏州的潘某也是“起机户织手”,终于富“至百万”。万历时吴小洲一家在南京开了一个糟房造酒,居然发展到“一二万金之产”。可见,自从宋代发生“商业革命”以后,中国古代家庭经营范围日趋广泛,传统农业社会的一统天下正在为工商业逐步瓦解。
三
唐以前,家庭财产的经营方针主要是节俭和量入为出。所谓“皆粗布之衣,脱粟之饭。”“中食而肉不足。”
而宋明以后,经营方针有了一定的变化,增加了以诚信为本的经营方针,这与古代家庭投资方向的变化有密切关系,宋明之前多经营土地,故较少与人打交道,宋明以后家庭经营范围扩大到工商业,与顾客打交道的机会日益增多,故强调以诚信相待,吸引顾客。宋代东京家庭经营的“正酒店”,对于顾客就以诚相待,一视同仁,“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注:《东京梦华录》卷5,《民俗》。)北宋京师东京樊楼旁有户人家开设的小茶肆,熙丰间有士人李氏入肆饮茶,遗金数十两于桌,后数年,李氏复过此肆,主人弄明其身份和核对遗物后,如数奉还:“集众再问李片数称两,李曰:计若干片若干两,主人开之,与李所言相符,即举以付李。”李氏欲分一半与之,主人坚辞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天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也。”此店主人还把历年“收得人所遗失之物,如伞、扇、衣服、器皿之属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以便送还。(注:明·陶宗仪辑:《说郛·摭青杂说》。)其诚信待客,实堪楷模。古代有些家庭对顾客的意见十分重视,若雇员在上菜时,“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注:《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对雇员故然严苛,但对顾客则是十分负责的。北宋大观末年,蔡京归浙右,乘舟过新开湖,叫来一艘正在打渔的小艇,“戏售鱼可二十髭,大小又勿齐。问其直,曰:‘三十金也。’”遂“使左右如数以金畀之”。不料没过多久,渔人又急趁大舟赶来,曰:“始货其鱼,约三十金。今乃多其一,用是来归尔。”蔡京笑而却之,渔人再三不可,“竟还钱而去”。(注: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以上发生在饮食、租赁、渔业、手工业等各个方面的诚信经营,反映了古代家庭经营活动中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经营方针。
在社会转型期,家庭经营方针不免出现泥沙俱下的状况,唯利是图就是宋明以后流行的一种不健康的经营思想。唯利是图的表现有很多,其一,偷税漏税,以权谋私。明弘治年间北京的“势要京官之家,或令弟侄家人买卖,或与宿商大贾结交,经过税务,全不投税。”(注:《明实录·孝宗实录》卷22。)他们还强取豪夺,“勋戚之间纵令家人开设店肆,邀截商人货物。”(注:《明实录·孝宗实录》卷117。)其二,色情相招,不顾风化。南宋时有的家庭经营“庵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注:《都城纪胜·酒肆》。)临安市西坊的潘节干、俞七郎几家开着茶坊,“楼上专安着妓女,名曰‘花茶坊’。”有的家主为了赚钱,竟让妻子卖淫。明小说讲,徽州岩子街边有一个小酒店主叫做李方哥,为了得到十五两银子,“开个兴头槽坊”,便令妻子陈氏与嫖客程朝奉淫乱。其三,刻剥掺假,偷梁换柱。明代小说《警世通言·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一当铺主“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又凡质物值钱者才足了年数,就假托变卖过了,不准赎取,如此刻剥贫户,以致肥饶”。其四,伪造假帐,狠心独吞。《二刻拍案惊奇》卷16《迟取券毛烈赖原钱,失还魂牙僧索剩命》讲宋淳熙年间。明州的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出本钱经营酒店,由林家管理,但林氏“连夜叫八个干仆,把簿籍尽情改造,数目字眼多换过了,反说是夏家透支了”,并贿赂州官,反告夏氏,从而独吞了合伙人的股份和资财。上述家庭经营中充斥的铜臭味和奸诈气,是原始积累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尽管已“人心不古”,但却开始了其“近世化”的历程。
四
经营手段是指家庭在经营方针指导下,采用的经营管理方法,在这方面,宋明以前与以后相差较大,反映出文化转型的某些轨迹。
手段之一,订立契约,完善手续。在传统伦理思想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中国人为人处事都讲诚信,一般借钱或办事都以诚相待,不打借条,不立契约,但宋明以后,由于家庭经营业务的扩大和商品意识的增强,按契约办事已成为习尚。如置买田地,宋代袁采就强调应该先找经纪人“牙家”,掌握对方将卖田产的详细情况,小心核对,看有无法律上的障碍:“索取阄书砧基,指出丘段围号,就问见佃人,有无界至交加,典卖重叠。次问其所亲,有无应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经分析、或系弃产,必问其初,应与不应受弃。如寡妇卑子执凭交易,必问其初,曾与不曾勘会。如系转典卖,则必问其元契。己未投印,有无诸般违碍,方可立契,如有寡妇幼子应押契人,必令人亲见其押字,如价贯年月、四至亩角,必即书填,应债负货物不可用,必支见钱,取钱必有处所,担钱人必有姓名,已成契后,必即投印。”(注:宋·袁采:《袁氏世范》卷3,《治家·田产宜早印契割产》。)如《二刻拍案惊奇》卷16讲,宋绍兴年间,庐州合江县赵氏村陈祈家因故打算先将田产典给本村富户毛烈,认为“产业交关,少不得立个文书,也要用着个中人才使得。”乃找大胜寺高公做中人,订了典卖赎还的契约,后陈祈欲赎回田产,将原价银两一一交明,毛烈昭数收了进去,却谎称原契在其妻手中,要求过一天再找还契约。陈祈要他“写一张收票与我。”毛烈以不会写字和“我与你甚交情”为由推辞。过后毛烈翻脸不认帐。陈祈一忿之气,告到县里,结果县吏丘大只摇头说:“说不去,许多银两交与他,岂有没个执照的理?”毛烈则“把交银的事一口赖定,陈祈其实一些执照也拿不出。”知县也说:“当官只凭文券;既没文券,把甚第做凭据断你?分明是一划混赖。”下令杖了陈祈二十个竹篦。小说之意,在于提醒人们重视契约合同。
手段之二,注意宣传,重视推销。唐以前,家庭经济仅仅是男耕和妇织,产品多是自给自足,不存在扩大销售问题,也就不太重视产品的宣传;宋明以后,家庭经营工商业日益增多,故经营手段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清明上河图》可见,张伞卖饮料的,悬挂着“饮子”的小布招牌;大酒店门口结着高高的彩旗,彩旗上标着“新酒”二字,门前写着“天美之禄”四字,均注重广告宣传。北宋“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注:《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据《梦梁录》卷16《茶肆》所载:“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向绍兴年间,卖梅花酒之肆,以鼓乐吹《梅花引》曲破卖之,用银盂杓盏子,亦如酒肆论一角二角。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于其上,装饰店面,敲打响盏歌卖”。均重视经营环境。节令促销是当时各家各户采用的常法。如宋东京“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画竿,醉仙锦斾”;“九月重阳,都下赏菊……酒家皆以菊花缚成洞户。”古人还重视开业优惠,如宋宣和间,丰乐楼改修后,“初开数日,每先到者赏金旗。”(注:《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主动推销是宋代小本经营者的促销手段,如“有卖药或果实萝葡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注:《东京梦华录》卷2,《饮食果子》。)
手段之三,聘请专才,协助经营。唐以前,富家大户多雇佣农民为其耕田地,有些农民人身依附关系很重;而宋明时期,家庭经营中出现了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上门协助经营的情况,而且其人身关系是自由的。如明小说《初刻拍案惊奇》卷35讲,宋时贾仁发财后“请着一个老学究,叫做陈德甫,在家里处馆,那馆不是教学的馆,无过在解铺里上些帐目,管些收钱举债的勾当。”显然其人身关系是自由的。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个“运用经济力量的地方甚多”的朝代,在民间亦复如此。宋明家庭在经营手段上的发展,即一例证。
中国自宋代起开始了其“近世化”的历程,同时也开始了其文化转型的进程,家庭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的新教伦理中勤奋、俭朴等观念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虽没有新教,但却不乏勤奋和俭朴精神,如《东京梦华录》中,就记载着东京市民起早贪黑在早市和夜市上贩货的勤劳状况。中国人一直强调“勤俭为成家之本”,反对“侈靡骄奢,博奕饮酒、宴安懒惰”,深知“若人心一懒,百骸俱怠,日就荒淫而万事废矣”(注:清·张师载:《课子随笔》卷2,《何氏家规》。)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成近代资本主义,原因固然很多,但政治制度未能配套发展,一直是困挠中国近现代化过程的主要问题。家庭经济向资本企业发展,未有法律上的保障,故不少家庭“以末致富,用本守之”,费正清等指出,中国自宋代“商业革命”以后一直固守着传统不变,有一个重要原因乃是“社会领导阶层效忠于传统,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必须与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所谓丰富的经验模式相适应”,所以他们对前所罕见的民间日益壮大的家庭商品经济无所适从,除了混水摸鱼地捞一把,加重其艰辛困苦外,并没有相应对策使之健康发展,致使古代的家庭经济未能在原始积累基础上,正常地发展成具有近现代性质的企业,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在近代门槛前徘徊,中国文化的转型也因此历尽坎坷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