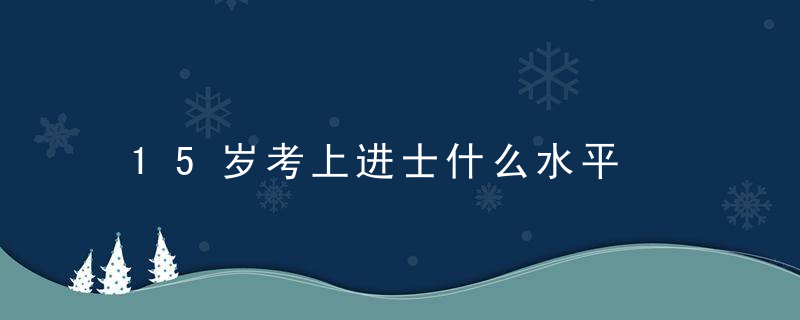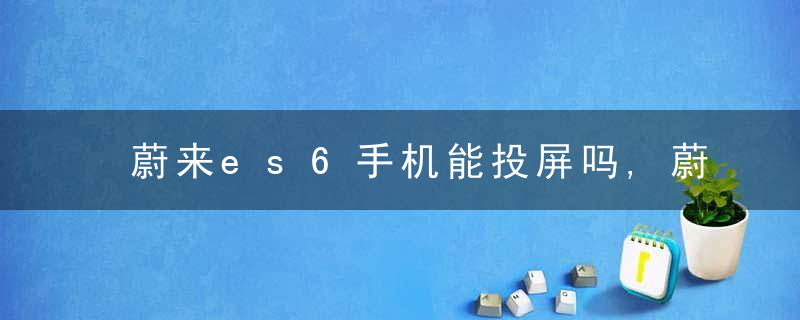晚清新政与中国知识界知识体系的转换

自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知识体系在短短一百多年里已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今天在校的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与晚清新教育兴起前的传统教育相比,已截然不同。一百多年来知识体系的变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值得学人进行深入的研究。而这一变革的真正发端,当数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期间。
一、传统中国知识人知识体系的特点
何谓传统中国人的知识体系?这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它与一些学者所讨论的学术体系、学术分科有一定的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简单来说,知识体系即一般读书人应该学习和具备哪些知识,属于较低的层次,而学术分科却是进入研究层次才遇到的问题。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应该是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现代科学成长起来之后逐渐定型的。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自科举制度定型以后,读书人所学内容受到科举制的极大影响,其知识体系基本上囿于科举所规定的儒家经典以内。阅读面宽的,才会涉及先秦诸子学说和历代史书等内容。换句话说,当时学习知识就是学习传统经典。一般而言,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技术和许多专门之学是被排斥在外的,在他们看来那只是工匠们做的事情。学子们入门的学习也好,进入研究程度的也好,都大体如此。阅读面窄到极端的,则如梁启超所抨击的:“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更寡矣。”(《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科举题名之后,有些人始用心治学,阅读研究的范围自然大些,但即便如此,其知识体系仍大体不会超出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和历史之类。
我们也可以从读书人的自我认定来思考传统知识体系的范围。清人姚鼐曾以义理、考据、词章为治学的门类,并认为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为先秦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考据为专门之学,但考的也主要是古代典籍;词章则不是专门学问,而是语文能力。实际上,当时人只要具备上述三者之一,就可以被视为读书人。学习桐城文体的曾国藩也曾在给诸弟的信中说:“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曾国藩家书》)
清嘉庆、道光年间,经世思潮渐兴,至咸丰、同治年间而盛。所谓经世致用,主要就是研求与治理国家或与政务活动相关的知识。曾国藩后来也把经济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他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求阙斋日记》)。这些可以代表经世的学问。在曾国藩任京官的十年中,他对这些事务都下过功夫研究。黎庶昌在《曾国藩年谱》中说:“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这些学问,包括了我们今天说的官制、财经、军事、司法、地理、水利等多方面内容,多与政务有关,其中地舆、河渠近于今天的自然科学,虽然范围比义理、考据、词章宽得多,但它们受到重视其实还是因为与政务有关。
我们观察传统图书分类,也可大略了解国人对知识的看法。清代已经定型的经史子集的分类,说明经占最主要的地位,史主要是经世者研习的,其他所有学科,都放在子和集之内。
总之,传统的读书人虽各有偏好,但基本以研读儒家经典为主,兼及诸子百家学问,这也就是传统的知识体系。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除了传统天文、医学等个别学科外,基本是文科方面的知识。清代杰出建筑家如主持清宫建筑的样式雷,在今天或许可以算是资深院士,可在当时,侧身士林者绝不会将他视为读书人,样式雷也不会以读书人自居。相反,如果某人饱读诗书,或进一步有著述传世,即便没有科举功名,也足够获得士大夫的尊重,因为他们具备了传统知识,能够与科举士人一起论道论政。
二、新政与新知识体系地位的上升
事实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尤其是1860年代洋务运动以后,新知识已经逐渐楔入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从李鸿章到张之洞所办的新学堂,就以学军事技术和各国语言为主。这种情况在传统士大夫身上也有所反映,曾国藩一度不让他的儿子学八股,而支持其研习数学,便反映了时代变化、知识体系变革的信息。不过,直到十九世纪末,新知识还远不能与传统知识的强势相抗衡。孙中山在夏威夷接受启蒙教育,后来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尽管他学有专长,且手不释卷,但仍被那些饱读诗书的传统士大夫视为没有文化,就说明了这种情况。
1901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举办新教育,是新政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按规定,新学堂里开设了大量的新学课程,虽然仍然规定了必须的读经课程,但是学子们研习的重点,显然已不是儒家经典,而是声光电化、西方政治和历史地理。1904年初,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使新学制度化。按“癸卯学制”的规定,小学课程设置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图画、手工等,中学堂的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虽然读经讲经仍作为重要课程,但已只是统治者控制思想的消极工具,不再是也不可能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了。至于癸卯学制规定的大学分科,有经学、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八科,经学只是其中之一,失去了以前的显赫地位。
1904年,一位官员在日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其害终中于国家,其流毒且甚于祖龙焚坑之祸。南皮总督(指张之洞——引者)真吾道罪人也。”(《恽毓鼎日记》)恽毓鼎担心的,就是传统学问日益退化、新学问已占据主体地位的情况。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孔孟道统和讲求空泛道德修养的宋明理学,无以抵御洋枪大炮,无以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
三、废科举的巨大影响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为止。1905年,由于日俄战争的刺激,清政府在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官员的要求下,宣布废除科举制。从此以后,除了特别的研究外,读书人不需要再读那些科举制必定要考的儒家经典了,因此,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知识体系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根支柱也倒塌了。
实际状况也确实如此。废科举仅仅两年,这种影响便已显现。1907年有位叫许珏的候补道向清廷上了一道条陈,说“学堂奏定章程,非不重四书五经,然大概多视为具文。盖办学之人既多尚新异,而教科太形糅杂,势亦相妨。上年在里,见十龄外幼童,入学堂已四五年,尚未读四书者,可为叹息”。这位候补官员要求“今宜申明奏定章程,凡十龄以前,必诵读孝经、四书;十龄以外,仿从前专经之例,许专读一经”(《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669页)。显然,这位官员是位较为守旧的人士,他的上书道出了传统经典和传统知识命运变化的实情。
这一时期,习新学的读书人的处境也大大改善。不用说没有任何科举功名的孙中山被拥戴为同盟会的领袖,即便在清政府方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01年以前,能够进入政权高层的读书人只能是传统型的、经过科举考试的,新政以后,掌握新学的读书人开始进入政府。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就做到巡抚、尚书;留学英国的法律专家伍廷芳做到侍郎、修订法律大臣;更有大量的留日学生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在一些新部门发挥着不小的影响,有的甚至在几个部兼职。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识。
及至民国建立,教育总长蔡元培认为“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明令废止小学校读经课程,可以说给旧知识体系画上了一个句号。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在许多新知识学科具备了自我研究和发展的能力,如地质、化学、物理等学科,且涌现了出色的科学家,新知识体系最终完全替代了旧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