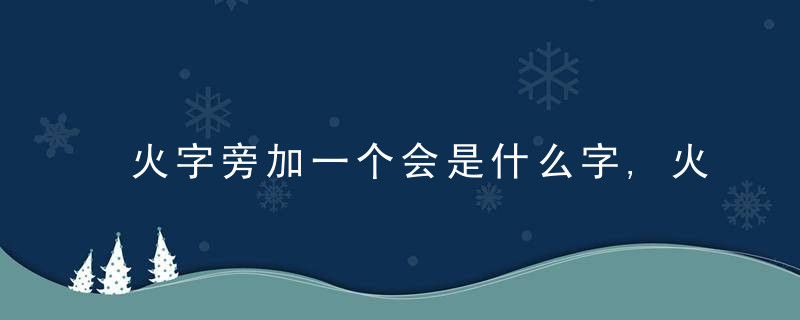《道德经》的“忍”法和“减”法(七、八)

(七)
佛家认为人的福报是修来的,认为布施是修行的最高法门,这是至理。修行说到底是给别人做“加法”、给自己做“减法”,这就是布施。
有的人布施,他不是源于慈悲,他给别人做“加”法,同时也要给自己做“加”法。他给自己“加”什么呢?他要别人赞扬他、宣传他,这就不是真正布施,而是做交易,即花钱做广告了。有天看到一个电视节目,电视上的观众都在为那个坐在台上的布施者打抱不平,都在谴责那些接受他布施的人,为什么?因为那些接受捐助的大学生毕业五年、十年了,都没有给捐助人写过一封信,表示感谢和汇报学习、工作情况,于是他们的“忘恩负义”受到接二连三的谴责。可见世间的绝大多数人,他是不会真正去布施的,他做这个事,是以交换为目的,是要所谓“双赢”,双方都要做“加”法,虽然不是交换金钱物质,至少是要换来感激、感恩加身,或者是要别人愧对自己,以示自己之伟大,否则他会不高兴乃至气愤,以至大怒到要做电视节目广而告之。殊不知人们在谴责他人“忘恩负义”的时候,这个自私自利的谴责本身,就已经跌破忘我、无私的道德底线了。
十年前我的家乡农村有个女孩,中考获得全县第一名,但是家境贫困无钱上学,许多好心人捐钱给她,客车驾驶员也许诺“她每次回家都可免费乘车”,这些帮助让这个孩子顺利进入州府所在地一所重点中学就读。以后她每次回家,那个驾驶员都强调让她免费乘车,让这个姑娘感觉很不自在。更使她尴尬的是——有次乘车,车上有个中年妇女突然当着全车乘客大声问道:“妹,你记得我不?我拿过钱给你读书呢!”这个女孩子立即连说感谢,还差点跪了下去。后来还有几个捐款人多次打听她的学习情况,让她不得不一次次地回报和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关心,使这个渐渐长大、开始有自尊心的姑娘经常处在歉疚、感激的紧张状态中,一年多以后学习成绩大降,还产生过自杀念头。
所以我们说,布施的最高境界是“无”布施,就是“太上,不知有之”的境界,你既然做了“减”法,就要“忍”住,真正“空”掉,好像没做一样,不要再给自己做“加”法——关心自己的钱财、精力是否“白花了”、“白费了”。你需要别人感激、感恩,这是小人做交易,不是菩萨做布施。你不要捐资助学,让那个姑娘在老家农村心安理得当农民,靠自己的劳动找饭吃,相比“交易式”的资助,这个功德更大呢!真正的布施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只有修“忍”达到菩萨境界、至少罗汉境界的人,才能把布施做得圆满。我的好友映颛先生说得好,布施需要慈悲和智慧。一般人做布施,他那个慷概解囊的样子很爽、很光鲜,但却伤害了别人,这是极其缺乏智慧的表现。
(八)
老子的无为并非只是做减法,也是做加法,或加或减要因人因时而定。而且或加或减,这其中有个手段与目的、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我们既要重视手段、法门的方面,更要认可目的、归宿这个依止上“减”的必然结果。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前者是过程中的小结果或一个大过程终了的大结果,后者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不是图谋的结果,否则就是“无为而有以为”,无为是假、有为是真的“下德”行为了。无不为既然是自然的结果,那就并不是修道的追求,依然还是过程中的凭借。
老子一生并无著述计划,他在过程中也是打算要做减法的。他晚年须发斑白,骑着一头青牛走过苍茫大地,西渡流沙,从此销声匿迹,这是老子以他的生命历程做的一个大减法。当然在这之前老子还是做了一个大“加”法,即留下《道德经》。老子在离开函谷关出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尹喜的朋友或是学生,他要老子把平生所悟之道写成经文留下,才肯放老子出关。或许老子不是一个极好的老师,没有把尹喜这个弟子教好,他没有得道,因此要老子把修道法门著文留下。老子在被逼无奈之下,便一不做二不休,洋洋洒洒写了五千字的《道德经》,然后独自一人骑上青牛,出关扬长而去,消逝于西北大地的茫茫原野,最终把自己“减”掉了。
孔子的确是大大地做了“加”法的,正因为孔子终其一生都做“加”法,所以他在人类精神遗产中比老子要矮小一截,主要表现在破除执着一件事上——孔子破了后天的分别我执,做到人与人合一,老子前进一大步,破了先天的俱生我执,做到了人与天合一。破除俱生我执,做到人天合一,这是宇宙人生最大的“减”法了,没有比这更大的。我们环顾人类数千年文明历程,只有佛家达到了与老子齐平的高度,并且佛家的破执做得更细腻精致,毕竟佛经就有数千卷,这是佛家在实现“减”法结果之前的过程中需要的一个大“加”法。
除了破执,孔子与老子的区别还表现在价值观上,老子追求的道是“太上不知有之”,孔子追求的仁,在老子看来顶多算是带有感情和功利色彩的“其次亲而誉之”这个等次。道比“上德”还要高,肯定是“无为而无以为”的,孔子的“上仁”要低一个等次,是“为之而无以为”的。这里关键的区分是“无为”和“为之”。老子的无为,也就是他的“减”法,或者说是不增不减,是完全地自然而然的,毫无做秀的色彩,这是最高的境界。孔子的境界差一个档次,因为他要“为之”,并且要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孔子的“为之”却是“无以为”的,就是他的有为(“加”法)没有居心、企图和所求,这是孔子很可爱并且值得尊敬的地方。
从人生幸福的修为而言,一个人认识、体悟的过程(规律)总离不开道理说明和物质创造,其中必然有“加”有“减”。在没有彻悟之前,说明道理这个“加”法本身,也是入道的重要法门。道理说教也像佛家讲的乘筏子过河,没有筏子不行,因此还得用“加”法;但是过河上岸抵达目的地之后,就要使用“减”法——抛弃筏子。人在悟彻以后看待一切说教,自然就有缺陷的一面,北宋道教南宗紫阳派鼻祖张伯端有一首《西江月》词说:“未悟须凭言说,悟来言说皆非。”冯友兰也说:“在使用负的方法之前,哲学家或学哲学的学生必须通过正的方法;在达到哲学的单纯性之前,他必须通过哲学的复杂性。人必须先说很多话然后保持静默。”这段话是冯友兰写作《中国哲学简史》的结语,他正是说了很多话,然后才静默下来。说话的过程是“加”法,静默下来就是“减”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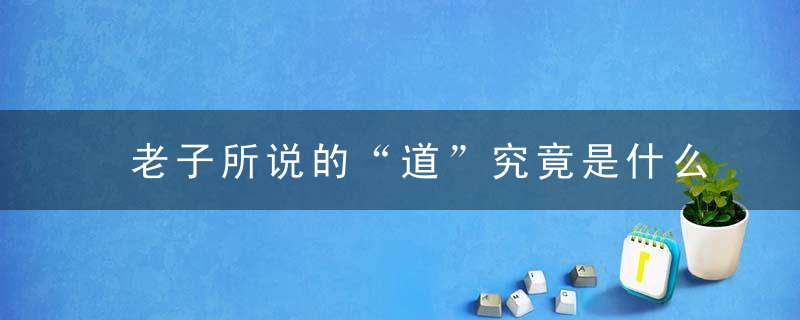






,基.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