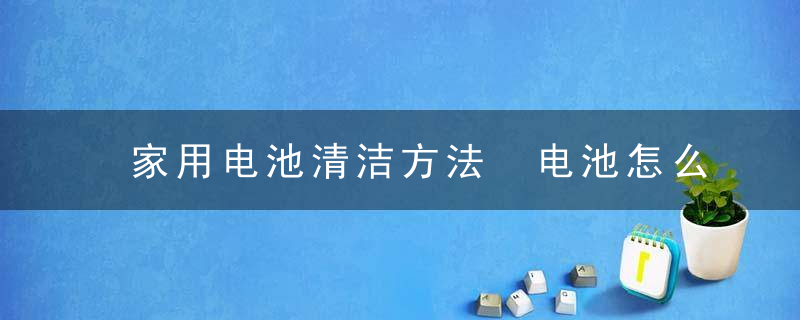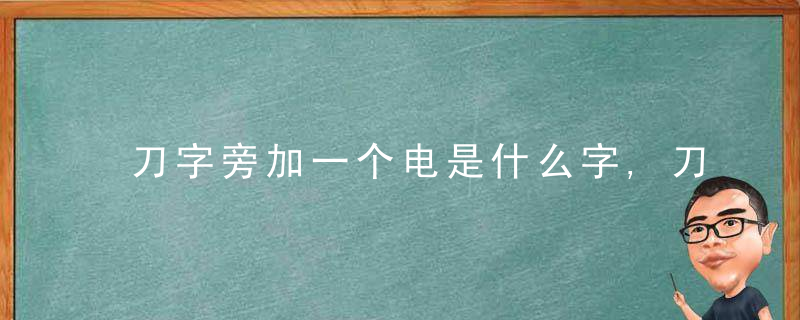抑郁症与性病笼罩下的中国农村

元宵节当天村里争着放起烟花。晚饭后,一位抑郁症患者一人跑到自家阳台。
图片来源:搜狐
据说被恶鬼上身的人会性情大变,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身体常感到不适
作者 | 张若水
编辑 | 小蛮妖
微信编辑 | 侯丽
(一)
彭阿叔就是被“厉鬼”缠身之后,才喝了百草枯死去的。
身着法衣的道士,左手持帝钟,右手拿拂尘,随着法铃震动,跟随其后的道士们击打铙钹、敲响云锣。为首的道士打出连续的吓人呼哨声,后面的道士们开始围着火堆疾走。
为了驱走厉鬼,保家人平安,彭阿叔的妻子不得不请道士做“烧链过火海”的仪式。
火烧得正旺,两条粗长的铁链在火堆中被烧得通红,仿佛两条窜出的火蛇。这场法事从天黑之后开始,将一直持续到铁链烧断。
在超度横死亡魂的仪式期间,彭水湾的村民们不得睡觉。若有人撑不住打了个盹,就会被驱出的恶鬼侵入体内。
据说被恶鬼上身的人会性情大变,喜黑怕光,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身体常感到不适。
一位抑郁症患者回到家直接躺在了卧室的床上,好像渐渐睡了 图片来源:搜狐
很多时候,超度的不是亡魂,是生者罢了。
彭阿叔的妻子王阿娘和两个女儿,身着孝衣,形神枯槁。彭阿叔的两个孙女和一个外孙女笑嘻嘻的,因为年幼,她们不知道她们失去了什么。
彭阿叔的大哥和三个弟弟的脸上也并未显示出任何的悲伤神情来。
对于彭阿叔的不得善终,彭水湾的村民们发出一声声的叹息。他们说,彭阿叔是个老好人,一定是因为他帮忙卖掉彭七爷去世时没放完的鞭炮,被彭七爷的鬼魂上身了。
彭阿叔的家人,是在一个月前才知道他辞去了在窑厂做了十年的脱砖坯工作。离职后的彭阿叔,成天在外晃荡,有时会躲到深山老林里,不回家。
王阿娘气得骂他是“好吃懒做”,彭水湾的老人说他是“中邪了”。
某个晚上,一家人准备熄灯睡觉,发现彭阿叔不见了踪影。屋前屋后找了个遍,最后在猪栏里找到了彭阿叔。
“大,你这是怎么了……”大女儿珍珍望着伛偻的父亲,声泪俱下,“大,你莫吓我…….”
彭阿叔眼神空洞,许久之后,他喃喃道“大不中用……阎王爷派黑白无常来接我了……”
“大要去见阎王爷……”彭阿叔朝猪栏的方向走动着,“鬼差在路上了……”
“妈,妈……我大…….”珍珍和王阿娘哭成一团。
(二)
第二日,王阿娘去了王家村。午后,随王阿娘一起回来的,还有王家村的风水先生。
风水先生前脚刚踏进彭阿叔家客厅,后脚就迈出了门口,站在走廊上,望着院内的一棵榕树道,“树顶见屋,必见鬼屋。”
风水先生连连摇头,“阴宅啊。”
“求您救救他大”,王阿娘双手颤抖地奉上一叠钞票。
风水先生接过钞票,悠悠道,“避煞化解之法——立马叫人砍了这棵树!”末了,不忘嘱咐一句“往后也莫在院内栽树了。”
当天傍晚,那棵长了十几年的榕树,倒下了。
自此以后,彭阿叔不躲在猪栏里了。等一家人入梦后,他就到村子外晃荡。
起早干农活的彭水湾村民,有时看到彭阿叔躺在草垛里,睁大着眼睛,把过路人吓得半死;有时看到彭阿叔抱着一棵老槐树,嘴里念念有词,听不清在说些什么,过路人上前去搭话,彭阿叔也不理睬。
有一天,挑大粪的彭小毛撞见彭阿叔站在池塘里,吓得彭小毛赶紧扔了肩上的粪桶,跳到池塘,拉住已被水没过腰的彭阿叔。
彭小毛将湿漉漉的彭阿叔背回家里,叫道“肯定是被水鬼拉下去的!”
王阿娘这才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安顿好彭阿叔后,她让大女儿珍珍在家照料着,自己去曹家岭请来了神婆。
傩戏驱魔 图片来源:搜狐
神婆来到彭阿叔的床前,对着珍珍吩咐道“把你大扶起来。”
彭阿叔搀着珍珍的手,按照神婆的意思跪下。
神婆点燃王阿娘递过来的黄表纸,尔后从怀里取出一张画满看不懂符号的黄纸,朝着彭阿叔念——
“我是天目,与天相逐。睛如雷电,光耀八极。彻见表里,无物不伏。急急如律令!”
神婆烧掉手中的黄纸,取过王阿娘准备好的白色瓷碗(内有半碗水),将黄纸燃尽的灰抓到碗里,晃动几下之后,将瓷碗放在彭阿叔的手上,命令他喝下去。
“大——”,珍珍的眉头皱成一团,转向她母亲,“妈,这么脏的水喝下去——”
“不要乱说话!”神婆厉色打断她的话,“你们先在屋子里待着,在我布好阵前,不要出来瞎转,万一碰到什么就坏事了!”
说完这些,神婆从她随身携带的包里倒出几只鞋来。先在彭阿叔的房门头上挂好一只鞋子,相继在卧房、厨房、大门口都挂上一只鞋子,意为“辟邪”。
然后,神婆点起一把香,走到屋外,将手中的香一根根围绕着彭阿叔家的房子插下。
“这是干什么?”珍珍不解道。
“此乃封房,任何鬼怪休想进家门!”神婆这次没有发怒,“过几天你大就好了!”
“多谢神婆!”感激涕零的王阿娘,从兜里掏出一叠钞票,双手奉上。
神婆笑着接下王阿娘的钱说:“我不过是积德罢了”。
(三)
过些日子,彭阿叔的状况似乎有了些好转。但仍时常不语,连他最爱的孙女喊他“爷爷”,也仿佛没有听见一般,坐在院子里发愣。
王阿娘心想彭阿叔可能是生了什么怪病,决定和珍珍带他去镇上的医院检查检查,抽血尿检B超胃镜全都来了一遍,愣是啥毛病也没有。
这使得王阿娘更加确信彭阿叔被恶鬼缠身。黄大仙附体的神婆,远近闻名的风水先生、以及西医的先进仪器都无法对付。王阿娘别无他法,开始吃素念经,烧香拜佛,在家熏艾(据说,鬼怪不喜欢艾草的味道)。
王阿娘不知道的是,这些厉鬼,没有哪路神仙能奈何得了。两周后,王阿娘和珍珍再次来到了镇上的医院,还有躺在急诊室病床上的彭阿叔。
“医生,今天忙得很吧?”彭阿叔笑着和医生寒暄,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是啊,”医生勉强挤出一个笑容,“你现在想不想吃点什么?”
“我高兴得很,”彭阿叔神情安然,“我从来没像今天这么高兴过。”
与医生说着话的彭阿叔,仿佛之前的那些苦痛已经离去了,仿佛附在他体内的厉鬼们也离开了。
医生露出一丝苦笑,示意王阿娘和珍珍出来谈话。
“你们准备后事——”医生还没有说完,整个急诊室只能听到王阿娘的哭天抢地声。
“不是洗胃了吗,我大刚刚不是和您说话来着,他好好的呀”,珍珍哭着乞求,“医生,您救救我大……”
“百草枯服用40毫升以上,中毒的死亡率基本上都是100%,你父亲他喝了100毫升……”医生解释道,“你们节哀顺变……”
从医十几年来,医生在急诊室和血液透析室接待了太多服用百草枯的农民,“我从未见过喝下超过15毫升百草枯还能活着出去的”。
农村抑郁青年在医院接受治疗 图片来源:搜狐
医院回家的路上,彭阿叔开始说不出话来,呼吸也变得费力而急促。到家后的第二天,彭阿叔的口咽部已经溃烂得厉害,接着就开始吐血,吐出来的血,王阿娘怎么也擦不完。
珍珍的眼泪从父亲的手背上滑到她的手心里,她紧紧握着父亲的手,想要从阎王爷手里拉回父亲,她的肩膀因为抽噎的缘故而抖动着。
“爷爷,你吃冰棍,”彭阿叔3岁的小孙女跑到床前,手里拿着根冰棍,“吃了冰棍就不痛了。”
“妈妈,爷爷睡着了。” 小女孩站在床边,望了望流泪不止的母亲,又望了望嚎啕痛哭的奶奶,不知所谓。
彭阿叔含了一口小孙女喂的冰棍,离开了人世。村里人闻讯,纷至沓来吊唁。离去之后,他们不免讨论起彭阿叔的死来。
(四)
“听说,彭阿叔是神智不清,拿了池塘边的农药瓶子装水喝才中的毒?”
“根本没有的事!他们家里人怕传出来丢脸呐,扯谎你也信!”
“那是彭阿叔自己喝的农药?不是被鬼缠身吗?”
“有可能是彭七爷的鬼魂!他跟之前的彭栓一样中了邪……”
他们口中的“彭栓”是一个因为“中邪”而一把火烧了房子的退伍小伙。彭栓在患病前,是个长相帅气又懂事的年轻人,深得彭水湾长者的喜爱。三年前,彭栓开始“中邪”,瘦得不成人形,每天晚上跑出家门,跳过池塘跳过水井。
一位抑郁症患者在路灯下茫然地呆站 图片来源:搜狐
他的父母为了防止他跑出来,只好把他锁在房间里。某天下午,正在棉花地锄草的彭栓父母被邻居告知,他家房子着火了。当年迈的双亲看到儿子烧焦地不能辨认的躯体时,痛不欲生。
大学读心理的王家表妹曾提了一嘴彭栓是不是抑郁症,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姨娘超她使了使眼色,笑道“小孩子别瞎说”,便把话题岔开了。
“抑郁症”这种病,彭水湾的村民听都没听说过的。即便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6年中国农村精神障碍的死亡率高于城市。在村民眼里,他们想寻死,那都是“想不开”。“心情不快怎么能算是病”?
1990-2014年我国精神疾病死亡率及其排序。
图片来源:中国产业信息网
人们对不了解的事物,总能与鬼怪扯上关系。像彭栓和彭阿叔这样从前好好的人,突然变了样,不是中邪,又是什么?
“我估计,彭阿叔是真的想寻死……”
“我听说啊,王阿娘就骂,你个臭不要脸的……”
他们声音慢慢放低了下去。大家会意,他们在说那件事。那个彭水湾村民知道的而彭阿叔家人想要掩盖的“秘密”。
十年前,彭阿叔也是彭水湾外出打工的一份子。他和家里其他四个兄弟,在外面修铁路。有一年春节回来,王阿娘叫他以后不要出远门了,到家门口找点事情做。
“钱是没有外面挣得多,总好过你出去逛窑子!”王阿娘满脸怒色,声音响彻了半个村子。
彭阿叔自知理亏,没吭声。
“还搞了一身病回来!”王阿娘骂骂咧咧。
很快,整个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彭阿叔得了“梅毒”——一种生活作风不正的病。只要去他家串门,会发现客厅塞进了一张木板搭的小床。白天,那是会客的沙发,晚上那是彭阿叔独自睡觉的地方。
(五)
在外修铁路的时候,碰上休息不用干活,彭阿叔和其他工人就会在一起打牌解闷。有时牌也懒得打了,大家就喝点啤酒吹吹牛,男人们几句话以后就离不开女人了。
有些工人是像彭阿叔这样与老婆长期两地分离、一年才能回家一次的,其他的是年轻未婚的或者年长的寡汉。这种时候,大家都异常的苦闷。
“我们去人民广场走走吧”,有人发出暗号。
每天晚上六点半以后,一些浓妆艳抹的女子或站或蹲在广场上,她们的年龄在30岁左右。她们只要看到像彭阿叔这样民工打扮的男人,就会上前来拉住他的手。
每个月一发工资,几个相熟的工友们都成群结队大家去找小姐,有时在人民广场,有时在按摩店。
至于保护措施,是超出彭阿叔考虑范围的。一是戴套不舒服,二是“艾滋病”这种病是富贵人得的。当然,陪着一起冒风险的还有提供性服务的小姐们。
彭阿叔觉得自己是“倒了血霉”才得“梅毒”的,因为之前他没听说其他工友得过性病。
“梅毒”——这两个难以启齿的字,是将彭阿叔钉在耻辱柱上的钉子。
彭阿叔在地头田间行走,遇到村里人时,头总会不自觉地低下去。
彭阿叔一下子觉得自己的头有千斤重,头痛欲裂,使得他整宿整宿都睡不着。他起身,望着院子里的榕树,第一次他有了想死的念头——吊死在树上,一死百了。
一位抑郁症患者今年刚36岁,患上抑郁症已经有18年 图片来源:搜狐
一想到女儿们看到自己挂在树上的样子,彭阿叔打消了上吊的念头。比起寻死,或许离开彭水湾是更好的选择。跟着几个兄弟去城里打工,这样的话,他就听不见王阿娘的争吵不休,看不到彭水湾村民们嘲弄的眼神。
然而王阿娘不允,理由自然是害怕彭阿叔把辛苦钱用到小姐身上去了。
“家门口能找到事情做就别去城里了,我在服装厂做裁缝也能挣些钱”,珍珍劝道。
大哥也劝他:“现在不比前几年了,不识字在城里混不下去啊,你人又太老实,在外面肯定是要吃亏的!你在家里总能照应照应他们娘几个。”
“我听老四说望丘山的窑厂要人,你去那吧,总比种庄稼强些”,大哥点起一根烟正要递过来,彭阿叔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已经戒了。
(六)
就这样彭阿叔每天骑着摩托车,往返于窑厂和彭水湾。窑厂的工作是早晚班制,早班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下午一点,晚班则是下午两点到凌晨五点。
彭阿叔每天的工作是脱砖坯。坯模子是由四块砖的空间组成,也就是说每脱一版坯子,就有四块砖坯子出来。脱砖坯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技术。干不好的话,脱出来的砖质量不好,烧制的时候容易弯曲变形,掌握力度和技巧才是关键。
脱砖坯是计件工资,最多的时候彭阿叔每天能拿到200块钱。按照每块砖挣五分钱,彭阿叔一天得脱四千多块砖。
干完活后的彭阿叔浑身黑乎乎的,洗澡的时候直接跳到附近的河里。河里洗完之后,回到搭建在窑厂边上的窝棚里,再用一桶清水从头灌下,才能洗干净身上的黑泥。
在窑厂闷热环境工作的工人们,总在午休时间抽根烟解闷,但彭阿叔从不参与其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戒了烟的缘故,更多的是因为他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话题,他们会谈自己贤惠的老婆有出息的儿子。彭阿叔能跟他们聊什么呢?
难道聊王阿娘的不体谅,难道聊留在家招亲的珍珍,难道聊年纪轻轻的自己在窑厂工作是因为不得已?彭阿叔实在是没什么好跟这些上了岁数的人聊的。
农村的男性劳动力,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建起无数的高楼大厦、高铁高速,只有在春节或农忙的时候回来与家人团聚。留守彭水湾的是老弱妇孺,像彭阿叔这样留在农村的中年男子是异类。所以,不管是在工作的窑厂还是彭水湾的家里,彭阿叔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
如果说窑厂的工作是每天忙得汗流浃背,那么回到家里,彭阿叔也没什么好日子过,王阿娘对着他不是吵就是骂。治愈“梅毒”并不是什么难事。可人与人之间慢性的、长期的“病毒”,却一点点地侵蚀了彭阿叔的心。
“臭不要脸的东西,滚!”——这句诛心的话成为王阿娘吵架时使用率最高的一句。
即使彭阿叔早已痊愈,王阿娘还是拒绝与她的丈夫同床而眠。有时彭阿叔无意间碰到她的身体,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恶狠狠地瞪着她。王阿娘的眼神里,有怨恨,有轻视,更多的是厌恶。
渐渐地,彭阿叔也跟着嫌恶自己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嫌弃自己碰她的手,接着是他的性器官、他整个身体、他的灵魂、他的心,丑陋肮脏。
(七)
彭阿叔知道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以吃,但有那种可以让他一解百愁的药可以吃。
彭阿叔在窑厂工作的十年间,他的兄弟们,仍去城里打工,家里的两层洋楼盖起来了,生活日渐富裕,这两年还在城里购置了房产。
彭阿叔家的老楼房,是留在家招亲的大女儿珍珍挣来的——王阿娘和彭水湾村民都是这么看的,甚至,彭阿叔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
想到自己的“不中用”,彭阿叔会在无眠的深夜里,老泪纵横。他想,这样肮脏又无用的自己是不配活着的。他想,他应该在死之前为家人留点什么。
图片来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