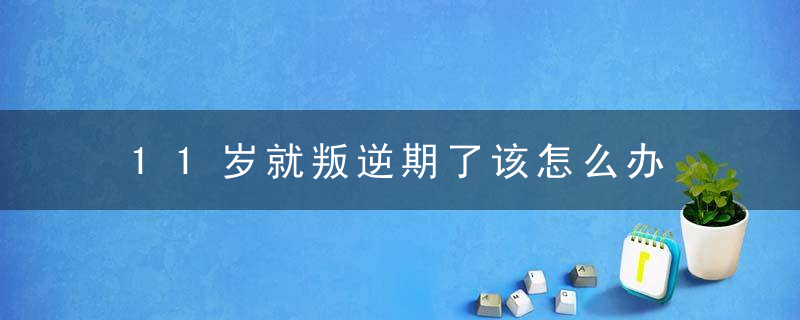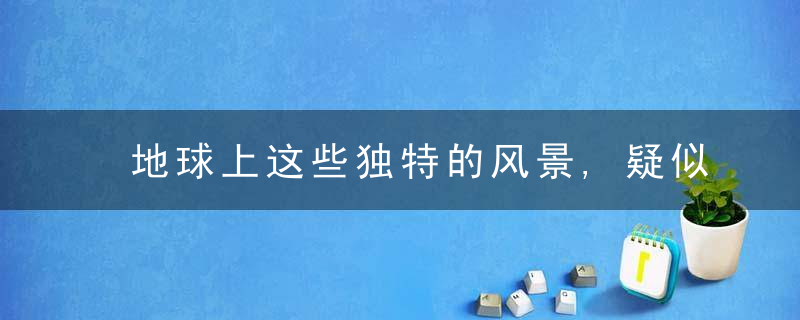大时代,我们谁又不是外省青年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读来仍然真实,
就是因为我们熟悉时代剧变的剧本,
也熟悉那种一直没有改变的、生活在异乡的巨大不安全感。
1993 年,年轻的罗振宇第一次来到北京。
他站在朝阳门桥下看着车流,突然生出了绝望的感觉。
早上 5 点钟,罗振宇走出火车站,满大街都是面包车,10 块钱一趟,是他坐不起的价格。旁边的大楼里的灯逐渐亮起来,这样的庞然大物,并没有给人安心的感觉,而是让人显得对比之下更迷茫了。
“将来哪辆车会是你的?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25年后他这样回想。
所有人都站在时代的背景之前:南方讲话之后,改革开放开始,只要能抓到老鼠的猫就是好猫,一批人开始先富起来。罗振宇感到强烈的时代震荡,是从大学室友们开始。刚进学校宿舍的时候,大家的生活费都差不多,可能你 60 块,我就 80 块,每个人都会为了晚上要不要留出一块钱吃一碗面而纠结。等到他毕业的时候,贫富差距出现了。
毕业以后,不再有“分配”,这时候,家庭关系的差异、富裕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一个人毕业去向的不同,而他选择了一个逃避的港湾:考研。
他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
1993 年,陈嘉映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完毕,回到北京。后来他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才过两三年,已经没有年轻人再对文化感兴趣,都是先富起来。一夜之间人文学者的地位一落千丈。”
在这样的环境下,考上研究生的罗振宇,第一次拎着两箱书走进宿舍,却撞上了室友丢在地上的一大堆啤酒瓶。
室友问他:“几点了?”
罗振宇戴着表,看了一眼,告诉他几点。
室友说:“还戴表呢?”
罗振宇回答:“戴表怎么了?”
室友又看了他一眼:“还读书呢?”
罗振宇说:“好吧,不好意思。”
90 年代的罗振宇第一次为了自己是读书人道歉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想到,自己以后会把知识咀嚼、切片、分装,以知识服务的名义,卖给渴望文化的大众。
但是他的商业策略,又似乎带着 1993 年那个时刻特有的焦虑。他曾经举行现象级网路红人 Papi 酱的贴片广告资源拍卖会,最终以 2200 万的天价成交。业界人士对他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就有批评说,这样的拍卖只会把 Papi 酱的价值一次透支。但罗振宇的回应是:
“我当然要把她的未来一把透支啊,这是现代商业的本质,要不怎么会有金融呢?……回到人这个最基本的出发点上,就是应该一把透支未来,让自己获得这个瞬间的资历,或者说地标性的位置……
《十三邀》主持人许知远在他的新书《偏见》中,讨论了他对于罗振宇的商业哲学的评价,这个评价落在了罗振宇的外省青年的形象上:“从芜湖的少年时光开始,那种强烈的生存哲学从未真正改变过,似乎总有一条饿狗在他身后追赶。”
如果曾经切身经历无法预测的时代变化,如果曾经站在车流之间,看如同怪物一般的异乡的大楼,也许更要疯狂地向前跑,跑到不需要因为是读书人而道歉的时候,跑到知识被切成菜肴端上桌面,却也喂不饱任何人的时候。
1993 年,是姚晨第一次入错行的开始。
她在福建南平长大,家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从事过演艺行业,但因为长得个子高,学校的文艺部老师就问她,要不要去参加北京舞蹈学院的招生。邀请的动机和舞蹈没有什么关系,姚晨答应的动机也和舞蹈没有什么关系:她想去看北京,北京有天安门。
即使从未接受过舞蹈训练,姚晨还是被舞蹈学院的老师挑中,据说是因为身材比例达标。1993 年姚晨顺利地来到了北京,当宿舍的同学都因为要和父母分离而哭成一片的时候,她心里特别高兴:我终于来北京了,也许有一天还能成为一个舞蹈家。
但是到了大二,姚晨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舞蹈天赋:身体的柔韧性不够,做动作也不能举一反三。她想要通过勤奋改变现状,于是在宿舍的同学们都睡觉以后,她还会穿上塑料布衣服,到楼下跑步。
她最终还是承认自己入错了行:有些时候,努力也无法补足天赋。
即使发现了这件事,她仍然要在舞蹈学院继续三年的学习。
“你发现了,也不可能逃出去呀。”姚晨这样说。
幸运的是,她在大学时遇到一位表演老师,认为她有表演天分,说服她去考表演。来到北京电影学院的姚晨,成为优等生,如果同学们要排练《暗恋桃花源》,她一定是云之凡的角色,一直是大青衣;当时的老师都说,如果跟姚晨一组,就能提高你们的作业质量。
但到了第二、第三年,她发现了变化,宿舍里突然都没人了。
同学们都被挑去拍戏、拍广告。而主持试镜的人见到姚晨总会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怪”;“这孩子长得挺有特点的,就是不知道该把你往什么地方用。”
太长时间没有戏拍的姚晨想,“我是不是又选错道了。……那么好吧,再改行。”
她再一次选择道路,去做情景喜剧演员,演《武林外传》。直到她有一次去报刊亭买杂志,在《南都娱乐周刊》上发现了自己的偷拍镜头,跟踪自己和伴侣的生活,在恐惧感中,才意识到自己突然有了名声。
在观众眼中,出了名的姚晨已经变过好几次道:在情景喜剧后,她又去演了《潜伏》,换了一个角色类型;然后成为“微博女王”,成为平台上首个粉丝突破百万的用户;再之后,做了联合国难民署的中国区亲善大使。
尽管如此,她现在还会用蛤蟆,来比喻自己的感受。
大学的时候,姚晨读黑泽明的《蛤蟆的油》,说到日本的深山里有一种蛤蟆,长得极其丑陋,当地人会把它抓起来放在镜子前,它发现自己是那么丑陋,就会惊起一身油,这种油可以提炼来治疗烫伤。
姚晨说,至今仍然常常有“惊起一身油”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来自幻想成为舞蹈家的年轻时代、在学校剧目中出演大青衣的时刻、被人跟踪偷拍的时刻,1993 年以来,从来到北京开始,似乎辉煌又黯淡下去的起起伏伏,会让人担心,也许某个时候,镜子会再次照过来。
1993 年,也是贾樟柯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读文学系的时刻。而他回顾自己故乡的次数,也许比罗振宇和姚晨都要多。
他和汾阳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在影坛崭露头角,是从“故乡三部曲”开始:在《任逍遥》《小武》《站台》里,作为背景的汾阳就是一个重要角色,操着方言的人们诉说着普世的情感。到了欧洲影展的时候,贾樟柯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把他的体验与汾阳连在一起:“北京是更大的汾阳,巴黎是更大的北京。”
许知远在他的书《偏见》里谈到贾樟柯,认为贾樟柯是让人羡慕的。“那些县城的个人故事、感伤时刻、无所事事、光荣与梦想,滋养了他,令他足以坦然面对任何新变化。……他诚实地带着他的县城经验,从容地进入了世界。”
拍电影二十年来,贾樟柯越来越想回到汾阳生活,回到当年的街道,和小伙伴们一起晚上去看电影,或者到县城去看演出。他谈起一个故乡的朋友,从八十年代末开始沉迷香港电影,从电影中研究香港的地理位置,并且能够准确地画出一张香港地图,标出港岛、油尖旺、九龙——黑帮电影中出现过的地点。等到贾樟柯到了香港,发现位置都准确。他说,总想把这个朋友拍进电影里——直到现在,故乡仍然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他不是一个焦虑的外省青年。事实上,站在汾阳的角度,去看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会觉得,外面的世界发展得太慢了。
在拍摄《三峡好人》的时候,他对于阶层固化有了第一手的感受。深入长江流域之后,人们的生活似乎是流动的,但这种流动并不带来改变,而是从长江打工,变成到东莞打工。到了奉节老城,满城都在放烟花,剧组的人都误以为是要欢迎他们,一问才知道,是一个老板的儿子过生日的庆祝节目。而在奉节的普通人家,是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的,只有“一个竹椅子,一些塑料袋,全部的家底”,贾樟柯就这样描述他的见闻。
自从拍戏以来,贾樟柯也会遇到来自观众的质疑。让他感到失落的不是质疑本身,而是这些质疑在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变化。
他总结了自己最常遇到的三种质疑:一是他的作品题材讨好西方人;二是他的电影不赚钱,是脱离大众的文艺电影;三就是他在近年来,开始进行一些商业操作,例如接拍大量广告,又会有人感觉到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独立导演。采访他的 90 后记者,请他回应的仍然是这些问题,人们的思想仿佛不再改变了。
于是,他在戛纳领奖的时候,做过这样的发言:
“我刚拍电影的时候特别有激情,我觉得电影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我觉得世界改变得太慢了。”
每个人的人生中,都有可能成为外省青年。
也许为了某种理想的生活,而迁徙到陌生的城市,又或者,在想要安于现状的时候,被时代巨变而击打成一个异乡人。而生存,就是与这种长期的异乡感、不安全感博弈,有些人想要向前奔跑,把不安全感甩在身后,也有人把不安全感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在自我怀疑当中生活,也获得更多自我提升,又或者,有人成为不安全感的旁观者,尝试去理解,时代的种种焦虑的来源。
这样的不安全感,也许也来源于我们身处的国家,它被某种物质生活高度成长的焦虑裹挟:这个国家突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需要与新的规则博弈,又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那是一种被突然抛入新环境的外省人心态--迷茫、无奈、被迫做出选择。
1993 年的故事,如果读来仍然真实,因为我们熟悉时代剧变的剧本,也熟悉那种一直没有改变的、生活在异乡的巨大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