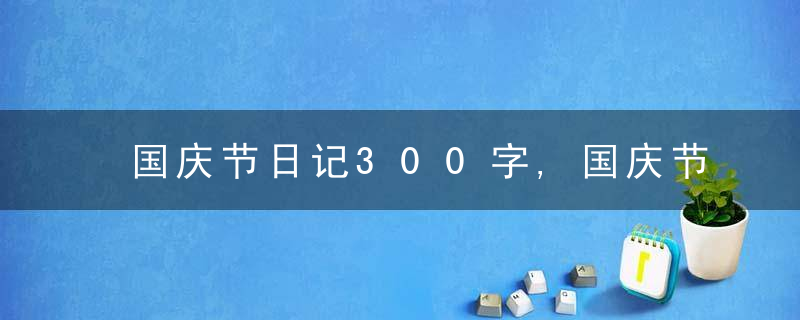农村自杀老人的平静和惨烈

●●●
“体面”的自杀
林木文(化名)沐浴之后,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这个69岁的老人坐在堂屋中间,一边在火盆里为自己烧纸钱,一边喝下半瓶农药。纸钱烧了一半,老人躺在地上不省人事。
“他很久以前就开始计划自杀了。”刘燕舞后来听说。待人们发现时,林木文已经没了呼吸。在这个距武汉不到100公里的村庄里,村民猜测老人自杀的原因是与儿媳失和。“他怕将来死了,孩子连纸钱都不给买。”一位村民对刘燕舞说,“这样死,还‘体面’些。”
那是2008年,刘燕舞所在的研究团队在湖北京山县进行田野调查。当问到村庄里有没有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时,得到最多的回答竟然是:“我们这里就没有老人正常死亡的。”
这也是成为刘燕舞研究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开端。6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项目主持人的刘燕舞走进湖北、山东、江苏、山西、河南、贵州等11个省份的40多个村庄。
他发现,林木文的悲剧不是个案,农村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他用驻村400多天的调查数据,画出了一条“农村老年人自杀率”的曲线:从1990年开始,中国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大幅提升,并保持在高位。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不久前香港大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进10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跌至世界最低行列,每10万人自杀入口不足10例。
“中国的自杀率总体上是在下降的。”刘燕舞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然后换了一种沉重的语气说,“但是,农村老人越来越难摆脱(自杀)这条路,这或许是他们稀释和消化现代老龄化社会痛苦的特有方式。”
可靠的药儿子、绳儿子、水儿子
林木文的死,并没有在老人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激起多少波澜。甚至,老人曾当过村支部书记的儿子,也没有像刘燕舞以为的那样责怪妻子,而是“很坦然”:“人总是要跟活人过的,难道还与死人过日子不成?”
刘燕舞说,自杀在当地被视作正常、甚至合理的事。村民们觉得犯不着议论并得罪他的儿子,“死了也就死了”。
不仅是普通村民,乡村医生对待自杀的态度往往和村民一样,“将其看作正常化死亡”。特别是当老人得了疾病有“磨不过”,选择自杀,乡村医生都不觉得这是自杀。
这让刘燕舞一行人震惊不已。“越是平静,越是让人不寒而栗。”刘燕舞的师兄杨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刚开始访谈老人自杀案例时,往往气愤的不行。一次访谈一位老太太,三天后老太太与媳妇吵架自杀身亡。学生们参加了老人的葬礼,眼睛死死盯着谈笑风生的老人的家人。
倒是老人比这群年轻人看得开。“我们这儿的老人都有三个儿子。”一个柴姓老人乐呵呵地告诉满是疑惑的刘燕舞,“药儿子(和农药)、绳儿子(上吊)、水儿子(投水)这三个儿子最可靠。”
实际上,老柴还有两个让他“引以为豪”的儿子。大儿子在镇上工作,小儿子在外打工,一个在镇上有楼房,一个在村里盖了楼房。但是7年来,老柴一直和腿脚不便的妻子逢雨便漏、倾斜的随时可能倒塌的土坯房里。
与刘燕舞一起调研的,还有另外40来个师生,他们分成10个小分队,驻扎在湖北京山县10个不同的村子里。他们都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
刘燕舞慢慢发现,林木文的死,并不算严重或者惨烈。在过去6年的调研里,他听到的故事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不少老人,因为行动困难,拿不到药水瓶也站不到板凳上悬梁,便在不及人高的窗户上,搭起一根绳,挎住头,蜷起腿活活吊死。
有两位山西的老人,儿子不给饭吃,还屡遭媳妇打骂,头朝下扎进家里的水窖中。“这些都是有必死决心的。”刘燕舞分析到。
他还记得有人跟他介绍说,一位老人要自杀,怕子女不埋他,便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挖土。
这样的案例接触多了,刘燕舞不禁叹息:“很多故事村民嘻嘻哈哈跟你讲,但都悲惨到难以想象。”这个脸被晒黑的青年学者说,“有时候会有股想逃离的感觉,就觉得这个世界不属于我。”
在自杀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更让刘燕舞等人震撼的是,在农村老人寻死的故事里,发现“他杀”的影子。
杨华了解到,有一对老年夫妇,同时喝农药自尽。老太太当场死亡,老爷子没死,但家属并不送到医院。第二天家里人给老太太办丧事。就让老头躺在床上看。第三天,老头命毙,就着为老太太办事的灵棚,立马又为老头办了丧事。
还有一个在外打工的儿子请了7天假回家,看望病危的父亲。两三天过去,发现父亲没有要死的迹象,这个儿子就问父亲:“你到底死不死,我就请了7天假,是把办丧事的时间都算进来的。”老人随后自杀,儿子赶在一周内办完丧事,回城继续打工。
“现代讲究市场理性,讲究竞争,看重核心家庭的利益最大化。”刘燕舞解释道,当农民之间,甚至一家子父子、兄弟间都开始按市场的思维方式处理关系,人们开始算账。
不少人给刘燕舞讲过给老人治病的帐:假如花3万元治好病,老人能活10年,一年做农活收入3000元,那治病就是划算的;要是活个七八年,就也不太亏本;但要是治好病也活不了几年,就不值得去治。
在不少老人的心里,这笔账的算法也是成立的。“农村自杀的老人中,有超过一半带有‘利他’性质。”杨华将农村自杀老人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利他型”的老人最多,他们倾向于为子女着想。
“这些老人不想变成子女的累赘。”杨华说,“自杀的后果也将给子女带来收益。”甚至,他们即便自杀还处处为子女着想。他们有的不在家里自杀,而是选择荒坡、河沟帮子女避嫌;或者与子女争吵后不自杀,待到关系平静后才自杀;还有两个老人都想自杀,也不会选择同一天或同一个屋自杀,而要错开时间,以免对子女家庭产生不好的影响。
刘燕舞认为,如果不到万不得已,老人都不会选择自杀。“一些老人说,宁在世上挨,不往土里埋。所谓‘利他’的表象背后,实质上更多的是绝望。”
刘燕舞的老师,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将这种已然形成的“自杀秩序”归因为“代际剥削”:自杀的老人年轻时“死奔”,给孩子盖房、娶媳妇、看孩子、一旦完成“人生任务”,丧失劳动力,无论是物质还是情感上,得到的反馈却很少。
“被榨干所以价值后,老人就变得好像一无是处,只能等死。”贺雪峰说。
在“代际剥削”大行其道的地区,与之伴随的,是农村老人自杀潮的出现。特别是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明显。
刘燕舞将这种自杀潮的出现称为病态。“2000年后,农村老年人自杀率升高特别快,且水平极高。”刘燕舞不无忧虑地说,“用‘极为严峻’来判断这一形势并不为过。”
刘燕舞认为,在病态的自杀潮背后,更多的是经济高度分化,给中年人带来的集体焦虑,那就是他们如何在市场社会中轻装上阵,参加激烈的竞争并胜出,无疑,作为比他们更加弱势的老人,就成了他们要甩掉的包袱。
“我自己负担都这么重,我哪能顾得了老的?”一些访谈农民直白地告诉刘燕舞。
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每年,刘燕舞有3个月在农民家中做田野调查。据贺雪峰介绍,整个中心每年的调研时间有4000天,平均每天有10人在乡村做访谈。
“我在全国跑的感觉是,随着现代性的侵入,传统性的没落,各地农村都在向京山方向靠拢,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刘燕舞说。
与他们的调查一同跑步前进的,还有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这意味着中国仅老年人口数,就相当于印尼的总人口数,已超过了巴西、俄罗斯、日本。其中,80岁以上老人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去年已达到2300万人。而且失去自理能力的老人继续增加,从2012年的3600万人增长到2013年的3750万人。
据刘燕舞介绍,在农村自杀的老年人中,有六成多集中在7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中国老龄化日益加深,京山的今天可能是很多地方的明天”。
许多尚未踏入老年的中年农民,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明天做筹算。他们在完成“人生任务”同时,不再指望养儿防老,而是留着部分积蓄购买商业保险。在法治意识较强的东部地区,有点老人向法院起诉子女应尽赡养义务。
据刘燕舞统计,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之后是情感问题。
换句话说,要减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就要解决三个问题:不饿死,不病死,不寂寞死。
刘燕舞建议,要解决当前矛盾,可以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和医疗矛盾。
国家推行的新农保每月只有55元,让不少老人有了盼头。“那就先不自杀了,再挺两年。”不少老人对刘燕舞说,“终于有人管我们了。”
另一方面,贺雪峰在湖北洪湖、荆门等地,陆续发起成立了4个老年人协会。协会有老人自发推选会长和理事,村里有老人过80大寿,协会去松块长寿匾,有老人病了,协会去看望,有老人去世,协会去送花圈······据当地老人说,有了协会,村里“挂面条”(上吊)的少了。
研究了6年老人自杀,刘燕舞最大的希望是这一问题能引起关注,“老人应该活得舒服些,能从容地面对死亡,能走的有尊严点,而不是采用非常规的手段,那太悲凉了。”刘燕舞说,“人都会老。”
“事实上,多数自杀的老人,其实是不想死的。”刘燕舞还记得2011年冬天去应城农村做访谈的情景。在他去得头一年,离他住处不远的一户人家,照料着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那年年底,子女们商量,给老人断水、断粮,希望他在年前死掉,“免得过年家里来客人,家里臭烘烘的。”
这是一个倔强的老人,“拼了命地活下去”。他躺在床上嗷嗷大骂,抓起粪便在屋里到处乱扔。一直坚持到大年初一,老人才咽下最后一口气。
● ● ●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