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狗不咬人”为什么没人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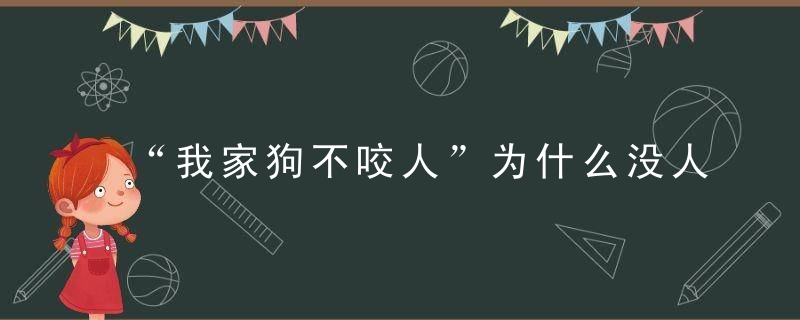
两年前到广西玉林见到一幕幕让我很困惑的场景,其中之一,是不论何种类型、何种体格的犬只,见到完全陌生的“爱狗人士”都毫不犹豫卸下防御。瞬息转变眼神,眨巴眨巴,尽是善意。有的还直接摇起尾巴来示好。但前一秒,它们可能还在笼子里狂吠不止。
近些年的玉林,是中国动物权利争议最激烈的一座城市。从2011年以来,每年的六月中下旬,都有一批批抗议者前来,通过街头辩论、行政举报和司法诉讼等途径抵制“狗肉节”——按照当地人的一种说法,全称是“夏至日荔枝狗肉节”。外界称他们是“爱狗人士”。我用更中性一些的动物权利倡导者或行动者。
玉林城区一家菜市场门口的激辩(2015年6月22日),作者供图。
为收集硕士毕业论文的材料,我到了这座城市,时间是夏至日前夕。烈日当空。
那些外来的抵制者,有的戴着墨镜,在当地人群中显得尤为突出。隔着墨镜,传说中的眼神交流甚至都不存在。但这样的突兀并未激起犬只的丝毫警惕。同年七月下旬,我到重庆参加一部叫《旺旺》的纪录片拍摄,导演说,他到各地拍摄,所见所闻莫不如此。你说怪不怪?我心中的困惑于是更大。
这些困惑,原本只是材料收集中不太重要的花边。我的关注点只是这一场抵制里的“国家—社会”关系(作者注:论文题目《边缘的中心性:动物权利运动中的国家与社会》)。但现在,连日来,围绕成都一起遛狗未拴绳被打毁容事件的争议,重新唤醒了两年前的场景。
成都一女主持人遛狗未拴绳被邻居暴打
按照媒体报道和视频监控,这起事件的过程不复杂。一位女士下楼买东西,将金毛带出门溜,没拴牵引绳。在超市门口,金毛朝一名小孩跑去。小孩家长立即护住小孩,另一名家长一脚将狗踹开。女士见狗被踹上前理论,双方旋即发生肢体冲突。一目了然。
遛狗冲突有(成都)城市养犬管理条例——要求出门遛狗需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拴牵引绳——打架冲突有民法。照常毋需争议。然而,网上的讨论还是炸开了锅,表现为一边倒地狂批遛狗被打女士。骂其“活该”。
被打的女士说,金毛跑到小孩面前只是高兴示好,而非攻击;而在小孩家长看来,贸然冲过来已是一种危险,谁也不知它会不会攻击,如果真咬为时已晚。两者都觉得自己的判断才是对的。“我家狗不咬人”,“它是畜生谁知道”。
“我家狗不咬人”,基本上是绝大多数遛狗者的观念;“它是畜生谁知道”,可能是所有反对者的意见。
毕业来北京工作一年,常常一出门下楼就见遛狗不拴牵引绳,我也有不开心。网上的言语“讨伐”很可能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目睹过这样的场景,而新闻报道中的遛狗伤人事件,乃至前段时间西安和上海等地流浪狗咬人致死,都添了不满和恐慌。但遛狗者是真的相信“我家狗不咬人”。我相信他们是真诚的。道理很简单,谁也不敢看到悲剧产生。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家狗不咬人”这一现今耳熟能详的说法是怎样诞生并流行起来的?
最直接最容易的一种归因是二十世纪末以来的中国城市化。既指土地商品化,更指生活方式和观念的城市化。这意味着,犬只在其中的位置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从守护者到伴侣者,而跟着改变的是我们对它们的性格假设。
我小时候家中养狗,看家护门,俗称中华田野犬。很喜欢它们,高兴时更要搂起来亲吻;但我同时也是一个怕狗的人,看到它们绕着走生怕被瞧见。我猜这或许是生长在农村的许多孩子,都会表露出来的两面,因为狗是两面的,夜以继日地严格判断孰“敌”孰“我”。如果判断失误,是要被视为“不看家的狗”的。养狗的人家非常清晰“善意”是单一向度的。到访者畏惧狗吠,却不太会担心被咬,预设并相信是有绳在拴。这是一个持续了千百年的生活共识。变数不大。
而你看城市生活中的犬只,就不一样,数经变革。早年的民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已在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兴起养猫狗当伴侣。改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城市人家养狗养猫一度被批政治觉悟不高,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格调;到新旧世纪之交,成了新中产阶级的一种“标配”;再到当下,政治和经济的标识意义都已式微。可一直不变的是对犬只的性格假设,是宠物,是伴侣,是可爱而充满善意的。它们眼中可能存在“主人”和“一般人类”的区别,但再也没有“敌我矛盾”了。
这是一个很简单但很重要的不同。你听到的“我家狗不咬人”由此而来。它早已存在,只不过真正的流行是如下两种力量的支持结果。一是新世纪前夜的中国城市住房市场改革,标志着城市化替换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新媒体的成长,即便媒体不报道,那些大街小巷的遛狗冲突也能得到传播。
既然犬只在生活中的位置变了,那一句“我家狗不咬人”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相信?现实生活中有烈性犬,有咬人事件,这些都是原因。但这里要讨论的是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因素,换种问法可能更清晰:这些犬只眼中不分“敌我矛盾”了,但表情和举止,为什么在养狗者和外人的解读中截然不同?这是第二个问题。而现在,需要重提玉林。
常听到一种流行说法,包括评说成都这起事件的,都把养狗者和“爱狗人士”等同起来。在我看来,两者存在天壤之别。
我确实理解不了两年前的那一幕幕,完全超出了自己的生活经验。是不是他们懂得怎样和狗打交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带着善意?何种交道,何种善意,这些都是听起来很虚的主观定义。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是带着善意即可,就该是像我们常听到的,你不惹它,它怎会惹你,大家相安无事才是。
但直到现在,遗憾的是,我还只能从“交道”和“善意”上归因。真后悔当时只看成花边而没有观察更多。
两年前的“狗肉节”前晚,做广州来的一位动物权利行动者的案例访谈。两个半小时,哭了不止四次。在回酒店的出租车上,向着窗外,“明天又有数不清的’狗狗’要被残忍地杀害,我真的很难受、很痛心。”我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情绪的人,也不善于安慰别人。更何况作为一个观察者,除了其中一些交流需要变通,其它时候都不干预他们,反而倒在甄别他们言语中的可靠度。
到了夏至日即“狗肉节”当天下午,玉林城区下了一场大暴雨,天空阴沉,只在电闪雷鸣中被照耀一下。我与四川来的两位动物权利倡导者,走在狗肉餐馆最集中的市场,到帐篷下躲雨。地面上的雨水汇集到路边地处,向着下水道湍急地流,淌着一滩滩狗血,餐馆后院和市场传来狗叫声,撕心裂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血腥味。
他们两位一男一女。向着天空流泪祈祷,随之念出一段话。
刹那间愣住了,我甚至认为不可思议。生于九零年,和同辈人一样都在一种去“仪式化”的叛逆中长大,怀疑中心,怀疑权威,怀疑信念。
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到各地行动。我不能完全认同他们的观念,保持着一个观察者的距离,但回顾现场的那些场景,我选择相信他们与犬只长年累月的交往、互动和磨合,已经改变了他们言行举止,乃至细致到一个嘴角动作和眼神。潜移默化的烙印。他们自己也只能用一个简单的“带着善意”来简化概括。
我们知道,动物表演中的驯服,通常用诱饵和暴力来刺激条件反射。而他们打交道的方式不一样。乍一眼看,是他们的一个动作、一个眨眼、一个声音和犬只建立了信任,但更深刻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却在影响每一个言行举止的日常观念。
可见“善意”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需要实践中的训练才可能具体操作。但现实是,至于这样和陌生狗交往的训练,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比如刚来城市的乡下人,刚上小学的小孩,还有生来怕狗者。眨巴摇尾,十分可爱,稍有不对就可能猛地一攻击。
目前的中国城市化还是低水平的,和陌生的宠物狗相处的经验匮乏,冲突不断,事件一出来,各种争议满天飞。于是有了第三个问题,养狗者和另一部分人的相互交流为什么就这样艰难?“我家狗不咬人”的困境根源是什么?
我们都清楚怎样和陌生的“看家护门”的犬只打交道,对不对?这是因为,默契千百年来都没有大变过。而现在,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实,有的人没有意愿或没有需要和陌生宠物狗直面打交道。因此更重要的问题很可能是,我们与陌生人相处的能力依然很低。
你看“我家”是一种主体性认同。经历过计划下的集体生活,城市中的单位制、农村的人民公社,“我家”是改革年代中破土而出的一种个体化。这一波个体化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同当下出现的单身、独居为两回事。破土而出意味着一种社会自主空间的增长,走出熟人社会和陌生打交道,然而,旋即迎来二十世纪末的消费转型,还有其它层面的因素,使得我们自己并未过上一种平等,相互尊重、协商和妥协的公共生活。
传说是台湾养狗人士与邻居的对话,图源网络
相比于以往,我们更关注自己是否满足,是否开心,而不再是一些遥不可及的宏大符号。然而,缺乏公共生活的个体化,难免会磕磕碰碰,冲突不断,各方受伤。原因是我们会自负自满,会无条件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是正当的,而不顾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经验。
美国青年政治学者阿林·弗莫雷斯科在他的《妥协》中回顾十六七世纪的英法两国,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英国的个体主义能同时做到“向内坚持内心”和“向外平等地协商和妥协”。但法国不。法国的人们认为,向外协商和妥协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而历史证明,那时候,英国比法国的公共生活更漂亮。现今全世界的公共生活和妥协都面临着挑战,只是因素不同。这是题外话了。
我会在脑海中重现两年前的场景,令人称奇,令人困惑,但也知道,那些同犬只打交道的能力,不是所有人都会。我仍然选择相信“我家狗不咬人”是真诚的,并不如人们所言是一个借口。还是那句话,谁也不敢看到悲剧发生。但“我家狗不咬人”也只是一厢情愿,它的诞生是犬只城市化的结果,而它的流行,是在一个自主性腾飞但公共生活干瘪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