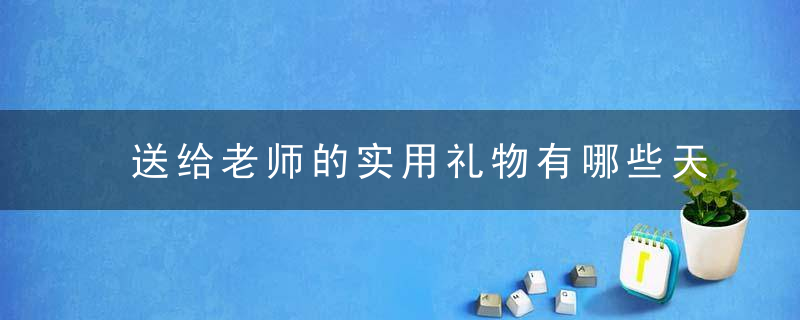(071)军统大案之囚禁小张
军统大案之囚禁小.jpg)
关于张学良与特务们的相处,可谓“前人之述备矣”,尤其是特务们对张的“虐待”,说得活灵活现,好像自己也参加过“虐待”张学良似的。这些说法当中,肯定有些是接近事实的,因为彼此之间,总归是看守与被看守的关系,不可能事事都由着张副司令的脾气。但如果说有意虐待,个人以为,就是借刘乙光们几个胆子,这些人也不敢。
第一,张学良是戴笠的把弟,以戴笠之心狠手辣,他手下这些人去虐待张学良,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第二,老蒋可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说过,要关张学良一辈子。张被终身监禁,是我们这些后人看到的结果,当时的人并不知道。万一哪天老蒋把张学良给放了,以张的身份地位,要“反攻倒算”几个小特务,如同碾死蚂蚁。除了自己找“不自在”,没有人会故意同张学良过不去的。
引起争议最多的,自然是刘乙光,此人一辈子的最大成就,就是“管束”张学良,当了一辈子看守,最后熬成将官,也留下了一辈子的骂名。
据说刘乙光有记日记的习惯,可惜,刘没有公开这些东西。既然刘自己不愿说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听听旁人是怎么说的。
为了解当时的情况,郭冠英曾经采访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
按:郭冠英,生于1949年,时事评论家。
郭冠英在台湾政治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与一位政治系同学王一方成为好友,这位王一方正是王新衡的儿子。
王新衡,我们前面说过,与蒋经国是留苏的同学,回国以后,曾在张学良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当科长。1959年,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接管了负责“管束”张学良的保安处,从此开始与张学良第二次“来往”(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被蒋介石安排在溪口读书时,就曾经与张学良就伴),蒋经国考虑到王新衡与张学良有很好的私交,令王协助自己与张打交道。此后,张学良、张群、王新衡,还有著名画家张大千还组成了“三张一王”的“转转会”,定期聚会。
正是通过王一方,郭冠英结识了他的父亲王新衡,又因偶然的际遇,认识了张学良。从此,用郭冠英的女儿郭采君的话说:“我爸爸不但进入了一个历史的宝库,他还想尽量打开库门,叫对张学良历史有兴趣的人,渴望着、争相想在他们画的史龙上点眼的人,进到这个宝库。”
据郭冠英记载,关于刘乙光一家与张学良的关系,刘伯涵是这样说的:
“我八岁就和张先生、赵四小姐生活在一起。张先生、赵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的子女一样,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母般敬爱。张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躺在书房的地上看书,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拾,后来我二弟学有所成,出国时,张先生和赵四小姐还送了路费,后来他成为了海水淡化专家。我妹妹则和赵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张先生开朗幽默,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了个大西瓜,叫我们回家来吃。我那时已经在巡逻舰上服务了,有时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以望见院宅中的大西瓜。”
张学良确实很喜欢刘乙光的孩子,1956年9月15日,张学良曾在日记中写道:“老刘(指刘乙光)谈到二麻子(刘次子的小名)即将出国,前拟赠之旅费,心领不受,惟拟借两万元的存单一用,用去作抵,两月后即可交还,余慨然诺之。”
郭冠英又问刘伯涵:“你父亲对张先生和赵四小姐到底怎么样?”
刘伯涵说:“有许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甚至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把我父亲写成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的寡情牢头,把张先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的身体一直健壮。……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像的事情。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和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陪张先生与四小姐。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们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没有见到张先生面露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当然,张先生识事明理,知道我父亲是奉命执行任务。有其职责和立场。”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张、刘之间的关系:
1954年年12月25日,张学良写:“早起写上总统及夫人(指蒋介石夫妇)信,交老刘请他派人送去。老刘阅后,认为他要自己亲送。于是我同他谈了我的心愿,彼愿传达,恐言错误事,请我写一简略给他。”
事情的起因,是刘乙光要到台北阳明山去参加“高级官员集训班”,张学良听了,突发奇想,打算请求蒋介石,让自己也去参加集训。
这件事,刘乙光觉得非常重要,担心派手下去送信误事,于是张学良把自己的想法又给他讲了一遍,讲一遍还不行,刘乙光又怕自己转述不够准确,让张给他写一个大概,他见了老蒋好照着说。
12月27日:张学良写:“老刘由台北返来,告知彼到后即报到,总统夜九点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承允,说好了。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
“刘欢喜的一夜未能好睡”,是说当时蒋答应了张的请求,刘乙光高兴得一夜没睡着觉。
哪知道蒋介石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卦了,觉得放张出来不妥。对此,张学良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在28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早起,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脾气,回来胡写信后,经老刘苦说,Edith(指赵四)亦加劝言。……”
29日,张又写:“老刘今早未行,又来余室,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余深感其意(老刘好意可感也),立即再改,交彼即去台北。”
起码在这件事中,张学良连续五天的日记非常能说明问题,即他与刘乙光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守与犯人的关系、否则,刘乙光不会因看到张学良即将获释的曙光而高兴得“一夜未能好睡”,张也不会肆无忌惮地在刘面前“大发脾气”,刘更不会因张学良“胡写信”而来“再讲信中之言有不妥之处”。
刘乙光的日记,我们是没机会看到了,但张学良的部分日记已经公开,披露了许多生活点滴,通过这些材料,颠覆了许多我们过去想当然和以讹传讹的事情,上面讲的刘乙光替张学良传信的事情就是一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937年11月13日,张学良奉命离开奉化移住黄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说:“下午七点动身离山(指雪窦山),七点半由入山亭汽车开动,余自开车,夜十一点半到山乘县汽车加油,经东阳、永康、金华,在金华渡河,天色已亮,在兰(溪)再渡河,约九点半时停于兰属永昌镇休息并宿焉。因避空袭昨连夜离开危险地带。”
次日,张又说:“晨五时起身,约六点五十分在寿昌附近渡河,至淳安午餐(约九点多),经威坪、界口、徽州,约三点许到黄山,暂住于黄山旅行社。余两日来自己开车,行约千里,只睡数小时,身体甚好。”
在这两则日记当中,要注意的是,在两天来的迁徙中,始终是张学良在自己驾车。
张学良会开车,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张连飞机都会开,开个汽车并不奇怪——1936年12月11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与其他“大员”一起到临潼“聆训”,回来的时候,就是张学良亲自驾车,拉着陈诚等人一同到西安新城大楼,参加为“”进陕人员的宴会的。
奇怪的是,以张此时处于禁闭中的身份,居然也可以“自驾车”。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司机不够,而是张静极思动,想过一把开车的瘾,而刘乙光等人又拗不过他,只好由他去。
这样的自由度,作为一个囚犯来说,够可以了吧。
12月25日,开车开得“兴起”的张学良,与路边的火车赛跑,结果车速过快,出了车祸。他自己在日记中说:“因为今日路程不远,九点许方起程,先渡江,经来阳,过黑虎口自己开车撞伤一挑担行人,付给几十元钱。”
11月18日,浙江嘉兴陷落,身在黄山的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蒋先生亲自打来(长)途电话,令我等到萍乡赴衡阳。”
就在一周前的11月11日,淞沪抗战失利,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会议”决议迁都重庆。老蒋在焦头烂额之际,居然还会打来电话安排张学良的行止。难怪在这里,张学良用了“亲自”两个字,想必,他也对老蒋的这通电话有所感触吧。
张学良是11月21日到达萍乡的,住到12月16日,一共25天。
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在此期间的日记:
11月24日:“萍乡有一大成图书馆,小有规模,图书馆管理人告知萍北杨岐山有刘禹锡之墓碑,现尚完好。”
11月27日:“昨有一现教先生告余三侯庙有一位阳兑先生,能知咎,我们步行十余里至大田村的三侯庙来访问这位阳(欧阳也)先生,知他是一斋公,在此一方,有点势力,他不在家,余等空返。”
11月30日:“绛园左邻有一位黄道腴先生,为一大学教授,往拜访,谈甚洽。黄先生告余甘卓垒故址,下午同刘、许等去芦溪镇(距萍约五十里),谒甘卓庙,登甘卓垒。”
12月4日:“同刘、许等乘自行车赴安源,行约十五里抵矿区,遇该矿工程师张某,系营口人,比国留学生,导余等入矿洞参观,归来已黄昏。”
12月8日:“游星子石。”
12月10日:“乘自行车游洞口泉,约二十余里,洞深大,可容千人,归来已夜八点矣。”
12月11日:“早访黄先生访问古迹,彼言在东区有一禅台,驱车游之,无可观游处。”
12月12日:“同凤至、步先生大家游星子石野餐。”
25天之内,张学良安排了9次活动,凭吊名胜古迹、访问遗老乡贤,其中11月30日一天安排了两个活动。他要去哪里,刘乙光、许建业就得跟着他去哪里。
12月17日,张学良移至宜春,后又至湖南郴州苏仙岭、刘乙光的家乡湖南永兴等地,在此期间,依然优哉游哉。我们再来看张从1938年元旦到3月3日这两个月中的日记:
1月1日:“中午下山,再乘汽车至下湄桥(距县城约四公里),步行约一里多至温泉口,有一甚好温泉,池甚大可游,有谭祖峦石刻。”
1月2日:“下山,拜访此地士绅陈九韶,访问乡胜,彼告以将军石穿窍为一大洞,桥行可通行,万华岩、陷池塘等。”
1月3日:“下山游陷池塘,附近有一温泉,此地甚好,余甚喜之。”
1月8日:“游将军石,无甚可游观,下山去温泉口。”
1月9日:“游白鹿洞,观宋代三绝碑。”
1月10日:“游万华岩,早六点下山,改乘汽车行约十数里,改乘轿子,行约三十里,抵万华岩,洞大干燥平宽,内有小河流出,叹为奇观,在安和圩午餐,归来已四点多了。”
1月12日:“下山赴温泉洗澡。”
2月20日:“同刘(指刘乙光)、童等参观儒林煤矿,为一土作矿场,完全用人力,黑暗痛苦。”
2月21日:“至永兴县城,渡便江,游观音岩,参观宝兴煤矿,为一机作矿场。”
2月22日:“游白马仙,在庙中午餐。”
2月23日:“乘车至来阳,遇雨未游而返。”
2月24日:“至永兴乘船到上游里许,登鸡公山有一小庙,在该地野餐。”
2月25日:“至永兴乘船行约六十里到大河滩午餐,由陆路乘轿返(约五十里),返家已灯火矣。”
2月26日:“至车田看土作铁锅制造过程。”
2月28日:“谒衡阳船山书院,中途遇空袭,暂避警报一次。船山书院,在湘江中,为彭刚直创建。王船山故里之船山在距衡阳卅里处。”
3月3日:“至相(湘)阴渡,曾泅水一小时,又开车至风渡巡玩一周。”
两个月之内,张学良又是安排了16次外出活动,2月25日,为了一顿野餐,能坐船行60里地,再坐轿子50里路回来,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从活动内容上看,张学良的视野大大拓宽,不光把目光盯在名胜古迹上了,增加了大量访贫问苦的时间,不仅慨叹煤矿苦力的“黑暗痛苦”,而且连乡下“土作铁锅”的制作过程,张学良都看得津津有味。
大家会注意到,从一月下旬到2月上旬,没有张外出的记录。这是因为在1月22日,于凤至病了,第二天张学良本人也病了,发烧。刘乙光派人去衡阳给他们请医生,1月25日,张学良说:“来两医生,注射一针,吃些药。”次日,张又说“余病见好。”
这是抗战初期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后期的情况:
1946年9月21日,被监禁在贵州桐梓的张学良说:“刘队长告知,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去渝请示一切。”
10月1日:“因将离去,老刘言可外出一游。同Edith(赵四)、刘氏夫妇孩子们,先到兵工厂之大山洞,再到兵工厂的招待所午餐,游桐南十六公里处之红花园,什么也没有,一个小村子,游元田坝,风(峰)岩洞,风(峰)岩洞倒不坏。”
10月15日:“自从得知要搬家,将近一月,昨日汽车才来。早四点廿分由桐梓出发,约十点在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渝郊外之松林坡。”
按:松林坡即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抗战期间,戴笠在这里为蒋介石修建了一座秘密别墅,但老蒋基本没有来过。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而死,保密局将这里改为“戴公祠”,祭祀戴笠。不知张学良看到他这位昔日把兄的牌位,心中作何感想。
松林坡是张学良在大陆幽禁时期的最后一站,1946年11月2日,张被转移到台湾,次日入住新竹井上温泉。
以上都是张学良自己说的,根据这些情况看,如果硬要说张处在“虐待”之中,恐怕与事实(最起码是大部分的事实)是不沾边的。
我们再来看张学良的生活用度。
前面说了,幽禁中的张学良,旅游是常事,不仅在溪口如此,转移途中,依然轻裘缓带、好整以暇,十分潇洒。
旅游就要吃饭,因此野餐的机会也很多。据邱秀虎回忆:“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傅学文与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天,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去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
前面所引的张学良日记,也能看出,野餐的记载相当的多。
生活条件最好的,要说是在溪口的时候。邱秀虎说:“在溪口时,张将军每天起床后,都要叫人抬一张椅子放在露天走廊,他坐下来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有时是赵四小姐与他同吃,有时是四小姐送到房间里去给他吃。他喜欢吃火腿蛋、牛奶、花旗桔子。”
这是早餐,再看正餐:“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明天吃什么菜,他说了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的约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他喜欢的是花旗桔子、美国苹果,其他好的新鲜水果也喜欢,还喜欢可口可乐汽水。”
邱秀虎说:“他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平时他很少喝酒,也很少吸烟。有时在饭后,只偶然吸烟,但吸半支就不吸了。”
张学良很注意保养身体,邱秀虎说:“他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当按摩医生。”
关于物资供应,主要是特务队去采购,邱秀虎说:“我们每个礼拜都要去宁波购买他吃的海味、水果等食品。花旗桔子,宁波有时买不到,就买点外国水果罐头。”
再就是朋友们送,据邱秀虎说,宋子文曾给他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
据张毅夫回忆,1946年11月,郑介民让他去看望张学良,当时,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
对于穿着,张学良不太讲究,邱秀虎说:“春秋天他很少穿上装,都只是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衣,下装常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穿一件茄克。夏天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下喜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穿长绸丝棉袍,戴鸭舌帽。在当时,有许多人来看他,我从未见他穿过整整齐齐的一套西服或中山装来接待客人。”
特务们刚到溪口的时候,需要集体定做便装,但溪口没有服装店。于是副官应汉民就找到宁波的利康西服店,让老板每周带着衣料来一次,给特务们量体裁衣。由于他常来,就知道张学良住在溪口。“所以每次来的时候,总要拿些高级的西服衣料样本给张看,张都未理。只有一次,张做了一条花呢的长灯笼裤,价约十七八元。”后来张说:“那个西服店老板总想做我的生意,我衣服很多,我也不穿西服了,做一条跑裤算了!”
由于家当太多,到张学良离开奉化的时候,蒋介石的外甥、宁波市警察局长俞济民派了八辆卡车载运人员物资,浙江省保安处派了两个排在前面开路,再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小车。一共十辆车离开溪口,浩浩荡荡前往黄山。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物资日趋匮乏,供应困难;加以不断迁徙,跑跑颠颠,张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这也是事实。邱秀虎就说:“在沅陵时,军统局对张的生活待遇已经逐步下降,远远不如从前。他的心情更加苦闷,只有借钓鱼来消磨岁月。”
1938年底,张学良被迁到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后来又到贵阳、开阳、息烽等地,这是他在大陆幽禁时期条件最差的一个阶段,也是他心情最坏的一个时期。
首先,是“管束”的措施越来越严格了。为保险起见,军统局派特务王崇武当了修文县的县长,又派邱秀虎为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后来邱被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由接许建业任特务队副队长的熊仲青接替邱任修文县保安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邱秀虎说:“从表面上看,我已离开了监视张学良的特务组织,其实这也是军统为了加强对张监视的一个掩人耳目的手法。因当时据报,在贵阳已有很多人都知道张在阳明洞,有的还准备借名赶场去修文看张学良。军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才调我到贵阳公开搞侦缉工作。我在贵阳的家,实际上就是修文特务组织的联络办事处,来人都住我这里,交换情报。如象在邮检中,查获写信来贵阳告诉张在修文的信件,便由我来调查在贵阳的收信人情况,向修文特务组织汇报。有重要事,我也到修文去。”
1942年2月,张学良转移到贵州省开阳县刘育乡,军统局又派特务李毓桢当开阳县县长,派刘育乡本地出身的特务王尧为刘育乡乡长。
会客也没那么自由了,在麒麟洞养病期间,戴笠看张学良实在闷得慌,于是派军委会运输统治局监察处贵阳分处处长龚少侠、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贵阳办事处少将主任吴仲谋,贵州缉私处处长郭墨涛,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等人来陪张聊天、打扑克,聊以解闷。
这些有机会见到张学良的客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军统特务。其他的人,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会见张学良,邱秀虎说:“在修文时,就连贵州保安处处长傅仲芳和贵州财政厅厅长周诒春要求去看张,军统局也不批准,因傅、周不是军统有关的人。”
1946年4月22日,张在日记中写:“本月十五日莫柳忱来寓探视,由处长李肖白陪同,带来家人及朋友信件多封跟亲友们赠送的甚多物品。莫在寓小住五日,谈话时李、刘常是在座。彼告余之东北人寄予我的热情,使我感激而惭愧,心中痛快而又难过,不觉眼泪流出。我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莫柳忱即我们前面说到过的东北元老莫德惠,经蒋同意来看张学良,并给他带来了亲友的信件。因机会难得,多少年没见过军统以外的人了,所以张“写好些信托他们带去”。
李肖白,军统著名的“湖南三李”之一,时任军委会特检处处长,是来监视莫、张会面的。
其次,这一时期,张学良精神上极其苦闷,只好以打麻将消遣,再就是看报。每当看到报载某某地又被日本占领了,张学良就会感慨地说:“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
无奈之下,张开始研究明史,多少年之后俨然大家。
1940年,已调任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的邱秀虎去看望张学良,“故人”相见,张很高兴,说:“邱秀虎,你在警察局,敲了多少竹杠呀!”
邱秀虎回忆,此时的张学良,“面容消瘦,头发脱落已成秃顶,显得很苍老,情绪也很坏。他常由警卫随行着去赶场,主要是买点食品。”
1943年,邱又到开阳去看张学良,此时的张精神更加颓唐,他对邱说:“在这里闷得发慌,无聊得很,只好养鸡,你看,我辛辛苦苦养了七八十只鸡,都是白色的广东良种,可惜害鸡瘟,一夜就死光了!”
1944年,张学良被转往贵州桐梓县,此时,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邱秀虎回忆:“据我所知,他带在身边的私人存款这么多年也花光了,后期去赶场,购买食品,也很简单了。身体已很衰弱,每天只是在湖边默默垂钓。”
在贵州监禁期间,张学良还生了一场急病。
那是1941年7月6日,张学良得了急性阑尾炎。刘乙光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张学良的生病及治疗,军统局是有详细的规定的,外科找谁、内科找谁,都安排了“可靠”的大夫,不能到外边随便看医生的。然而,看张学良的病势,刘乙光认为找这些大夫都不行,必须马上送贵阳,找大医院。
然而,张要离开修文,须打电报请示重庆军统局本部,一来一回,万一耽误了时间,人死了怎么办!
于是,刘只好去找自己原来的手下、贵州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长邱秀虎商量对策。经讨论,刘乙光决定去找当时的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向他备案,先把张送到贵阳再说。
吴鼎昌,1884年生,原籍浙江吴兴。吴本是银行家,曾先后任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董事长。1299年,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家银行成立四行储蓄会,吴鼎昌为主任(谢晋元死守的四行仓库,就是这四家银行联合出资在上海修建的仓库),后吴鼎昌成为财政官僚。抗战开始以后,吴任贵州主席。
吴鼎昌听了此事,知道非同小可,当即同意将张转送贵阳治疗。刘、邱又到贵阳医学院找到了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杨静波给张开刀。
邱秀虎回忆:“决定后,我们就把贵阳医院的后院全部包下来,把张从阳明洞送来,由贵州省会警察局局长夏松指定侦缉队便衣在医院附近放哨监视。
经检查,张学良的病已经十分严重,为了保险起见,当时杨静波只给他做了切开引流手术。术后,在张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他暂时移居贵阳麒麟洞。当年冬天,张的阑尾炎再次复发,刘又将杨静波大夫接到麒麟洞,为张学良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张才算度过一场大劫。
对于刘乙光担着干系送他到贵阳治病这件事,张学良一直心存感激,到晚年仍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