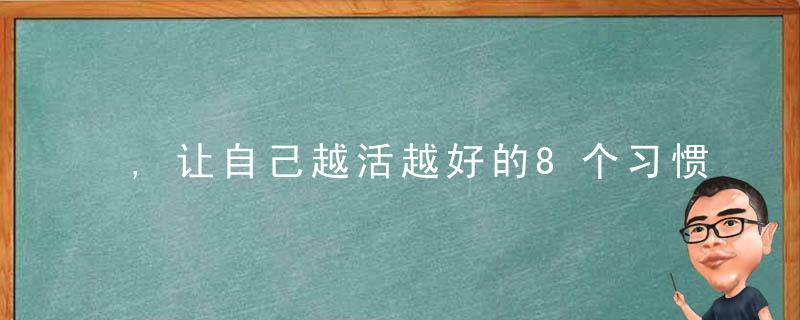织女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博士;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新世纪 底层文学与中国故事》,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 十月文学奖,现居北京。
织女
文丨李云雷
1
那时候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织布,我家里就有一台织布机,全是木制的,平常摆放在东屋里,要织布的时候才拾掇干净。我家主要是我姐姐织布,我记得那时候她坐在织布机上,双脚有节奏地踏着踏板,两只手飞快地投梭接梭,哐当哐当,伴随着踏板的声音,我们就开始盼望着,等她织好布,过年的时候就有新衣服穿了。我姐姐在村里有不少小姐妹,她织布,她们也织布,有时她们凑在一起,就会叽叽喳喳地议论着,看谁织的布好看,鲜亮,图案新,花纹美,她们相互品评一番,回去的时候都暗自憋足了劲,要织出更好看的花布。
在我姐姐的小姐妹中,芳枝和桂枝织的布总是别出心裁,村里人看了都说好,她们是一对姊妹,是我一家远房叔叔家里的,她们家在我们村西北的胡同里,离我家也比较远。她们俩经常到我家来,一来就扎到我姐姐的房间里,在那里说个不停,笑个不停,也不知道她们在说笑什么。那时候她俩大约都十七八岁,都长得很美,是我们村里的两朵花,不少小伙子都让媒人去她们里提亲,但是她们的父亲都不同意,说她们还小,等过两年再说。但是在村中,在地里,在街上,无论她们走到哪里,都会吸引来很多目光。那时候我还小,根本不懂,但我也很喜欢跟她们一起玩,有时她们来找我姐姐,也会给我带一些好吃的。我也跟我姐姐去过她们家,虽然是在一个村里,但那时我却觉得她们家很遥远,很偏僻,我跟着姐姐出了胡同,走上大路,过了村里的小学,在那里向西拐,在第二个胡同口再向北走,走过三四家人家,就到了她们家。她们家的门楼朝东,很高,全部是红砖砌成的,大门是铁皮包的木门,这在当时是我们村里的富裕户。进门是一堵迎门墙,墙上画着青山绿水,迎门墙和门楼之间,搭着葡萄架,正是夏天,上面爬满了绿油油的葡萄藤,半空中还悬垂着不少青色的葡萄,在风中摇摆着,很诱人。拐过迎门墙,北边是她们家的堂屋,西边是厢房,芳枝和桂枝就住在西厢房里。她们的门口栽种着一棵茂盛的柿子树,叶子很厚,很宽大,上面结的柿子快熟了,隐藏在叶底,像一个个小灯笼。
我姐姐一来,芳枝和桂枝都很高兴,她们又叽叽喳喳地聊了半天,桂枝还爬到树上为我摘下了一颗红柿子。这时我才知道,她们这一天不只是在一起玩,还要为织布配线,这可是织布的一道重要工序。后来我才知道,在织布之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先是要纺线,把一团团棉花纺成一个个线锤,那时候每天晚上吃完饭,我姐姐没事就坐在床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摇着纺车,一手抻着棉线,一边摇一边缠,慢慢地,一个鸽子形状的线锤就纺好了,在我姐姐纺线的时候,我就趴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有时候她也会问问我学校里的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纺完线就要染色,那要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配好染料,将线锤浸染好了,再一个个摆开,在太阳下晾晒,那些线锤好像各种颜色鲜亮的鸽子,红的,黄的,绿的,一个个流光溢彩,似乎要展翅飞上天空。染完色之后就要配线,要织成什么样的图案,先要将线搭配好,那时要在院子里扯开长长的线,按照花样一一安排好,这一头有人扯着线团,那一头有人将线一根根固定在织布机的档板上。配好线之后,将档板装在织布机上,这是织布的纬线,织布的时候,坐在织布机上,踏下脚板,用飞梭将经线来回穿插,每踏一下,就甩一次飞梭,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踩踏声,经纬相交,一丝丝,一寸寸,慢慢就织出一匹布来。
那天上午,她们要做的,就是配线。在芳枝家的院子里,我姐姐在堂屋门口固定住挡板,桂枝扯着长长的线向南走,走了大约四五米,在那里将线头固定在另一块挡板上,固定好一根,她再返回来,再将另一条线扯过来,系在挡板上。芳枝在边上看着,指挥着,让桂枝将哪条线放在哪个位置,在桂枝走来走去扯线的时候,她也走来走去,从前边后边,左边右边,从不同的角度看配线的效果,有时她会纠正桂枝扯错了的线,让她换一个位置,有时她还要看一看花布样子,跟我姐姐商量,“我觉得这条红线放在这里,会更好看。”有时她又说,“这根白线不能放在这里,冲淡了颜色”,我姐姐和桂枝就点头。她们三个人在那里说笑着,忙碌着,不时地打趣。
这个时候,我坐在柿子树下,有时也跑到她们身边,这儿看看,那儿瞅瞅,我姐姐怕我扯断了线,让我躲到一边乖乖坐着,桂枝又去给我摘了一个大柿子。我坐在那里捧着红柿子,看到在灿烂阳光的照耀下,长长的线抖一抖,半空中五彩缤纷的,颜色像是要跳了出来,芳枝和桂枝在彩线之中穿梭,就像两只飞来飞去的蝴蝶,又像在五线谱中跳跃的音符,那么明媚,那么美。
2
过了没有两年,我们村里就开始流行洋布了,的确良,卡其布,涤卡,腈纶,这些新的布料都是大机器织出来的,都是从外地运过来的,又轻,又薄,又软和,又好看,很受村里的女孩子喜欢,但是这样的布都很贵,只有城里的女孩才穿的起,我们村里也只有少数富裕人家的孩子才能穿,她们穿着这样的布料做成的新衣服,骑着自行车在村里驰过,姿态很轻盈,像要飞起来一样,总是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是啊,跟这样的布比起来,我们自己织的布显得又土又笨,又厚又重,剪裁成衣服又没有形,看上去不美,也不大方。我姐姐就很喜欢这样的洋布,虽然她也喜欢织布,不过现在,织布对她来说更像是单纯的劳动,而少了织出一布的喜悦。这个时候,我姐姐仍然常常和芳枝、桂枝在一起,但她们谈论的话题慢慢发生了变化,她们很少再谈怎么织出新花样或新图案,而是在说城里哪条街上可以买到好看的布,尤其是桂枝,她对好的布料很好奇,经常来家里叫上我姐姐,一起去赶集。
那个时候我们村里都很穷,很多人家刚刚能解决温饱,手里都没有多少钱,可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们村里的女孩子对美有了憧憬,她们看上了一块花布,总是要想办法买到手,然后裁成裙子、褂子或裤子,穿在自己身上。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女孩子也没有太多办法赚钱,她们都是自己多干一点活,攒上一点钱,再去买布,有时候为了买一块花布,她们要攒上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
我记得我姐姐那时候干过的活,有割草,采草药,编草辫子,等等。割草就是背一个大筐,到地里去割青草,割好满满一筐再背回来,然后摊开在阳光下暴晒,等草晒干了,再背到城里去卖,城里的畜牧局每年都会大量收购,为牲畜储备冬天的草料,一斤草才几分钱。草药可以卖的贵一点,但是更花时间,也是一阵阵的,有时候需要这种,有时候需要那种,那时候我也跟着姐姐去采草药,认识了不少药名,像马齿苋、满天星、夏枯草、紫苏叶、国槐籽等等,中药铺里还收蝉蜕,我们也常到树林里去寻觅,看到一个蝉蜕在树枝上较高的地方,我就像个猴子似的,三下两下爬上去,帮我姐姐摘下来。编草辫子主要是女孩子干的活,要细心,耐心,草辫子的原料就是麦秸秆,在我们那里麦收之后到处都是,编织之前要先选出长而白的麦秸秆,在水里浸湿之后再晒成半干,编织的时候,先把前端固定好,然后将麦秸秆分成三股,像编辫子一样,将这三股麦秸交叉编织在一起,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女孩都梳着辫子,编草辫子的方法,就跟她们编自己的辫子一样,所以她们做起来都很熟练,很手巧,她们坐在阳光透亮的树荫下,说笑着,打闹着,手指在麦秸秆上翻飞,草辫子便从她们的手底下长了出来。那些草辫子都会编的很长,一圈圈绕起来,绕成一大卷,她们就驮到城里去卖掉。那些草辫子可以做草帽,可以做草垫,也可以做成工艺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我姐姐和芳枝、桂枝卖掉草辫子,就可以买她们想要的花布了。她们做这些活,是在田间劳动之外做的,她们挣了钱,也就是自己的了,家里父母也不管,或者想管也管不了,我姐姐就是,挣了这些钱也不交给家里,就去买一块花布,或者给我买点好吃的,所以很多年之后,我爹还在说,我姐姐就是从那时候养成了乱花钱的毛病。
不过我姐姐她们那时候买的花布,或者新衣裳,确实很新颖,很漂亮,至少在当时我的感觉是如此,记得有一次我姐姐带我到芳枝和桂枝家里去,在她们住的厢房里,我姐姐和她俩在那里兴奋地谈论着,坐在她家的床上,我的手不小心触到了挂在床头的裙子,那好像是一件白纱裙,我感觉自己的手触摸到了窸窸窣窣的纱的质感,那还是第一次,带点响动,带点透明,又是那么鲜亮,那轻微的响声和沙沙的感觉让我很陌生,也很新奇,我忍不住用手去摩挲接触到的那一片纱。这时我姐姐看到了,连忙过来抓住我的手,“别乱摸,别摸脏了!”那一件裙子好像是桂枝的,她快步走过来,仔细查看了一下,见没有弄脏,才刮了一下我的鼻子,“坏小子,弄脏了小心我打你。”芳枝也走过来,将我从床上抱下来,边抱边说,“别那么大声,小心吓着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从此之后,那件沙沙响的裙子就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那略带摩擦感的真实触觉,三个姐姐的说笑,柿子树的碧绿叶子,下午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过来,窗格的影子在床上缓缓移动,又似乎永远停留在了那里。
为了买一件好看的衣服,我们村里的女孩还有更大胆的举动,那就是桂枝,她想买一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那是当时城里女孩最流行的穿着,那件衣服很贵,无论是割草,采草药,编草辫子,怎么攒钱也凑不够,连芳枝的加上,也还差得远。每次她去城里赶集,都要去百货商店看看那件衬衫还在不在,去了两次还在,她怕让别人买走了,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办法,最后她终于想出了个主意,就是把头上的辫子剪掉去卖。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女孩都留着辫子,长长的,又黑又亮,走在路上,大辫子一甩一甩的,很动人,我姐姐是这样,芳枝和桂枝也是这样。当桂枝说要铰掉辫子去卖时,我姐姐和桂枝都很吃惊,都劝她不要剪,那时候大辫子是我们村里女孩最重要的审美标志,要找对象或找婆家,对方都要看这个女孩的辫子长不长,黑不黑,亮不亮,只要有一条漂亮的大辫子,在我们乡村里,就不愁找到好婆家。桂枝的辫子本来很漂亮,但现在为了一件衣裳,她竟然要剪掉,的确出人意料之外。不过桂枝既然下定了决心,也不顾她们的劝阻,她一个人偷偷去赶了集,到理发店里剪了个短发,卖掉了辫子,又拿卖辫子的钱去买了那件衣服。那一天下午,她穿着那件红衬衫,骑着自行车,从城里回到我们村,一路上神采飞扬,很多人都看呆了。不少人纷纷摇头叹息,说她像个假小子,又说她没有了辫子,可怎么找婆家啊?也有不少人说她真时尚,真清爽,尤其是她竟敢剪掉辫子,真是大胆,这让我们村里很多女孩很羡慕,我姐姐就说,桂枝真是好样的,不少女孩子想剪又不敢剪,只有桂枝,说剪就去剪了!
3
芳枝和桂枝虽然是两姐妹,但她们的性格并不相同,这可能也跟她们的年龄有关,芳枝是姐姐,从小就要照顾妹妹,所以她很温柔,很有耐心,也很听家里大人的话,但桂枝就不一样了,她是家里的老小,小时候家里人都很照顾她,也很宠爱她,有什么好吃的都给她吃,有什么好玩的也都给她留着,所以她从小就很大胆,很任性,很活泼,走到哪里都是说说笑笑。她们姐妹两人的性格也很协调,一静一动,一阴一阳,就像开在枝头的两朵花,一朵平淡素雅,一朵热烈奔放。
芳枝不像桂枝那样喜欢新鲜,喜欢时髦,当我们村里很多女孩都开始穿的确良的时候,她还穿着家织的粗布,她也还在默默地织布,不知是她喜欢,还是为了家里的生计。那个时候我姐姐经常到她们家里去玩,有时候我放了学,就先不回家,直接到她们家里去找我姐姐。有一天傍晚放了学,我又到她们家里去,推开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我走进去,只听见咔—咔—踩踏织布机的声音。我顺着声音,来到她们的房间门口,发现没有别的人,只有芳枝一个人在。她坐在床边的织布机上,正在专心地织布,她的脚轻轻地一踩一踏,织布机就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她的双手灵活地飞梭、接梭,在织布机两侧翻飞着。此时我正好看到她的侧面,西边的阳光从窗口照过来,照在七彩的经线和纬线上,照在织布机上,也照在芳枝的身上,勾勒出了她美丽的身影,像闪着光,像镶上了一层金边,她的辫子随着铿锵的节奏一起一落,似乎要飞扬起来。我不知当时是否看呆了,但这个场景却长久地留在我脑海中,每当我想起桂枝,就会想起她坐在那里织布的情景。过了一会儿,芳枝才发现我,她啊地大叫了一声,捂着胸口说,“吓了我一跳,你这孩子,来了怎么也不说话?”我看着她,不知该说什么,她平静下来,才跟我说,“来找你姐吧?她刚走没多久”,又说,“先别走,我给你拿个柿子。”说着她从织布机上站起来,从筐子里拿出一个黄澄澄的柿子,塞到我手中。
那个时候,到芳枝和桂枝家里来提亲的媒人络绎不绝。我们村东边有个叫吴家村的村子,那个村里的春生也到他们家来提亲。春生长得高高壮壮,浓眉大眼,他在离我们这儿百十里地的一家煤矿区下井挖煤,在我们村里人看来是吃国粮的公家人,每一次回来,他都穿着白衬衫,黑皮鞋,拎着一个有香港字样的黑皮包,在当时很是时髦。春生家的媒人到芳枝家提亲,芳枝的父母都很高兴,觉得芳枝能嫁给一个公家人,以后就可以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去享福了,就答应了下来。那一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春生从煤矿回来,跟着媒人到芳枝家去跟女方见小面。所谓“见小面”,就是让青年男女双方见面,这是我们当地婚俗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见完“小面”之后双方满意,随后就是“见大面”——双方家长亲友见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订婚、下帖、结婚了。
但是在芳枝和春生见小面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简单地说,就是春生没有相中芳枝,反而看上了桂枝。我们都不知道,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也可以做一些猜想。从芳枝的个性来说,在亲事面前,她一定是羞涩的,她可能只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待着,不敢去看来向她提亲的人,即便是在母亲的催促下,她也只是最后才在堂屋出现一下,匆匆见一面,很快就又逃到自己的房间中去了。桂枝呢,桂枝没有什么负担,她活泼,又好奇,这个即将成为自己“姐夫”的人,在她眼中或许充满了神秘感,在那个晚上,她可能好几次装作去倒水,或者上菜,偷偷跑到堂屋里,去看这个叫春生的小伙子,看他的模样和他在陌生环境中的窘态,她可能还会偷偷跑到房间里,将他的可笑和可爱之处讲给芳枝,边讲边夸张地笑着,芳枝听了,害羞得红了脸,要去打她,她一闪身躲开,芳枝气的笑骂,“你这个死妮子,早晚你也会有这一天!”是的,看上去一切都很自然,但是在春生心里却发生了变化,春生并不知道自己要见的姑娘是什么样,芳枝惊鸿一瞥似的出现,或许并没有在他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桂枝,这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她假小子式的短发,她时髦大胆的衣裳,在那个夜晚,或许深深打动了他的心。所以在这次见小面之后,他就向父母和媒人提出,他相中的姑娘不是芳枝,而是桂枝。
这样一个事情,对芳枝、桂枝和她们家里来说,都是很难堪,也很难办的,尤其对芳枝来说,是很大的心灵伤害。但是怎么说呢,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乡村来说,也并不少见。那个时候,我们乡村里很重视婚丧嫁娶,但也有不少变通的途径,“姊妹易嫁”的事情也并非没有,比如姐姐去世了,妹妹嫁给“姐夫”,这样还可以更好地照顾姐姐留下的孩子,再比如男女双方相亲,男的长得不好看,就让同族中长得体面的兄弟代他去相亲,女孩相中了这个小伙子,嫁过来才发现嫁的是另一个人,等等,类似这样的事情也很多。在这样的情况下,芳枝的父母或许也觉得,春生相中芳枝还是桂枝,并没有多么大的差异,他的条件好,也有选择的余地,喜欢桂枝就桂枝吧,要是一开始说给她就好了。桂枝呢?桂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本来是给姐姐相亲,怎么相成了自己?最初她是惊愕,后来再细想一下,觉得春生这小伙子自己也是喜欢的,要眉眼有眉眼,要模样有模样,要跟他成亲也很好,只是担心芳枝会生气,会别扭。芳枝呢?芳枝的心里当然很别扭,很堵得慌,这是怎么回事?本来是自己相亲的,没相中自己也就算了,这也是相亲中常有的事,现在不但没相中自己,反而相中了妹妹,这算什么事呢?是自己比妹妹差吗?是自己哪里不好吗?她的心中又委屈,又难受,又难堪。这个时候媒人就出场了,我们那里的媒人,一个个都是能说会道的,也能猜中别人心里想的事,他说,怪我这个媒人没有当好,事先沟通不够,就乱点鸳鸯谱,但这也是一种缘分,不打不相识,人家春生也说了,芳枝姑娘好是很好,什么地方都没挑儿的,但怎么说呢,他更喜欢桂枝这个类型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强扭的瓜也不甜,我们就顺其自然吧,都是自家人,咱也别见外。咱芳枝这么好的姑娘,谁看不上才瞎了眼,咱再找一个更好的,这个就包在我身上了……,媒人这样几次三番说下来,渐渐弥合了一个家庭的伤痕,也促成了春生与桂枝的婚事。第二年春天,他们就结婚了,桂枝嫁到了吴家村,过了一两年,她作为家属,也跟着春生去了矿区,从此远离了我们村。那时候我们村里人都很倔,很犟,我们对一个人最生气的表现就是不再与他交往,不再与他说话,用我们那里的话说就是“不搭腔”,我们村里人后来才注意到,从相亲那一天晚上开始,芳枝就跟桂枝不搭腔了,再也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
芳枝是姐姐,桂枝比她小,结婚反而在她前面,这在我们村里也并不多见,但风平浪静之后,似乎也并没有什么。现在她们共有的房间,成了芳枝一个人的房间,没什么事的时候,她就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咔——咔——,踩着踏板,双手在五彩丝线中穿梭,时间也在织布机的响声中慢慢流逝。芳枝坐在那里,表情很平静,我们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或许她什么都没想。
4
现在,我们村里早就没有人织布了,我家里的织布机先是放在东屋,后来觉得它太占地方,挪到了西边的草棚中,风吹雨淋,慢慢就朽坏了。我们村里当年有那么多织布机,现在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村里的女孩子再也不织布了,她们穿的都是城市里流行的时装,她们喜欢到城市里去打工,一个一个都走了,平常村里看不到年轻人,一到过年的时候,她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各种时装,就回来了。春节一过,她们又像候鸟一样飞走了,我们村里再也没有以前热闹了。我也是常年在外漂泊,很少回家,但每一次回家,都能感受到浓厚的情感,我时常感觉到,我们村里人和城里人不同,城里的人今天爱,明天恨,变幻不定,很脆弱,但我们村里人的情感是稳定的,爱恨都是一辈子,有的甚至会传到后辈,世代交好,或者父仇子报,只是这样的情感太沉重,浓烈,执著,我也有点不适应了。
我姐姐告诉我,我们村现在还有一台织布机,就是芳枝家里的,现在芳枝还在织布。她又说,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大家都想穿的确良、腈纶、涤卡,嫌自己织的布又土又笨,现在反过来了,我们家织的土布又成了好东西,想想也是,我们织的布是纯棉的,棉花是自己种的,纯绿色,又是纯手工,穿上去又透气又暖和,比起大机器织的化纤品好多了,只是现在村里的女孩子都不会织布了,会织布的都老了。
那一年,桂枝离婚后,带着女儿回到我们村,那时她在城里生活已经很久了,衣着打扮很光鲜,很亮丽,在那之前,桂枝有好多年没有回来了,可我们村里人不断能听到她的消息,我们听说,春生在煤矿里干得很好,成了矿区的干部,桂枝和孩子的户口也都转正,成了吃国粮的人。我们又听说,桂枝和春生离开了煤矿,春生在做买卖,做得很大,桂枝在城里买了大房子,也不用上班了,就在家照顾孩子。我们还知道,桂枝的父母去世的时候,桂枝没有回来,听说那时她正在国外陪孩子读书。但是我们村里人也发现,当我们热心地谈论桂枝的时候,芳枝却从来不说什么,有人在她面前提起桂枝,她也不说话,只是转过身,默默地就走了。
那一天,桂枝开车来到我们村,等她下车时,我们村里人都没有认出她来,她将车子开到老家的胡同口,先下来的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孩,再下来的是一个戴着墨镜的城市女人,她们牵着手向前走,在芳枝家门口停下来。芳枝家的房子还是老宅子,父母去世后,村里将这块宅基地给了芳枝,她也没有再翻新,这座房子还是原来的样子,迎门墙依旧,葡萄藤依旧,只是那棵柿子树更加茁壮茂盛了。
桂枝一进家门,就听到了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响声,她拉着女儿的手,循着声音悄悄地走到院子里,转过迎门墙,走到厢房门口。在那棵柿子树下,她看到芳枝仍像多年以前一样,静静地坐在那里织布,她的双手甩着梭子,灵活地翻飞着,双脚轮流踩着踏板,卡—卡—的声音很清脆。小女孩看着好奇,刚要开口说话,桂枝用一个手势阻止了她。桂枝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芳枝织布,泪水慢慢从墨镜边缘沁了出来。她终于跨进了门槛,冲着芳枝的背影喊了一声,“姐,我回来了。”她看到芳枝的背影一下子停住,愣在了那里,但是,芳枝并没有转过脸来,她只是怔了一下,脚底又慢慢发出了卡—卡—的声音。
桂枝走到织布机旁,摘下墨镜,对着芳枝的背影说,“姐,我回来了。我知道你恼着我,我也很后悔”,说着她轻声哭了起来,“现在我才知道,春生不是好东西,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芳枝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桂枝继续说,“姐,我知道你恨着我,咱爹娘生病去世时,我在国外,不能赶回来。可是现在,姐,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了,只有你,你不能不理我……”
芳枝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桂枝又说,“姐,我知道你喜欢织布,我做梦都梦到我们在一起织布,那时候我们多好啊……,现在我想回到村里,盖一个织布厂,我们一起织布,你看好不好?……”
芳枝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桂枝又说,“姐,这是我女儿,你外甥女儿,是咱下一辈的,你恼我可以,别恼孩子好不好?”说着她拉过女儿,“这是你姨,快喊姨。”她女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惊恐地看看她,又看看坐在织布机上的芳枝,轻轻地喊了一声。
芳枝坐在那里,还是一动不动。
桂枝默默地看了她一会儿,又默默地走了出来。
桂枝站在柿子树下,抬头看了看那棵柿子树,这是夏天,柿子树的叶子宽大,肥厚,像只只绿色的手掌,柿子还是青色的,隐藏在枝叶的后面,轻轻地摇摆着,闪动着。桂枝叹了一口气,扯起女儿的手,一步步走出了家门,走出了胡同,在她身后,又响起了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声音。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桂枝戴上墨镜,拉着女儿的手,穿过长长的胡同,回到她的车里,慢慢离开了我们村。
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村里人就听说了桂枝病故的消息,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什么病,现在城市里怪病那么多,村里人都叫不上名字。但也有人说,夏天她回家时就已经生病了,她回家来,就是想和芳枝和解,想在家中寻找安慰和解脱,但是芳枝的态度,却伤透了她的心,可能也加重了她的病情。谈起这件事,我们村里人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纷纷摇头叹息。
那一年冬天,芳枝也生病了,她在我们县医院住了很久,才回到家。回到家里,芳枝把织布机拾掇干净,就开始织布了。她仍然在以前的那间闺房里织布,先是纺线,染色,配色,再就是织布,门口那棵柿子树又听到了织布机咔嚓咔嚓的响声。那一天,她在织布机上呆坐了很久,看日影从东到西慢慢转过去,她仿佛看到了桂枝在家的日子,又一次听到了她的脚步声,说笑声,耳语声,她的泪水无声地打湿了织布机上的五彩丝线。坐了不知有多久,芳枝又开始织布,她安静地坐在那里,脚踩着踏板,双手如飞梭一般翻飞,那匹布一丝丝增长,一丝丝延长,仿佛将她萦绕的思绪都编织在了一起。偶尔她会抬起头来,看看窗外柿子树散落一地的树影,在那一刻,她好像在等待什么。雪落下来,高高悬挂在枝头红灯笼一样的柿子,一点点白了,但又像扑不灭的火焰,静静地燃烧。
——完——
——本文摘自李云雷小说集《再见,牛魔王》(作家出版社,2017)
本期责编:Sa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