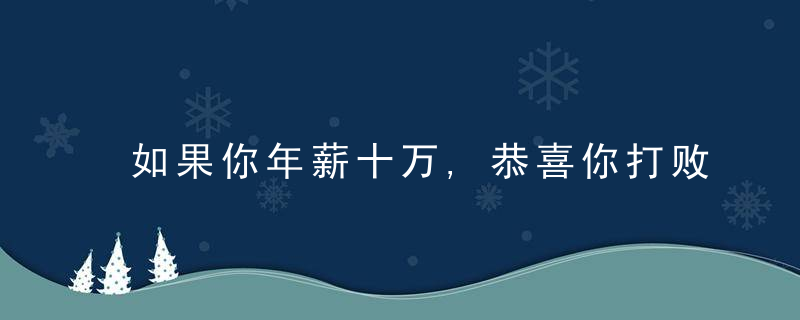博士春节返乡:老家仍保留客人来了女人不上桌习惯

我爱我的故乡,可女儿出生以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讲述我的故乡。
因为我只知道一半故乡,一半男人的故乡。
我的女儿教会我另一半故乡。
我与故乡有两次断裂:一次是少小离乡,跟随父母来到城市,后来因为求学、工作,辗转济南、沈阳、焦作、北京、温哥华,可谓地理上的离乡。一次是女儿出生,从此她便无缘家谱、族谱,被排除在村庄的公共事务之外,又让我有了心灵上的离乡。曾幻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我,第一次对故乡有了精神上的反叛。
我的故乡在山东聊城西边的一个小村。今年因为“博士返乡”的社会调查项目,我重新回到这里,想为家乡的发展尽些绵薄之力。
但我不知道,在城市出生的女儿,会如何遭遇我的故乡。在她出生以后,我开始试着寻找我不知道的另一半故乡。
当然在饭桌上是找不到的。
我的家乡也算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但吃饭不仅要分清座次,长幼尊卑一目了然,而且至今保留着来了客人,女人不上桌的习惯。
回乡聚会,大都是一群男人抽烟喝酒。以过年时聚餐为例,男人吃饭多在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辈分高且年长者坐在正对门的位置,辈分低且年轻者坐在两侧或背对门的位置,至于女人们,遑论辈分和年龄,只能坐在厨房或者卧室等其他地方。
如今,很多村民已在附近的城市安家立业,如果父母也随其进城或者离世,那么大年初一回村拜年的大都只有男人,而把女人和孩子留在城里的家,这让我出生的村庄更像是男人的村庄。
儿时的我也是不能上酒桌的,因此可以穿梭玩耍于偏房与厨房之间。那个时候,村里不管谁家来了客人,都是女人在厨房忙碌备饭,男人在堂屋喝酒聊天,小孩在院里摸爬滚打。女人和孩子只能等到男人们吃完,才可以吃剩下来的残羹冷炙。正因如此,在物质比较拮据的年代,讲究的男人形成了吃饭不光盘的“礼仪”,例如吃鱼不翻鱼,留下另一半给妇女和孩子吃。
吃到另一半鱼,对于儿时的我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因为桌上的男人们喝酒,一喝就要喝上几个小时,中午一般从十一点喝到下午三四点,晚上则从六七点喝到凌晨十二点,有时候两场连上了,就喝一整天。喝酒时烟雾缭绕,散场后满地狼藉,一桌人酩酊大醉。饭菜里会混杂着烟酒味,是我儿时抹不去的记忆。
喝醉酒的男人,好的闷头睡觉,没德行的会对女人吆五喝六,甚至大打出手。女人则要刷盘洗碗,打扫满地的烟头和骨头,收拾男人的呕吐物。乡间舆论不齿于喝酒就打骂女人的男人,但也容不下能当男人家的女人,否则会成为街头巷议的笑柄。
我的父亲属于喝醉后仍讲礼仪的男人,祖母在世的时候,每年正月初三到正月十五,家里始终会有来看望她老人家的亲戚,父亲会一直陪客人喝酒吃饭,而母亲则在厨房独自忙碌。客人走后,母亲会用谩骂和埋怨来表达不满,不过另一波客人到来时,她会钻进厨房,再次忙碌起来,母亲害怕让父亲背上“不当家”的恶名。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和父亲再次回到家乡,留下母亲和我的妻女在城市时,我才理解母亲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女人们,在一群男人烂醉如泥的背后,她们对过年、春节,一定有着不同的记忆。
除了主妇们,对于故乡的很多女孩来讲,她们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着“大门不出,二门不入”以及“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串亲拜年喝酒几乎看不到她们的身影,一直等到结婚出嫁,她们才会以主妇的身份,出现在乡村的社交场合。
最近几年,农村逐渐丰饶,女人和孩子终于不用等男人吃剩的那一半鱼,而是可以和男人同时开饭了,只是她们仍大多摆张桌在厨房或偏房,并以极大的耐心等待男人的酒席散场。
大年初一,我走了几户人家,听到、看到、记录下的,仍是男人喝醉后的村庄。
我可以在墙上找到另一半故乡。
那是墙上到处都可看到的“关爱女孩,就是关爱民族未来”、“生男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的宣传标语。
标语背后是多年性别平等教育一直努力改变的现实状况:女儿尚在产房,门外一户人家添了男孩,大家都会围上来说“恭喜、恭喜”,而当得知我添了女孩时,围上来的人们则会宽慰道“男女都一样”。
在故乡,男丁意味着家族的兴旺。一般35岁至45岁的村中男主人,大都至少有一个男孩,即使在计划生育最严格的时代,也鲜有独生女的情况。年龄再大一些的村民,即便已经生了五六个女孩,也要一直生下去,直到最终得到一个男孩为止。一些家庭因为超生被罚的所剩无几,有的为了躲避计生体检,甚至远避他乡。
在家乡,像我这样只有一个独生女儿的人,几乎找不到,比我的博士帽还稀缺。
故乡酒桌上,我经常可以听到很多“能人”的故事,只是这些能人都是男人,没有女人。有些家族谱记录了一些嫁到本村的女人,而忘记了在本村出生和长大的女人,因此,我的女儿无论有何种成就,都似乎和这个村庄没有关系了。
几年前,我热衷于整理家谱族谱,现在想到这种某位名人的几十几代孙到我这里即将终结时,这种热心便所剩无几,更何况我的祖上并非某位名人。我写了村庄很多男人的故事,但却没有女人的故事。
如今,故乡的很多仪式因为年轻人进城而越来越简化,只有葬俗仪式还保留着一家一户摊派一个男丁的传统,如果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则意味着以后无人接替户主人,参加这种仪式的“互助”。
一次聊天,村里一位上了高中的女孩拿出自己的日记,她这样回忆参加祖父的葬礼:“跪在棺材边上哭了几天,我已经哭不出来了,但是还得像所有人那样,拿一片手绢遮住眼睛……大家只看到一群不怎么上门的亲戚卖力的表演他们的悲痛,却不去关心这个即将埋在黄土中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而另一些刚嫁入村中的女性也并不轻松,其中一位在聊天时说,她每次都从胡同进村,从来不敢走村中大街。村中的大街、桥口公共领域往往被打牌的男性所占据,偶尔年长的女性凑足了人数,才会在大街口聊一会儿天。
可女儿出生以后,很多热心的村民向我表示了同情。因为我如果以后不要男孩的话,则将被归入“绝户”的行列。在故乡,这个词并不只是指没有子女的人,还专指没有儿子的人。酒桌上,有人说起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娶“老绝户头”的女儿,怕儿子以后面临养老压力。
在乡村,女孩长大出嫁换回一笔彩礼后,在舆论上便没有了太多的养老责任,老人还是秉持着“养儿防老”的理念,一直住在儿子家里。很多老人把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产都提前分给儿子。也有老人按孙辈处分财产,弟兄两个,一个有儿子,一个有女儿,他们的父母会立下遗嘱,把财产分给有儿子的那个儿子。
一些老人讲究落叶归根,魂归乡里,但是女儿出嫁终究要离开村庄,而她们的父母则担心,一旦跟随女儿到异乡,则有可能再也回不到故乡。只是现在值得“安慰”的是,很多男孩也离开了故乡,留下一个只有老人的村庄,而随着这些老人故去,整个故乡也故去了,那些在堂屋喝打酒的男人和那些躲在厨房和偏房的女人都会只成回忆……
我爱我的故乡,可女儿出生以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向她讲述我的故乡。
因为我只知道一半故乡。
我的女儿教会我另一半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