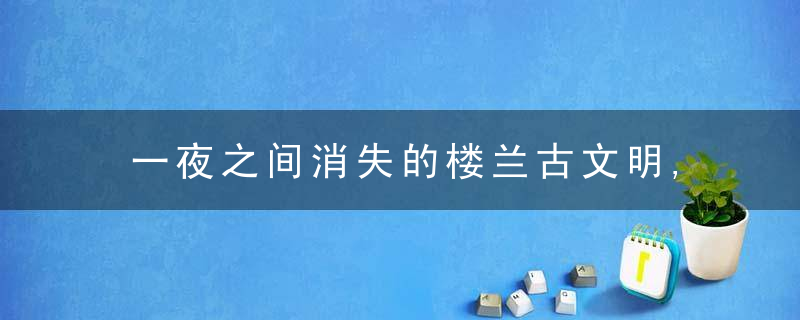郭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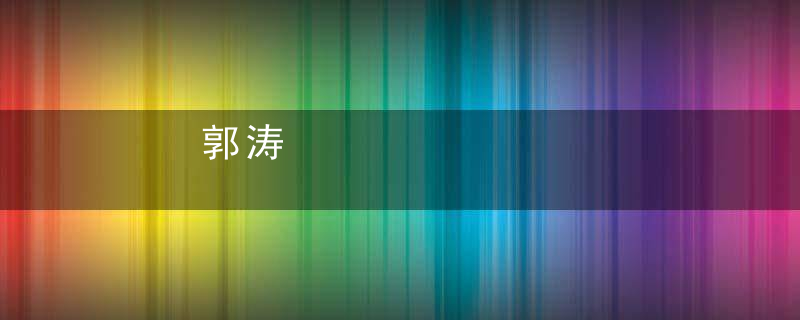
史学月刊
三
从国野到里落:早期的聚落形态与空间分野
透过文献我们知道,“里”“落”都有普遍居住地之义,作为单个聚落形体位于居住空间的中层,介于个别居住体“家”“屋”与群组聚落体“乡”“聚”之间,它们是否代表了秦汉时期基层聚落形态的两种类型呢?
“里”义与内、中同,与外相对,《广雅·释言》:“内,里也。”引申为内向集聚。“落”则有散落之义,引申为外向分散。《史记·汲郑列传》记:“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洁。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索隐》解释道:“落犹零落,谓散也。”参照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族群生态的观察,“落”也有明显的分散性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国,东接交阯,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各立君长,其人皆椎结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诸落。”西南夷地区聚、落分立,区别较为清楚,“聚”内人群从事定居农业,有城邑,置君长,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相对社会化,与中原地区差别较小。《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巂、昆明“诸落”的生活方式有更为详细的描述,记载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所记内容基本相同。只是《后汉书》中明确称“巂”“昆明”等为“诸落”。少数族群地区巂、昆明等“诸落”内的人群“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居,无君长”,即从事迁徙的游牧业,组织形态和生活方式相对原始,其领地也相对开阔。对边疆地区族群和地理景观的观察,都是以中原人的生活方式和汉地的组织形态为参照,虽然汉地的“落”与边疆地区的“诸落”“部落”(马王堆《地形图》中有“君”和“部”等组织)等有别,但“落”意指分散、零落和相对自然、原始的组织方式当是共通的。
目前考古发现的农村聚落遗址,就地域环境、经济文化面貌而言,可以分为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类型;而在农业文化聚落遗址内部又可明显看出聚落形态上分散与聚集的差异。以辽阳三道壕遗址、河南遂平小寨遗址、河南内黄三杨庄村落遗址为例,这三处农业文化类型聚落遗址,包含多个房屋居住体的同时又以单一聚落的形式存在,聚落层级上较为基础。三道壕遗址和三杨庄遗址的相同点较多:均地处河流冲积平原地带;农业及副业生产性质突出,且生产、生活空间紧邻;整体布局较为分散、无规律,房屋被分隔,排列无次序,各户较为独立,这两处遗址可以归于一类。三杨庄遗址是“宅在田中,田中建宅”,农业生产特征突出;三道壕遗址主要生产形式为烧窑,故其居址间隔着窑址,这与前揭池田雄一分析的《管子》中两种类型的“落”相似。而遂平小寨遗址更多呈现密集、有规律的格局,户与户之间显露出密切的关系,其水井和街道有一定的规划,体现出较强的公共性和内部联系;同时,其农业生产遗迹并不显著,以集中居住的生活遗迹为主。遂平小寨遗址当属于另一类。它所体现的特征与文献所记“里”的形态颇为对应。根据出土文献,“里”的布局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形制规整,内部布局较为集中。放马滩秦简《法律答问》(简186)记载:“越里中之与它里界者,垣为‘完(院)’不为?巷相直为‘院’;宇相直者不为‘院’。”可知“里”的具体规划情形为:“里”有里门和围墙,连通并分隔内外;“里”中各住户相连或间隔较小,户之间有墙垣;“里”中道路交错、街巷纵横,各家住屋周围还有院子。四川画像砖中汉代“街市”的图景,关于曲阜“阙里”的文献记录———“南北一百二十步,东西六十步,四门各有石阃”以及边塞屯垦区因屯戍移民而形成的经过规划的“第一里”“第二里”等,都可以看出“里”经过了较齐一的规划的特征。另外,一般认为农田在里之外,里门和由若干里构成的聚落之邑门,将聚落内部和广阔的田地分隔开。即住宅与田地的空间格局是分开的,田地在里门之外。这种居住空间与农业生产空间分隔的格局,也与秦汉时期“乡里”与“田部”相分离的特点吻合。其时,行政管理上分设两套机构,里的管理属于乡部,而田的管理属于田部。邑中道与邑中舍,田道与田舍,也分别由乡部和田啬夫管辖。故而,无论是从聚落形态上分散与聚集的平面展布方式,还是从生产与生活空间的联系程度来看,两类由个别居住体组成的农村聚落遗址与文献中的“里”“落”都存在很紧密的对应关系。
古代聚落形态中的“集村”和“散村”是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提出著名的“都市国家论”观点,而“都市国家”的先决条件是高度发达的“集村型”聚落形态。他所依据的主要是正史资料。但是众所周知,以正史为代表的文献所揭示的内容倾向于国家及地方行政能有效管控的地带,由此而呈现的聚落形态自然也以规范化、标准化的“集村型聚落”为主体。近年来,通过对文献的深入解读,尤其是新出史料以及考古遗址的研究,针对“都市国家论”的挑战日益增多,对“集村型聚落”形态的说法时有补充,“散村型聚落”的广泛存在逐渐得到认同。以上据我们的分析,秦汉时期的农村聚落遗址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分别可以与文献中的“里”和“落”相对应,两类遗址的最大区别在于分布格局上的集聚与分散。以往认为“秦汉时期居民普遍居住在围墙包裹的城及里内”的流行观点也需要重新考虑,因为据秦汉时期聚落遗址可知,在居住形态上,居民不一定都是居住在乡里城邑之内,乡里之外农田、窑址等生产区周围也有大量散居现象存在,这类聚落形体的分散性特征更为显著。
此外,在出土文献中还可以看到一些乡里之外的地名,这些地名背后的聚落实体也可能属于“散村”类型。在反映墓主人生前公私活动的秦汉“质日”简中有一些此类地名,如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质日》中有一段记载:
正月丁卯(1),嘉平视事。
丁亥(21),史除不坐掾曹。从公,宿长道。
戊子(22),宿迣赢邑北上蒲。
己丑(23),宿迣离涌西。
庚寅(24),宿迣□□(离涌?)邮北。
辛卯(25),宿迣罗涌西。
壬辰(26),宿迣离涌东。
癸巳(27),宿区邑。
甲午(28),宿竟陵。
乙未(29),宿寻平。
其中的“宿迣赢邑北上蒲”“宿迣离涌西”“宿迣□□邮北”“宿迣罗涌西”“宿迣离涌东”的具体地望难以考索,但可以基本明确的是,这些复合地名中“赢邑”为乡聚类组织,“北上蒲”属乡下组织,涌西、涌东等是河流旁的聚落,地望均在今江汉平原腹地。由地理环境来看,这些地名的组织形态当与城内的“里”有所不同;而由“宿”可知,它们同时也是居住空间,代表了聚落实体。无独有偶,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按:其定名也应改为“质日”)有“宿羽北一”,“羽”指羽山,“北一”当为羽山之北的聚落名。“北上蒲”“涌东”“涌西”“羽北一”这些都应当属于散居的聚落,基本上以地理方位和地形地貌命名,另如“三屋落”以聚落构成形态命名,不同于“里”多以嘉名、地理位置、数字、取自他县名等的命名方式。
在同一地区往往并存着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聚落,如放马滩地图(2号木板地图)中除了“乍格”之外,亦见“舆里”“杨里”等里名,所不同的是“乍格”偏处于河流上游,行政建制稀疏,但与“中田”“南田”“东田”临近,清晰地展示了田、落关系;且“乍格”与山、谷、谿类地名一样不以方格框定,这与“田”“里”等以方格框定标示具有明确赋役、户口管理的行政意义有别。“里”的自然地理条件则相对较好,位于河流下游开阔地带,临近县治,行政建制密集。当然,安陆地区的行政建制自然不仅限于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所记亭、落、城,其乡里建制亦当比较丰富。
“里”“落”分野,即集村型“里”和散村型“落”的聚落分布格局,是早期国、野之分的遗留。正如邢义田根据上揭三处农村聚落遗址形态的研究所指出的:“汉代农村聚落内部布局形态非一,不像文献中说的那样整齐划一。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城邑之里和乡野聚落之里在形态上的不同。城邑中的里经过规划,可能较为规整,乡野农村即使纳入里的编制,其居址布局显然并不一定十分整齐”。先秦时期聚落的格局为:国、郊、牧、野,国人和野人常常用以对观。至秦汉一统时代,国野之野、都鄙之鄙并没有完全消除,国野之分的现实及观念仍然突出,《说苑·修文》记:“事毕,出乎里门,出乎邑门,至野外。”《汉书·食货志》亦曰:“在野曰庐,在邑曰里。”颜师古注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邑里和田野属于两种不同空间,野外的居住地称“庐”。根据《说文·广部》:“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和颜师古注《汉书·食货志》“庐舍”曰:“庐,田中屋也。”可知,作为居住场所的“庐”,其主要特征是农时居住,位于田野,且相对简陋。另外,从《说文》关于居处的释义出发,在汉代的社会生活中,“家”“屋”“里”“落”相较于“庐”也更具有普遍的居住意义。城及里外常居地称为“落”,田野中临时居地称为“庐”,“庐”为单个居住体,“落”为聚落形态,但两者都是“里”外的居住空间且均与田直接关联,故文献中又见“庐落”之称。国、野之分在简牍文献中也很清楚。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附《魏户律》“民或弃邑居野”,《日书甲种》(简144正叁)“戊戌生子好田野邑屋”。《岳麓书院藏秦简(叁)》一“魏盗杀安、宜等案”(简167正):“一人杀三人田野,去居邑中市客舍……”一目了然,城邑与田野均有居住地,形成邑中舍与田舍并立的景观格局。
总之,文献和聚落考古两方面的证据都表明秦汉时期集村与散村是并存的,以“里”为代表的集村型聚落和以“落”为代表的散村型聚落,呈现出明显的地理分野,这一区分与先秦时期国野之分格局暗合。
四
结语:“体国经野”与帝国的末端行政
秦汉时期,乡、里在基层组织中具有普遍意义和高度概括性,各类“集簿”和由之形成的统计资料往往以之作为基层行政组织的标准统计名目,如尹湾汉简《集簿》汇总了东海郡乡、里、亭、邮的数目和官吏人数;《汉书·百官公卿表》言“十里一亭”“十亭一乡”的行政组织关系以及乡、亭数目。但是,在此规范化的行政系统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组织形式,基层社会面貌的真实性与复杂程度如何,都已经逐渐成为讨论的热点。以上我们揭示的两种类型的聚落形态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是都被纳入了秦汉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系统。这类基层社会的末梢组织,对于理解帝国末端的行政运行尤为关键。
聚落的行政化现象,除了聚落在地域上被纳入行政管理范畴之外,更进一步的是聚落名的行政组织化。北大藏秦《水陆里程简册》“落”的出现,基本确认了“落”的地方行政意义,同时告诉我们秦汉时期的地方基层行政组织也并非只有乡、里类行政地名,还有“落”等一些自名聚落及组织名,其中就包括“聚”“丘”。“聚”较为频繁地见于史籍,它的出现可早至战国以前,生成具有一定的自然性,但在商鞅变法之后它又被纳入一般行政管理系统中,一定规模的“聚”成为县之下乡一级的行政组织,两汉时广泛分布于南北,尤其是不少“聚”有参与户籍等行政管理的记录,故其命名可能存在行政命名和聚落自名等多种形式。“丘”目前主要见于东汉及孙吴时期临湘地区的出土简牍中,属于自然形成的居住区,但它处于官方行政管理之下。根据人名及身份对照可知,“丘”与“里”存在着复杂的对应关系。另外,新蔡葛陵楚简有地名“丘”19处,对于“丘”的理解多参照走马楼吴简中的“丘”,以其作为“居民组织单位名”,与邑、里同类。陈薭则指出:丘为专名,为“某丘邑”的省写,并非楚国基层行政区划组织;并重申了一个重要的论点:“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采取的是城乡二元的制度,即对城内社区用直接控制的手段,对广大农村聚落则通过中间行政组织间接驾驭。”北大秦《水陆里程简册》中亦有“阆丘亭”“桃丘道”,结合传世文献中各带“丘”地名及其分布可知,“丘”或仅表示一种自然地貌类型,是平原边缘地形略微凸起且适宜居住之地。更有一些如“北上蒲”“涌东”“涌西”“羽北一”等不是“里”的乡、邑之下的地名,其性质和名义还有待进一步认定。除了“聚”之外,不考虑“落”等组织名和居住形态而提出的“都市国家论”的观点确实有失偏颇。
由于帝制早期管控能力有限,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聚落形态,采用了不同的行政管理方式,集居形态的乡里因其规范化特征更多的是被纳入了直接的郡县行政系统,管理相对系统而全面;散居形态的“落”则属于治安督察的范围,隶属于“亭”行政。聚落形态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可见一斑。国、野之分格局早已存在,而针对城邑聚落和乡野聚落的不同行政管理方式,即《周礼》所谓“体国经野”在战国时期进一步推行。陈伟曾对包山楚简中楚国的地方行政制度做过深入研究,指出了楚国基层行政组织“邑”与“里”的区别:“邑为乡野之中的地域组织。”“里很可能是城邑中的地域组织。”“简书中关于邑的记载往往与田地相涉,谈到里的时候却没有这方面的联系,盖即出于这一缘故。”又,先秦文献中的“里所在的政区系统仅限于国都(国),或其郊区(乡、遂)一带,同时存在的包含有邑的政区系统则位于边鄙地区(鄙、都鄙等)。简书中里、邑的关系似乎正与这一分别对应”。楚国的这一制度设计和运行,无疑是讨论战国秦汉基层地方行政运作的重要观照。郡县制下的乡里行政管理是标准化的,主体是分乡分里的分块式管理,而乡、野(都鄙)管理的分立,则受圈层式管理思维的影响,是一种辐射影响式的方式,体现了对以《禹贡》“九州制”为代表的分块式和“五服制”为代表的圈层式两种政治地理思维的灵活运用。
THE 特别声明:本文为企业作者上传发布,仅代表该作者观点、快闻网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6期,注释从略。
史学研究
专业刊物
史学月刊
一个有深度的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