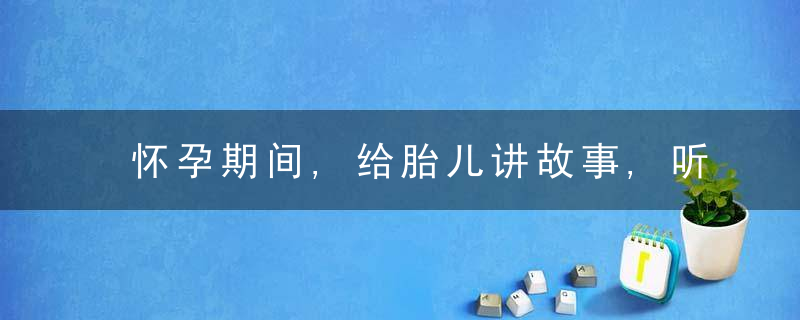说几句跟电影无关的话,一个曾经的法学学子的吐槽

回想入学第一节法理课上,老师就让我们进行了一场选择,任何一个即将跨入法学门槛的人都必须进行这场选择,你是选择信仰自然主义法学派,还是实证主义法学派?
自然主义简单说就是相信法律背后是以一种自然正义为依据的,所谓“恶法非法”;而实证主义坚持法律的基础正是法律条文和法律行为,所谓“恶法亦法”。
当时我们都把自然法学派作为一种过时的法学主张来看待,与现代技术主义传统和客观中立的态度显得格格不入。
当代哲学家里面我唯一还有兴趣的是美国的理查德·罗蒂,可惜这位年纪不大的哲学家死得比他曾经热爱的列维·斯特劳斯还要早。罗蒂很老实地承认说,对于正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不是哲学家可以回答的了,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发言权是值得质疑的。相对于他那本严谨细致的《后哲学文化》,我更喜欢他那篇小随笔《托洛茨基与野兰花》。哲学只是一个智识方面的游戏。
如果连曾经作为知识之王的哲学家都在这个技术主义的时代表示出了自己的谦逊和无能为力,那么律师或者法学家对于正义之类的概念似乎就更应该闭口不
... 显示全文 律师真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职业,曾经我也想象着自己有一天能在法庭上口若悬河、挥斥方遒。
回想入学第一节法理课上,老师就让我们进行了一场选择,任何一个即将跨入法学门槛的人都必须进行这场选择,你是选择信仰自然主义法学派,还是实证主义法学派?
自然主义简单说就是相信法律背后是以一种自然正义为依据的,所谓“恶法非法”;而实证主义坚持法律的基础正是法律条文和法律行为,所谓“恶法亦法”。
当时我们都把自然法学派作为一种过时的法学主张来看待,与现代技术主义传统和客观中立的态度显得格格不入。
当代哲学家里面我唯一还有兴趣的是美国的理查德·罗蒂,可惜这位年纪不大的哲学家死得比他曾经热爱的列维·斯特劳斯还要早。罗蒂很老实地承认说,对于正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已经不是哲学家可以回答的了,哲学对于这个问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发言权是值得质疑的。相对于他那本严谨细致的《后哲学文化》,我更喜欢他那篇小随笔《托洛茨基与野兰花》。哲学只是一个智识方面的游戏。
如果连曾经作为知识之王的哲学家都在这个技术主义的时代表示出了自己的谦逊和无能为力,那么律师或者法学家对于正义之类的概念似乎就更应该闭口不言了。
一个博学而又诚实的人是讨人喜欢的,不管他的诚实意味着什么。所以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里展示的那种诚实让我迷上了他,罗蒂在《托洛茨基与野兰花》里展示的那种诚实也让我倾心。同样,这部日剧《Legal High》里男主角古美门也因此而让我喜欢,因为他足够诚实,在第一集里就承认了作为一个律师对于正义和真相是无能为力的,从而把自己的律师身份真正变成了一个技术主义者。
在《Legal High》的第四、第五集里,这种对于正义的多元性和含糊性获得了集中的表现。帮助受侵害的居民向房地产商要求合法补偿是一种正义,但保护房产商不受到巨额赔偿的威胁,以使那些依靠房产商而工作而生活的普通人有一个饭碗,这是不是正义的呢?推翻一个腐败的官员是一种正义,但反对这位官员的其他官员,本身也是腐败官僚中的一员,那么这场权力斗争中又有什么正义呢?
所以古美门律师早早就说,我们律师不是神。无非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技术人员,协调这个社会的矛盾冲突,让他继续运行下去。
这样的古美门律师不讨厌,恰恰是他很诚实地有这种自觉,所以他既认可自己的不择手段,也认可对手的不择手段。说到底一切为了赢而已,如果说律师有正义,那么胜利即是正义。
但我讨厌的是什么呢?讨厌的是一面乐于承认自己技术人员的身份,从而回避一种沉重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却要占据一种制高点和优越感的律师和法学家。
我曾经很相信“法律信仰”这句话,这是我大学的老师灌输我们的。一切以法律为准绳,即使犯人没有得到应得的惩罚、即使正义没有得到伸张,只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中国进步的一种表现。
但现在我不相信了,这也是我背叛了自己的大学专业从事别的工作的原因,因为我是一个认死理的人。既然法律本身以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它,而律师也不过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人员,那么,法律和律师高于道德和大众的制高点和优越感究竟从何而来呢?
是因为法律相对于道德具有更高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吗?或者从技术主义的角度分析,法律相对于道德具有更高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但同样从技术主义角度而言,这种法律相对于道德的优势是工具理性意义上的优势,而丝毫在形而上地位上并不高于道德。
于是,完全可以说,当在某个时候,道德或者舆论比法律能够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规范社会秩序,那么法律并不是不能被折衷或者干脆抛弃掉的。
这也是我最终在药家鑫案或者是最新的敖翔案上选择站在舆论的一方而不是法律条文的一方。我觉得这其实没有什么问题。更何况到底什么才是刑法上“性质特别恶劣”,只能依据于经验判断,而经验判断,一个法官或者律师,未必就比一个普通大众更有发言权(按照大卫·休谟的哲学观点,也许反而是这种定性判断应该交给大众来完成,定量判断是技术人员的工作,也就是律师和法官的工作)。
我很反感律师和法学家把要求从重判的大众叫做暴民,因为律师和法学家没有丝毫立场可以这样叫,如果他们不愿意承担一种“追求正义”的道德责任而只是一个技术人员的话。
当然的确有暴民存在,我昨天晚上就碰见了一个,因为对于敖翔案不满,所以在微博上装成敖翔的辩护律师,胡言乱语煽动民愤。我也曾经听闻过,在合肥少女被毁容的案件里,网上也有人装成被告发表一些嚣张言论,勾起民愤。
但我会称他们为暴民,一样是因为他们不够诚实。如果这是一种控方律师的手段,那么我不仅不会认为他卑鄙,反而会由衷佩服其作为一个技术人员的尽忠尽责。就好象这部电视剧里的古美门一样。但如果,他们一方是将自己打扮成一个道德的卫道士,一边却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抹黑别人,从而突显自己真的道德无暇,那么就真的让人作呕了。
如果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变成一个技术人员,世界会不会更好一点呢?其实未必。世界需要理想主义者,但需要的是那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讨厌那些称呼大众为暴民的律师,他们一边对外宣称自己是一个技术主义者从而逃避社会责任,一边却又要求别人无条件信仰他们手中的技术工具,而且他们不承诺这种技术工具一定能带来正义。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一个工具?我同样也讨厌那些真正的暴民,他们将自己装扮成正义的代言人,但他们自己却同样将正义降低成一个获得胜利的工具,从而在正义的借口下可以进行一切卑劣的行为。
我更喜欢列维·斯特劳斯和理查德·罗蒂这样的老实人,喜欢古美门律师这样毫无节操的纯粹技术主义者。他们也许改变不了世界,但至少他们能很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1794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