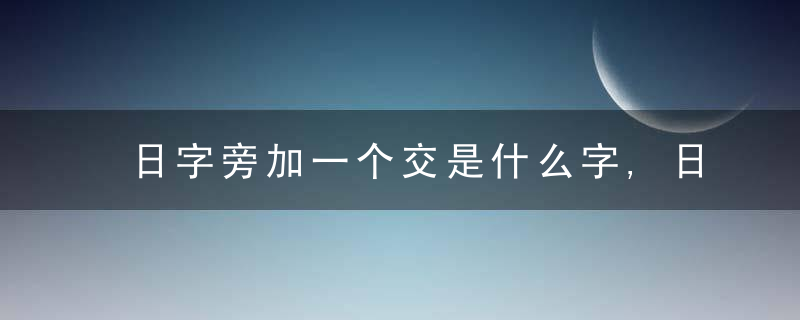那个对的名字叫郑问

郑问(1958-2017)
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的老东家高信疆先生约我在当时开始号称“东区”的一家酒馆见面。我们俩从来没有这种约法,因为情况实在特殊。见面第一句话,高公说的是:“我们来办一份报纸吧?”
相较于整整七年前我离开高公麾下的昔日,进入八十年代后期的台北有着明显的不同,人们浮躁地盯看着股市指数冲向台北的制高点,听着也说着财富重分配到别人口袋里的神话,而所谓“台北神话”,正是我和高公约会的酒馆的名字。“怎么样?我们来办一份不一样的报纸。”
关于几个月以后诞生的《中时晚报》和那个时代其他的报纸究竟有些什么不一样?可能得写一本专书才说得清。倒是高公想象中要和多年以前他戮力经营、引领风骚的“人间”副刊有些不一样的晚报文学副刊,这是当下就考倒我的问题。高公约我谈,就是希望我能主持这份新报纸的文学副刊。但是,谁能在高信疆巨大的身影底下想出什么真正“不一样”的副刊风貌来呢?别说风貌了,就连形状也摸索不出吧?
“撇开‘人间’编个不一样的副刊?你吃我豆腐,高公。”我说。
我没有想到高公立刻答道:“我有骆绅,你没有,这是你吃亏的地方。不过——”
骆绅是高公的学生,也是“人间”的头号执编,多年来一直都为天马行空的主编高公提供一切“使命必达”的编政服务。然而高公的话还有下文:“你要是能有一个林崇汉,那就厉害了!”
我给尚未诞生的副刊起了个名字,叫“时代”。但是那个下午,一路用琴汤尼酒泡到黄昏深重夜色浓郁,我们俩都没有想起:有谁能够像当年的林崇汉那样,以鲜活、细腻、无与伦比的宏大气势与写实风格打造出“人间”的版面美学呢?那个人,会是谁呢?
“有的时候,成大事就是想起那个对的名字。”高公说。
那个名字是郑问。我当天半夜想起来了!
不是要办报吗?发行人余范英很开心地带领着第一批招募来的创报同仁参观新建大楼,还只是个水泥框壳,看得出大堂挑高宽阔深广,日后装潢起来,自应有一份富丽堂皇的排场。
我们在粉尘和电焊气色之间绕着粗大的水泥柱胡乱踱走。郑问和我一步一步踏着水泥楼阶,甩开众人,直上六楼。我胡乱指着某个角落,像是已经规划好了、极有自信地对他说:“以后呢,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上班了。”
实则我所指的位置后来是厕所。而郑问看来一点也不在乎新的报业大楼究竟是个怎么样的格局、怎么样的门面。我之所以急着让他去想象或感受大楼落成之后的工作样貌,多多少少带着些鼓舞士气的动机——那是跟当下我们的处境有关的。
我们那时还没有办公室,甚至没有办公桌,参观完施工中的大楼那天中午,我和郑问才开始去购买“时代”副刊的第一批家当。那是两把九十公分和六十公分长的钢制直尺和一套圆规、一组极大的三角板、两块绿色的切割板、铅笔、蘸水笔,还有些琐琐碎碎的文具。我们借用白天中国时报“人间”副刊闲置的办公室画版,在骆绅上班之前匆忙离开,还真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郑问在工作上对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买两块切割板?”
“你一块、我一块啊!不是吗?”
“你也是美编吗?”他严肃地问。
我只是想帮忙罢了,可是这话一时之间说不出口。
郑问接着说:“那就给以后再来的助理用好了。”
他始终以一种非常温和的态度不让我碰那些美工器材。
郑问是一位杰出的画家,我其实并不知道他究竟会不会设计版面。但是很快地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个人如果不是普通会画,而是那么会画,那么他一定也会搞版面。
不过,眼中就是办报二字的发行人、社长、总编辑交代下来的第一个任务与设计无关,乃是:“中时晚报”四字报眉必须固定下来。根据报系创办人余纪忠先生的意思,是要和“中国时报”四字完全吻合。
这两个报眉相同者四分之三,即使从“时”字里也不是不可以采下一个“日”字偏旁,作为“晚”字的部首。可是问题来了:“中国时报”四字,昔年乃是出自于右任先生手笔,三原草书书风著名千古,而他的碑体沉稳厚重,不但摹写极难,就算是起于右老于地下,恐怕也未必能把自己数十年前的字临摹到神形俱足的地步。
这件事,不是高公所声称的大事,但是郑问触手即成。是他,花了几分钟的时间,盯着“中国时报”的原红色报眉看了个仔细,而后捉起水彩笔来,为那个“日”字偏旁添上了一个“免”,于右老的北碑雄豪之气竟然一瞬间汩汩而出。
一般的说法应该是:从第一天上班开始,我就察觉郑问不怎么开心。但是,哪一天算第一天呢?说得准确一点:是南部老家传来采访主任陈浩的父亲病重的消息那一天。有个不知道什么职务的同事林恺表示:怕陈浩心绪不宁,长途驾驶不安全,于是自告奋勇向发行人请假,说要开车送陈浩南下。就在一阵忙乱之中,郑问忽然问我:“你们都很熟吗?”
我说:“谁跟谁?”
看着匆匆穿过旧大楼长廊的两个渐行渐远的背影,郑问说:“你啊,跟他啊,还有他啊?”
大家不都是这两天才被挖了来聚成一堆的吗?我摇摇头,说:”不算很熟吧。”
“我谁都不认识。”郑问仍旧看着空荡荡的长廊,说:“可是他要开车送他去台南──如果不熟,他们路上要聊什么?”
我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像郑问一样,在你永远不可能注意到的细节之中耽上老大的心思。我说的还不是画画,而是生活。
他不太说自己,从不提家人,绝大部分不工作的时候,他像是空气一样发呆。每当我说了一桩也许不足为奇的什么事的时候,他总会瞪大了原本就不小的眼睛,显示出非常惊奇的模样。起初我还以为我说的事的确别有一些让人意外的趣味,后来才渐渐发现:郑问只是用看起来很惊奇的表情来掩饰他根本没有听我说了些什么。而且,越当他对某个话题毫无兴趣之际,他脸上的惊奇就越是夸张。仿佛他是两个人,一个躲在另一个的背后;藏起来的那个冷冷凝视着这世界最表象的样貌,以便随时素描或临摹;而面对世界的这一个,则不断示人以“啊!好有趣、多有趣──我以前从来不知道!”的反应。
试版期很长,我们每一天上午八点到班,逐渐被高公那种二十四小时必须随时随地发动的精神所感染,经常到接近午夜还不能收工。或许是出于一种弥补亏欠的心理,我总会在误了晚餐时间过后拉着郑问穿过报社对面的巷弄,到华西街小吃小酌。回想起来,他对饮食的兴趣不高,晃来晃去,最后总是一家名叫北海道的烫鱿鱼蘸山葵酱和猪肝汤。然而没有一回例外,无论是趁店家料理的时间、或者是吃饱了咬着牙签散步回报社之前,他必然要绕道一家蛇汤店门口,把鼻尖凑在铁笼上,仔仔细细观看笼中蜷曲扭动的蛇,然后赞叹地说:“真是漂亮!”
“可以回去了吗?”我说。
“你不觉得它们真的很漂亮吗?”他说,“像游泳一样活着。”
这是我永远不能同意郑问的一件事。他每一次都问我,我每一次都摇头。接着,他缓缓摇动着臂膀,仿佛蛇就长在他的肩膀上,一路摇回报社。不过,在那样一条短短的路程之外,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如何开心。
“中时晚报”开张第一天,他以极其精细的笔触、九十度俯角,画了一尊大炮。点燃炮火的士兵就像他在几年以前的《战士黑豹》以及多年之后的《东周英雄传》里那些让角色肢体产生华丽动感的表现一般,使观看者不由得不放缓了速度,必须以一种近乎凝视的姿态,观赏画面整体的布局和细节。我对高公说:“大师(这是早年‘人间’所有的编辑对林崇汉的昵称)回来了!读者不会看文章了。”
大炮是个“1”字,那是开张第一天的注记。第二、三天的版面则分别呈现了“2”和“3”(设若我的记忆无误,那3字还搭配了三毛的一篇散文)。郑问在第三天笑着告诉我:“这样搞下去会死人。”
郑问果然没有捱太久,他很可能是中时晚报第一个离职的员工。离职的原因很简单:他不能为了一份养家的薪水而放弃画画。高公在挽留他的时候的确使尽了种种高明的修辞技法,他高举双臂、仿佛招揽着数以十万计的报纸读者,其中一句是如此令我动容:“你的每一块版面,都是让几十万人目不转睛的艺术品,怎么说没有时间画画了呢?”
高公毕竟没有说服郑问,但是那一句“目不转睛”说得太恰切了。郑问的漫画作品就是在交织操纵着繁缛写实与大块写意的笔触之间,让我们看漫画的节奏根本改变了。有些时候,感觉他发了懒,刻意省略了角色身上的某些必要的绘饰。然而我们若是凝视得再久一点,或可以更有余裕揣摩出画家的意旨:省略了某些衣服上的花纹或装具,正是为了凸显角色的那顶帽子啊!可不是吗?那不是普通的帽子,而是君王的冠冕──且看那冕旒,正在风中飘荡。
郑问离职的那一天,职务交代给一个会画可爱卡通娃娃图案的小姑娘,就在他把切割板铺在小姑娘桌上的时候,我不期而然想起几个月前打电话给高公的那个深夜。
“我想起谁可以像林崇汉了!”我兴奋地喊着,“郑问。你下午说过的,要想起那个对的名字。”
这个名字陪伴我们的时间相当短暂,却令所有目不转睛之人回味深长。
本文刊2018年5月26日《文汇报 笔会》
所配画作均为郑问作品,张大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