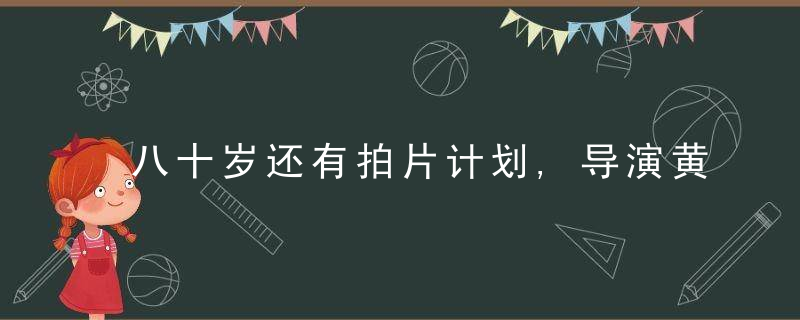一杯苕酒敬父亲

父亲的形象一直停留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在大姐家,有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没有我, 拍照时我没出生。 照片上共五人,父亲、母亲、爷爷、大姐和二姐。母亲扎一对大辫子,父亲剃着光头,爷爷坐在照片中间,父母站在爷爷身后,两个姐姐挨着爷爷坐。
黑白照片不太清晰, 父亲的形象就此固化下来。
我是家里几姊妹中唯一男丁, 但父亲没让我享受到应有的熊猫级待遇。上小学前,家里给我缝制一身新衣服,我高兴极了,在黎家大湾每家每户窜,上树掏鸟蛋,下河捉鱼鳅。当我一身泥回屋时,天快黑了,父亲正坐在门槛上等我,身后放着三根手指粗的黄荆条子。
父亲脸比夜都黑, 黄荆条子在我屁股上的啪啪声,连母亲都看呆了,居然忘记来救我。当晚,我俯卧在床上哼哼着,边哭边透过麻布蚊帐偷看父亲。 父亲端坐在四方桌前, 桌上一粗陶碗里盛着一小半碗酒,酒味飘来,是烂红苕酒。桌子正中,豆油灯发出昏黄的光,如父亲的眼睛,浑浊暗淡。父亲抓起碗,嘴唇慢慢靠近碗沿,狠咂一口,滋溜声在静夜里传遍整座房子。
这幅剪影一直压抑我好多年。
我趴在床上,内心充满恐惧,屁股火烧火燎,内心满是小小的恨,我恨那双粗大的手,我恨那三根抽断了的黄荆条子。
三天后,我才可以下床。我不知道父亲为啥下手那么狠。
小孩不记隔夜仇,那点小小的恨,在后来的岁月中早已烟消云散,但那烂红苕酒味却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之前,很少见父亲喝酒,家里也没酒,除非来了客人。父亲谦逊着让客人坐上席,他陪侧坐,母亲在灶房煮饭。我满屋子跑,偶尔到桌子边望一下,见大人不理,又围着桌子开转。那酒,远远地扑来,一股烂红苕味。酒不诱人,诱人的是花生味,从他们嘴里传出,脆崩崩地响。我无法抵御这香味,总磨磨蹭蹭向桌边靠,或往桌底钻。转悠久了,父亲用一双黑头竹筷夹一粒花生给我,然后敲打我小脑袋喝道:“滚!”
客人大抵看不下去, 夹一粒花生给我,又用筷子沾一滴酒让我尝。筷头一入口,若火如辣椒。我皱着眉,干咳着,嬉笑着,小脸憋得通红。客人笑说,不像个男人。父亲对客人调侃报之一笑,虎起脸对我说:“走开,莫打扰大人说话。”
此后, 我将酒味固执地定义为烂红苕味。 那时的酒一般都是用烂红苕或苕皮酿造。就是烂红苕酒也没多余的,只有来客才可去代销点打一点。
父亲高大,但特别瘦,胡子拉碴,我一直在想父亲之所以能够把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娶回家,一定得益于这副身板。
爷爷去世后,父亲老爱阴脸,成天不说话,总呆呆地蹲在屋角抽旱烟。一天,我见父亲破例倒了一小杯酒独喝,喝了好几个小时。一家人重担全压他身上,他的孤独与无奈没人能懂。我敢肯定,父亲是恨自己无力撑起这个家。
父亲开心喝上一杯小酒,要追溯到联产承包那年。地里庄稼让父亲开心极了,他知道秋收后家里再不会饱一顿饥一顿了。母亲在阶沿上切猪草,噼里啪啦地切。父亲看上去有些累,脸上已没了以前的雾霾。一到家,他就端一把凉椅放在院坝边核桃树下,打开身子躺下。
母亲转身进屋倒一小杯酒,端到凉椅前那根板凳上,不说话。父亲眯着眼,似乎没看见。我见他鼻翼动了动,深深吸一口气,放下二郎腿,睁开眼,看看母亲,又看看那杯酒。端起来,甩着鼻翼左右闻闻,放唇边浅浅抿一口,哧溜一声,再咂咂嘴。
这是我见过父亲最为优雅的饮酒,以至于我怀疑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父亲招招手说:“娃,来尝尝。”我说去拿根筷子来。父亲说“不拿”。父亲端起酒杯:“哪个大男人用筷子沾酒喝。来!整一小口。”酒顺着喉头滑下去,一股火辣烧毁了我五脏六腑。
那一年,父亲死于破伤风,那股浓烈的烂红苕酒味也随之而去。那一年,屋后竹子在开花后很快就枯萎了。
子欲养而亲不在。每年清明节,我必到父亲坟前祭奠,每次去,我都想给他带点酒,可我跑遍全城也无法找到一瓶烂红苕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