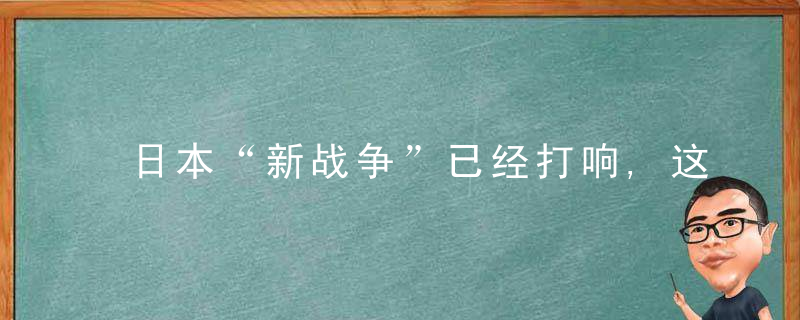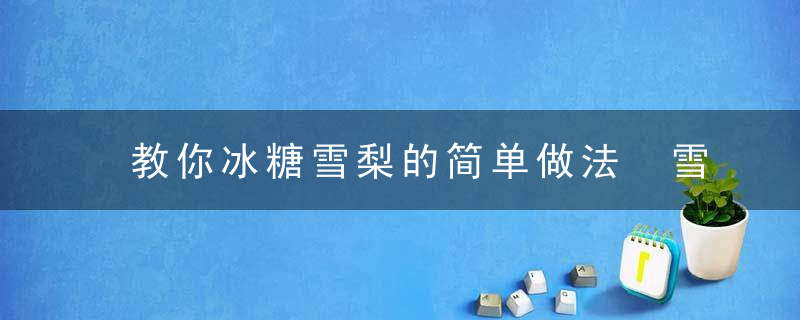中国人为什么没文化

网上流传一个说法:“目前咱国对艺术的欣赏水平,停留在:(弹钢琴)弹得真快,(唱歌)唱得真高,(画画)画得真像。”
好笑之余,这确能引起很多人共鸣,回应着一个许久以来的普遍感慨:“中国人真是没文化。”1980年代的“文化热”可说便是这种焦虑感的体现,但三十多年来,中国人似乎并未感到自身在整体文化水准上得到了多么显著的提升——至少和我们的经济增长不可同日而语。
对此,一个通常的观点是:这只是因为中国人穷,解决温饱问题还不过一代人时间,恩格尔系数直到去年才降到30%以下,怎么能指望他们能把多少钱花在文化消费上?
然而,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毕竟从未实现全民富裕的古代中国、甚至饥寒交迫的晚清民国,文化水准恐怕还比现在强;而经济兴盛看来也并不必然会让中国人更有文化——香港可能算是华人社会中经济最繁荣的了,却长期背负“文化沙漠”的恶名。社会学者何国良、梁世荣以1993及1995年的社会指标调查为依据研究后发现,香港社会虽然自197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增长了一代人时间,但却并未像西方社会那样,随着社会日趋富裕,而逐渐转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在香港人的心灵中,物质主义根深蒂固。即使社会及经济环境在过去二十年已经发生急剧变化,但也不易改转过来。”现在大陆社会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正与香港当时接近。
说一个社会“没文化”,通常是指其民众普遍缺乏审美能力,这往往又伴随着其精英的文化创造力薄弱。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文化的不断创新则不仅提升一个社会的整体文明水平,而且特别有助于它的政治品质的改进”(余英时语)。因此,“中国人为什么没文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而言并不是一个小问题,但要回答它,可能比我们想像的要复杂得多。
功利主义的文化观
当然,首先要明确的是:怎样才叫“没文化”?这不仅仅指缺乏文化艺术鉴赏品味、缺乏基本的知识、举止无仪,有时还特指不识字。“没文化”不一定是“没智慧”,一个文盲老太太也可能根据其丰富的人生阅历,说出一番极富哲理的话来。但对于“有文化”的基本准入装备,不同人的界定千差万别,英国学者斯诺(C.P. Snow)曾说,人文知识分子眼里,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人属于没文化;但在物理学家看来,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人也没有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在人们的身份认同上常常起到一种“区隔/排斥”的作用,这一点很像时尚在现代社会所充当的功能:拥有了它,你就能占据鄙视链较高的位置。
因此,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文化”其实是一种权力,历史上无论中外,那些无文字的族群或不识字的边缘群体,大多被视为“没文化”而被权力结构所排斥。但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这些以往被边缘化的群体进入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按托克维尔的话说就是:“大革命是一种极为新颖的革命,其最有力的参与者是最没文化和最粗俗的阶级,当他们被鼓动起来并且由知识分子来为其制定法律,一种全新而可怕的事物便来到了这个世界。”这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们熟知的一幕: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传统的“雅文化”大多被视为封建糟粕而被扫进了垃圾堆。
从表面上看,现代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远高于先辈:据美国学者罗友枝的研究,19世纪中国35-45%的成年男子和约2-10%的女子都具备基本读写(两千个汉字)的能力,这在当时全世界来说已属不低,却显然远不如识字率高达96%的当下中国。然而,“文化”不仅仅是会认字,大学毕业但美术鉴赏仅能说出“画得真像”的人比比皆是。原本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就是靠一小群知识精英来守护的,当他们在时代剧变的浪潮中被冲刷殆尽后,剩下的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文化观。
简单地说,这种观念认为,无论读书识字还是“文化”,都应当是“有用”的。香港人之所以没有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社会富裕之后转向精神性的自我实现,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他们是特殊的经济动物,而是因为在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中,人生的最高意义并不是超越性的,相反是相当世俗的: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光宗耀祖”,都并不带有超越性的冲动。
在这种传统下,中国人依靠自身的才能达致成功,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下的“自我实现”不是一回事,倒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获致社会地位乃至权力的努力,并以此得到社会认可;而后者则偏重伸张自己真实的个性特质,突出与他人的不同和创新贡献。
中国士人的这种观念由来极久。《史记·苏秦列传》就记载他羞于被家人嗤笑,发愤说:“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低头受教,学到的东西却不能用来升官发财,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
这在两千年来都能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共鸣,所谓“大丈夫当封万户侯”(流传到今天的版本则是“男人要有进取心”)这样的想法深入人心,无论李白还是辛弃疾,这些中国古代一流的文人,都想着要以自己的才华获取一番功名,班超“投笔从戎”与其说是爱国,不如说是为了封侯。在科举制度确立之后,“才华”与“功名”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文人自此可以向社会证明,自己的才华可以有望“兑现”成地位和权力。
只有当他们奔波劳累或无法功成名就时,才会发出诸如“白首为功名”、“可怜白发生”的感慨,退而求其次,在业余时间从事一下文化创作。徐渭、蒲松龄这样的文化巨人,却都曾是屡试不第的落魄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极多。如果不追求有用却沉溺于诗词书画之中,那么就要被指责为“玩物丧志”。
晚清外交官李凤苞在《使德日记》(1878)中写道:“尝疑西人之习华语,不过为通商传教,有所为而为耳。及来欧洲,方知有终身探讨中国古文诗词及满蒙文字,苦心孤诣,至死不变者。且有妇女详考亚细亚古民种、古文字、古诗词者。”他之所以感到困惑和新鲜,是因为中国人投入精力去做文化研究,都是“有所为”的,却发现西方竟真有人“不为什么”,只是单纯的喜欢。
现在好多人痛感中国人“不读书”,工作后能保持日常阅读习惯的人极少,即使读书,目的性也极强——为了考公务员,或者只读本职有用的书。平心而论,中国人历来如此,《儒林外史》里的书生基本只看科举应试用的“时文”;1891年南京著名刻书铺李光明家广告开列的109种书册名目,史类仅有四种稍讲解点基本历史常识,说明当时学子不需要读史书,因为科举考试不考它。日后成为著名教育家的蔡元培1904年写了一篇白话短篇小说《新年梦》,里面说:“每人一生的课程:七岁以前是受抚养的时候,七岁到二十四岁是受教育的时候,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做职业的时候,四十八岁以后是休养的时候(但休养时亦可兼任教育等事)。”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人生规划里,只有到退休后才能“正当”地享受文化生活的闲情逸致。这便是陈寅恪所说的,以往中国人认真研究文史,“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
因此,中国社会长久以来的一个悲剧是:你想做某事时没有“资格”,但等到你有资格做的时候,热情却已经被消磨殆尽。这种“有用”的标尺一直若隐若现地存在于许多中国人的意识中,我一个大学同学前些年重逢,手里多了一串开过光的檀香木念珠,他说:“你还在读那些没用的书吗?我觉得你还不如读点佛经,真的。”或许在他看来,我在大学里就很“脱离现实”,总看一些既不会考、对职场也无用的书,而他建议读佛经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高层商务人士的“精神话题”之一。
如果要说现在有什么不一样,那或许在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要证明“知识”或自身“有用”,变得更困难了。
知识与文化无法直接有效地“兑现”为权力与财富,还投入那么多时间精力,这让许多人感到相当费解。不仅如此,民国以来新的社会结构使得原先当兵、从商等边缘的渠道也能通向权力,这进一步滋长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傲慢:他们反过来瞧不起文化人,因为这既不能当饭吃,也没有任何利益。近四十年来的经济繁荣进一步排斥了非功利性的文化活动,有时还伴以诸如“你真闲哦,还有心思看书”、“书这么多,卖掉都能在哪换套房了吧”之类半真半假的嘲讽。当然,这或许也是一个契机:文化活动不必再证明自己“有用”,毕竟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
文化如何进入生活
与这种要求文化“有用”的心态密切相关的,是一种非专业化的态度。因为既然个人只是在先办完“正事”之余才因个人兴趣去从事那些非功利性的文化活动,那么理所当然地,他们往往清高地表示不依赖后者为生。这就造成一种延续至今的双重困境:学画不能吃饱饭;但如果你要以画画为生,那卖画又被视为俗气。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名篇《黄英》中谈到了这一态度:马子才沉迷于菊花,得知有佳种时不惜千里求购;但当新结识的陶生(其实是菊花神)说“你家也不富裕,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倒不如卖些菊花也能谋生”时,他很鄙视,说我本以为你“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生笑着说了一句“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也”。
陶生所言相当豁达,但马子才的态度却才是更典型的中国人心理。
我妻子是自由插画师,美国那边有人在网上看到,十分喜欢她的画风,想定购几幅向未婚妻求婚。这事有次说起,一位朋友脱口而出:“那如果是我,你喜欢的话,就送给你好了。”这也就是说,中国人内心不习惯买艺术品,这就附带产生两个问题,一是很多人看到好的却不想付钱,能送最好,不送那就算了,不尊重艺术生产;二是很多艺术生产者自己也耻于谈钱。因此这种清高语调的背后,本质上恐怕是中国人尚未普遍意识到现代艺术和学术都是高度专门化的职业活动。
说到底,中国仍是一个尚未经历充分现代化的社会。从历史上看,文艺家要维持自己生活,要么靠家产可以不愁吃穿,要么靠赞助人(权贵或国家),要么靠市场(实际上等于无数赞助人)。在传统时代,文化艺术的确很难“当饭吃”,无论中外,中世纪最好的画家和音乐家如果要专注于自己的技艺,唯一的办法通常就是找一个权贵作为赞助人。
杜甫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他既不靠写诗为生,也没把全部时间用来写诗,况且也没地方卖诗,幸好还能托庇于成都府尹严武门下。
只有到了社会经济形态逐渐复杂化、市场化,艺术家可以在市场上卖出自己的文化产品获得报酬时,他们才获得了相对的独立自主权。
一个社会的文化品味、审美趣味要得到提升,仅靠几个不世出的天才艺术家是不行的,那需要文化产品能深入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这只有文化艺术的生产工业化之后、经历长期的潜移默化才有可能。在国内的城市里,上海普通市民的品味可能是最好的: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也听古典乐,居委会大叔能拉手风琴乃至三四种乐器,随便什么地方常会冒出乍看其品味与社会阶层完全不符的人,哪怕是平常人家也大多认为应该受艺术熏陶。这正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经历:在近代中国,它是唯一一座真正的“现代城市”,从而拥有自己深厚成熟的市民文化底蕴。
这种“文明的进程”率先出现于近代欧洲: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层在满足温饱之余也开始有钱进行文化消费;另一方面,艺术家也开始拥抱这一市场需求,让文化活动渗透到公共生活中去,此时,文艺批评家们的活动也开始专门化,为公众的品鉴提出参考指南。在这样不断的互动中,社会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味自然而然地便得到了提升。这种理念深入人心,就连纳粹德国时期,希姆莱都秉持着“每个德国家庭都要享有艺术品”的信念(虽然“我的党卫军成员的家庭优先”),坚持将瓷器、绘画、唱片等大规模生产以供应社会消费。美国在文化事业上相对落后,19世纪镀金时代时全社会忙着赚钱:“人们的所作所为无不仅仅直接着眼于物欲的目的;至于审美,或者是次要的,或者根本不存在。……每件事物似乎都反映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即衡量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是金钱。”(《美国企业史》)但到20世纪初,美国的艺术和艺术市场也起飞了。
中国的特殊性在于:长久以来大众都力求温饱而不暇,价值观又偏重务实“有用”,因而文化艺术常常只是社会精英非正式活动的产物,也没有经历文化艺术市场的现代化;其结果,在国人的意识里,那些高雅艺术与自己有着相当的距离感,和自己的现实生活不发生直接联系。即便是书店,在很多人眼里也就只是个卖书的地方,是一种面向特定人群(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学生)的特殊商品——有时买书人甚至意识不到书也是商品,它常常要么被半神圣化,要么被视为应试的工具,但总之都是“非日常的”,与普通成年人的生活有某种距离,和周围普通人不大产生关联,只有知识分子才觉得这是“成瘾性必需品”。换言之,无论是书籍、音乐、美术、话剧,人们都觉得“和我没多大关系,平日没有它也过得好好的”。
这样,中国人文化生活的贫乏既是供应不足,同时“需求”也不足。谁会专门买票去看戏剧、话剧、音乐会?甚至免费的博物馆展览也不多。伦敦的很多戏剧票价最贵也就是60英镑,是普通人负担得起的,而国内高雅艺术曲高和寡,完全脱离民众日常生活;低的又非常低,电视剧和二人转,能广泛传播的多迎合大众最低的趣味,往往是简单通俗、粗糙刺激的作品,缺乏既有一定品味又能被普通人接受并消费得起的中间档。
与此同时,民众也没有追求,觉得艺术离自己很远,喜欢自嘲是粗人,只抓住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稍有一些文艺,就要被贬成“装逼”——所谓装逼,就是因为脱离日常生活(不是自己喜欢文艺本身,而是觉得那腔调好)。但在佛罗伦萨,那就是日常,一个出租车司机也能和你如数家珍地讲到很多活动,博物馆展览和文艺要在哪里看。
一位朋友感慨之余说:“在欧洲,一个人喜欢一幅画,花几百块钱买回去挂墙上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国内有吗?没有。你我都算是文化人,也都没这样吧?没有一个正常的艺术品市场,只有一个投机的、脱离民众生活的市场。中国不出名画家的作品没人买,成名了又爆炒到不正常,买它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因为保值升值。”
所以,怎样才算有文化?
你会不会觉得那些是“必需品”?生活中少了它们是否就不像生活了?
当然,这些年有了网络,中国人在知识分享、文化流通方面确实比之前做得好多了,加上社会逐渐富裕化和之前十几年的大学扩招,有能力进行文化消费的群体毕竟还是有所扩大了。如今市面上很多博士论文著作出版后也都轻松卖到三千册,一些相当学术的专著甚至也能卖到上万册,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
随着社会的变迁,如今中国社会的专业化程度大大提升,但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这又使得原本就缺乏公共文化生活的中国人进一步窄化了自己的兴趣。很多大学老师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外,对别的书都不看;古典文学老师讲白居易《长恨歌》,但对写过同名长篇小说的作家王安忆都不知道。
当然,这样的现象不仅国内如此,很多专业的内容确实只有专业的群体才感兴趣,也正因此,一个公共对话、并有批评沟通的文化环境才显得尤为重要。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但或许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