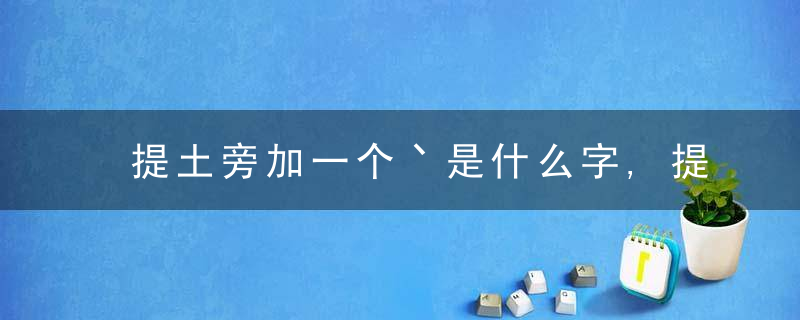十年网瘾一轮回

一
不久前,来自天南海北的众多父母,同心协力拯救了一位在B站被up主“骗诱”,险些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女,及时避免了更恶劣的影响。而利用了“围观”“人肉”“编段子”“讨贼檄文”等众多网络时代特有的“作战”手段,站在B站那位up主对面的并非寻常路人,而是上个时代的“资深网民”。
也就是说,在这则“网瘾大叔拯救网恋少女”的故事中,这些网瘾大叔来自一个属于10年前的地方——NGA。
二
NGA全名“艾泽拉斯国家地理”,这一语出《魔兽争霸》,又因《魔兽世界》而为人熟知的论坛名,与“厨艺”“育儿”等版块名,是如此不搭。
21世纪过去十多年,NGA早已从一个魔兽论坛,变成综合游戏论坛,又变成大型综合论坛。越来越多的80后wower,偶尔会发出感慨“这是我在育儿版发的第一帖”。
精英玩家俱乐部与育儿版相映成趣
wower是一个人群,指网络游戏《魔兽世界》的玩家。你以为他们是什么人?“高职”(对“高端职业玩家”的讥讽),中二病,乃至网瘾少年?
实际上,即便在当年看来,魔兽世界的玩家也遍布各行各业,很难把他们归为同一类人。就拿“下线理由”来说,解放军战士会说“排长喊我集合了”,白领会说“老板叫我搬砖了”,学生会说“我妈查房,我先装睡十分钟”。当有人喊出“一会上课”时,不要劝他翘课,因为他可能是老师。
曾经被贴上一系列标签的wower,如今已是社会各界的中流砥柱,与曾经鄙视、不解乃至害怕他们的长辈相同。他们同样成立家庭,养育子女,如果你问他们的另一半是不是同为游戏玩家,他们会告诉你一千个不一样的答案。
将80后的NGA与00后的B站在上周骤然联系起来的,恰恰就是亲子关系。文章开头提到的少女诱骗事件中,身陷其中的00后少女本人,有一位来自NGA的80后妈妈。家庭与“爱情”的冲突,长辈与小辈的代沟,种种纠结,当年的“网瘾少女”面对如今的“网恋少女”,心情不可谓不复杂。
有人戏称,现在这帮00后以为只有自己才懂互联网,殊不知他们那些把戏,早就被前人玩得滚瓜烂熟;也有人喟叹,10年过去了,我们怎么回头看待当年的自己?
三
本世纪初,在《石器时代》《魔力宝贝》《传奇》等日韩网游刚刚进入中国时,一些少年最先拥有了“网瘾”的前缀。放学以后的时光,他们把当时为数不多的零花钱都换成游戏点卡。有时候,还会把点卡再换成游戏里其他东西。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肝”又“氪”了。
然而那时候根本没有“肝”“氪”这种说法,PC对于部分人家的孩子还是奢侈玩意儿。电子游戏虽然在当时也不算特别高门槛,更谈不上昂贵,但孩子与电子游戏之间的关联,毕竟要通过“家长”。买游戏机要钱,买卡要钱,买光盘要钱,去网吧也要钱。孩子与游戏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难逃家长的法眼。
石器玩家曾经的氪金目标之一
北上广的孩子比较幸运,他们有眼界更开阔的童年。即便当时的拨号上网相当昂贵,但与同学之间受人仰望的GBA、PS2等相比,也是半斤八两了。因此,在日韩网游刚刚进入中国社会视野时,大城市的少数孩子成为了他们的忠实粉丝。因游戏而悲伤的家长,也最早在大城市出现,就和最早的网吧一样。
最早的网吧不禁止孩子入内,但与之后几年相比,还算不上孩子的天堂。对非核心玩家尤其儿童来说,网吧本身作为新生事物的距离感,以及“蓝极速事件”带来的恶劣影响,足以令网吧本身值得怀疑。正因如此,此时多数少年并不十分依赖“网吧”,“网吧”与“网瘾”,尚未被关联起来。
不止一位学生家长和老师曾经公开表达自己对游戏的态度。一些学生因为玩游戏严重影响了成绩,不得不遭受父母的百般限制。有些孩子从家里偷钱、骗钱用来支付不菲的游戏开支,更严重的连学校都不去了——这些当年的问题学生,再过几年就要被媒体称为“网瘾少年”了。
不过,即便个例并不少见,“网瘾”一词在当时离多数人还比较遥远。由于彼时参与游戏的人群比例不会太高,中国互联网的早期住民仍然是文字内容的消费者,即便个别学生将大量时间、金钱投入游戏,也只有他们的家长在叹息落泪,并未引起整个社会的声讨。
四
然而,社会总要注意到,国家总要注意到。
2008年,作家刘明银出版的“纪实文学”《战网魔》中,就明确将“网瘾”当作一种疾病。央视播放的同名纪录片更让许多家长像相信“食物相克”一样,相信了“网瘾是一种病”。
在《战网魔》中,刘明银认为,玩家接触暴力、魔幻游戏,性格就会变得凶暴,最终成为游戏世界里的“怪物”。这种缺乏科学根据的臆测,在陶宏开、杨永信等“专家”的赞同声中,逐渐为不明真相的家长群体所接受。
刘明银也记述了“网瘾少年”接受“电击治疗”后重获新生、感恩戴德的离奇场面,而杨永信涉嫌刑事犯罪的治疗方法,也一路延续到了今天。这不禁令人想起世界上曾经拥有最多精神病人的国家苏联: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因精神病院的存在而存在,也随着精神病院的轰然倒塌不治而愈。
遭玩家恶搞的“磁爆步兵”杨永信
社会舆论当然不是一面倒的。《看你妹之网瘾战争》等网络动画的发布,就是来自玩家群体的“有声抗议”。
当然,发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一方拥有出版社、电视台等渠道,一方则仅仅在玩家圈子里自娱自乐。何况,如果只看内容,《战网魔》等作品虽然荒谬,也还采用了大众习惯的叙事口吻;而《网瘾战争》等严重恶搞的亚文化作品,则无疑属于“鹰派科普”,几乎无法起到启迪大众,传播正常的网络观、游戏观的作用。
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下,我们没办法苛求弱者表现得既勇敢又理智。何况,你试图反抗的是身为美国人也能大言不惭讲出“美国人不玩网游”这种鬼话的陶教授。
五
80后可能没想到,不管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全中国形形色色的00后,最终都会遇到和他们当年同样的问题——一旦一个人玩了网游,沾了“网瘾”,他的一切问题,就都可赖到网络头上。
十年过去,一切都变了,似乎一切也都没有变。网瘾少年依旧网瘾,国家依然视网络游戏如洪水猛兽。
今年两会上,胡万宁的一番话,恍如出土文物见光散发出的霉味——“要像控制毒品一样控制网络游戏,必须一竿子打死。”
是什么给了胡委员如此强烈的危机感?
今天的WOW恐怕有心无力了。取而代之的,是遭受人民日报“三评”的《王者荣耀》,是屡次遭修改画面、文字内容的各种“纸片人”游戏,是焦点访谈口中“几乎全裸的女性角色”——如果照《焦点访谈》的标准,泳池中和选美大赛上,就都是“几乎全裸的”人类了。
事实上,以不少80后的游戏标准,00后热衷的东西可能确实“不是他们的菜”。总会有个别年纪不小的硬核玩家跳出来,痛心疾首地高呼国内游戏市场被“垃圾”网游、手游充斥,甚至点名嘲笑某些游戏的“氪金”玩家,直指他们不懂游戏的乐趣。而显然地,00后也并未屈从于老家伙的意志,道理也很简单:我凭什么需要你来告诉我什么叫好、什么叫坏?
每代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东西——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对游戏的“无用”爱好正是每个人、每代人热爱和平、美好日常生活的表现之一。面对恐怖分子的袭击,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宗教、种族、肤色地联合起来,站在和平立场上谴责恐怖主义,正是出于对这种美好日常的信奉和维持。
毕竟,比起争论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游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更该自问:假如这种日常的美好被打破怎么办?
当然,如果不断章取义,胡委员并不是真的要把游戏“一竿子打死”。胡委员重点表达了对未成年人沉迷网游的焦虑,而这种焦虑,结合世界各国的政策,多少是有道理的。
针对自控力差的未成年人,国家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吗?不是。
除了发布当年如笑话般的“绿坝-花季护航”,“突击搜查网吧”“绑定身份证”等措施,老早就被国家用于针对未成年人的网游管理。可惜,这些漏洞百出的监管实在起不到什么作用。如今的青少年,沉迷“网游”的阵地早已转移到手机上;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没多少孩子非得奔赴网吧去冒这个险。至于身份证验证,10年前的学生就会“绑哥哥的”“绑家长的”“绑网上1块钱买的”,这种低级措施又有什么用呢?
至于那些因为内容原因无法引进的作品,玩家完全可以去“盗版”,乃至挂上代理去“跨区”。许多根本看不懂日文的玩家情愿用着付费代理,生啃日文,承受着汇率的波动在日服“氪金”,只是为了享受更好的游戏内容。
这就像几年前引起国家注意的“海淘”一样。如果国内的供给不能满足国人的需求,“代购”们甚至愿意冒险“冲关”。需求的存在无法抹杀,如果国家无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提供商品,自然也就无法享受商品相伴的税收,以及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增长。
“如果没有游戏吸引,青少年可以去做更有意思的事情。”这种表述也是游戏恐惧者的陈词滥调。十年过去了,也没见哪位大人物推动了哪个产业、什么玩意儿发展,让其变得比游戏“更有意思”。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游戏的原罪,还是不作为者的耻辱。
六
这是一种双输。
在玩家个体的层面上,他们始终无法洗脱被污名化的“网瘾”,一旦玩上游戏,就要承受父母乃至邻人的白眼。
就算你不在意,舆论压力仍然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为了避免“几乎全裸的女性角色”,“责令修改”后的游戏内容,始终无法原汁原味。至于那些修改也没用,甚或出品方根本懒得接茬儿的作品,玩家则无法在国内拥有正规的游玩渠道。
而集体层面上也未曾好到哪儿去。10年前就在“战网魔”了,10年后仍需“三评《王者荣耀》”;而10年前对国产内容的严厉审查、监管,使得中国的游戏行业在某种层面上几乎原地踏步。即便有网易、腾讯这般规模庞大的公司,就全国游戏市场来看,优秀的国产游戏数量仍然占比极低,而在世界范围内堪称有影响力的作品几乎为零。
国内的游戏公司,一度因为市场不发达、产业不成熟,只能为外国大厂打杂、代工;而整个中国的游戏行业,就如同几十年前的制造业一样,忍受着国外同行的“剪刀差”剥削。对于每个人来说,在游戏公司工作绝对不算一件有前途的生计,父母都会劝你转行。
而在代工了巨量欧美3A大作,得到充分历练后,中国的游戏工作者本来期望能在属于自己文化的市场大展宏图——结果10年以后,他们出品的游戏或是直接做英文版、只面向海外市场;或是停留在梦想的起点,始终没能超越自己当年为之代工的作品。而在游戏公司工作,如果不是腾讯、网易,人们仍然不觉得是有前途的生计,父母仍会劝你转行。
少说也有20年的中国游戏市场,能否像欧美游戏、日本游戏一样,在国家的角度承担文化输出的任务?日本人认识三国,是否仍然通过KOEI Tecmo的《三国志》《三国无双》?中国的大多数游戏从业者,是否不再从属于“低端代工产业”,是否像真正的创作者一样,输出自己的内容,拥有自己的职业尊严?
而在世界范围内,游戏的意义甚至早已超出了传统范畴,而真正成为一种“基础设施”,进入各行各业。近两年骤然兴起的“功能游戏”(或曰“严肃游戏”),便是显著代表。美国开发商BreakAway从1998年起便面向垂直行业开发严肃游戏,横跨国防、医疗、教育等八个领域,在医疗界(而非游戏界)屡受表彰。
而类似公司也遍布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等。教育游戏《PaGamO》在台湾K12教育人群中使用率高达20%,《生死征兆》被用于训练急救医生的应对技能,《量子移动》则将游戏众包研发模式从蛋白质折叠拓展到量子物理研究。
而中国游戏行业的土地上,名为“网瘾”的毒草,仍然随风飘扬。
七
除了情绪比较激动的胡万宁委员,今年两会上还有数十位代表提出自己对网游的看法,其中多属负面。
符宇航等十名代表联合建议:网游如精神鸦片极大危害青少年,需要严控。而为人熟知的巩汉林不惜“家丑外扬”,提出自己不到两岁的孙女就喜欢“盯着手机不放”。
即便在两会中,只要一谈网游的危害,逻辑就无足轻重了。
我们当然不知道各位代表、委员是怎么管教自己孩子的。但很显然,他们想要管教的,不只是自己的孩子。
游戏玩家可能会选择与他们对立起来。然而,一味呼吁不监管、少监管,恐怕是不现实的。拿先进经验来看,美国、日本会针对未成年人,将游戏作品区别对待。每一位资深玩家也应该认识到,部分内容对少年儿童确实有不利影响,而游戏作为尤其强调娱乐性(一些游戏甚至直接追求在线时长)的内容,也容易对未成年人产生过强的吸引力。
如果你当年就曾是他人口中的“网瘾少年”,你是否也后悔过当年自己的一些行为?哪怕你今天有着非常辉煌的事业,当年因沉迷游戏对父母造成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的隔阂,是否难以弥补?
如果无视这一点,那么游戏产业不仅无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更会逼得如胡委员等人走上“一竿子打死”的道路——干脆成年人也不要玩就好了。应该清晰认识到的一点是,对于那些不玩游戏的人来说,他们关心游戏的唯一入口,可能就是他们的孩子。
但是望眼欲穿地等待分级到来,也称不上理性。玩家和从业者应该认识到,在书籍、电影等大众文化都未曾实现分级的今日中国,呼吁“游戏分级”未免过于乐观。
幸运的是,电子游戏起源于技术,它的内生问题不仅可仰仗外部干涉解决,也可仰仗技术本身。国内一些技术强大的游戏公司,为了避免政策倾向愈发收紧,便赶在风向变化之前,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自我约束方案。
如果说从前简单粗暴的“身份证绑定”已被证明无效,那么通过引入AI,增强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等身份鉴别方式,或可有效区分未成年玩家。值得庆幸的是,何寄华等人便提出了类似提案。
2017年2月16日,腾讯便推出了“网络游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之“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协助家长对孩子的游戏账号进行监督。此外,网易、世纪华通、完美世界、搜狐畅游等游戏行业中的重要企业,在现有监管框架之上,纷纷跟进了自家独创的未成年保护措施。
可惜的是,行业内部未就相关标准达成共识,因此这一标准从“自律”变为“政策”,仍需时间。
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为了成年玩家有更好的游戏体验,行业内部已经达成了“壮士断腕”的共识。断腕固然可惜,“断头”则是不能接受的。
八
佛罗里达枪击案之后,身为共和党人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坚守“反对控枪”立场,在新闻发言中找了许多甩锅对象,游戏赫然成为其中之一。
3月9日,特朗普直接在白宫面对众多媒体来了一拨“暴力游戏展示”,并进一步明示游戏使青少年崇尚暴力。眼观如此荒谬之事,不知道好莱坞的各位电影导演有没有唇亡齿寒之感?
而中国也该由此看到,世界各地的老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他们对游戏的偏见无法消除,那么游戏“自证清白”一事,还真要交给行业自己来完成。














打一生.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