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痛失北方四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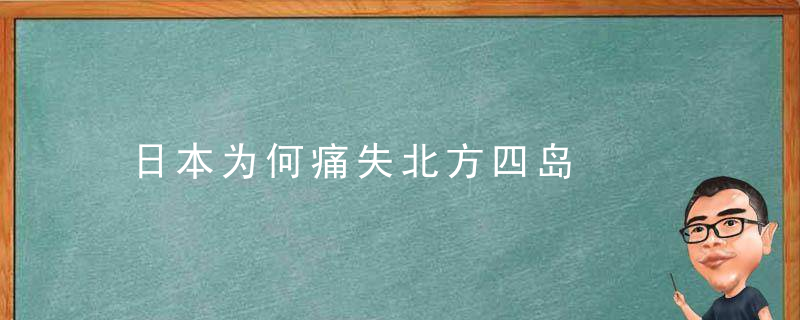
顺时针研习历史,逆时针解毒世界
微信公众号:历史研习社
作者:任逸飞
审核:喵大大 编排/制图:Magician
正文共:8841 字 24 图
预计阅读时间: 23 分钟
最近,日、俄两国争议不断的“北方四岛”(俄方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再起波澜。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俄罗斯萨哈林州州长奥列格·科热米亚科于3月中旬宣布,萨哈林州将与美国工程机械和采矿设备制造巨头卡特彼勒公司合作,在“北方四岛”中的色丹岛新建一座柴油发电站。
▲2017年2月7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加“北方领土日”集会
上述表态立即引发日本朝野的强烈反应,4月4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众议院外务上发言称:“第三国企业在北方四岛从事经济活动违背我国立场,表示非常遗憾。”他同时强调,日、俄双方应当尽早解决四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并缔结和平条约。
“北方四岛”是对太平洋西北部千岛群岛向南延伸部分的四处岛屿——择捉岛、国后岛、色丹岛及齿舞诸岛的总称,总面积有5038.33平方公里。四处岛屿中,择捉岛的面积最大,有3185平方公里。“北方四岛”,连同库页岛(即今萨哈林岛)南部的“桦太”,在二战前曾都是日本领土。然而,随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苏联依据《雅尔塔条约》宣布四岛归属苏联,并旋即派兵予以占领。
▲“北方四岛”
国后、择捉、色丹及齿舞诸岛的地理位置图
在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中,尽管日本正式放弃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领有权,但从未承认过苏联对“北方四岛”的占有。1956年10月,日、苏在莫斯科签署《联合宣言》,苏联曾表示只要未来双方缔结了和平条约,苏联会将齿舞、色丹两岛归还日本,但日本则坚持四岛全部归还后方能缔结条约,双方互不让步,四岛的归属问题由此长期得不到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控制着“北方四岛”,直到今天,日、俄两国依旧没有缔结和平条约,这在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领土争端也成了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大绊脚石。
“北方四岛”争端看似是一个二战的历史遗留问题,可鲜为人知的是,日、俄两国在该地的博弈实际已持续了两三百年。自18世纪末叶起,德川幕府即与沙皇俄国在当时称为“虾夷地”的北海道、北方四岛及库页岛南部发生频繁接触,对于当时推行“锁国”体制,竭力避免与外部世界有过多交往的德川日本来说,在寒冷的北方地带与俄国人的遭遇可谓是惊心动魄,而这些意料之外的碰撞更是对往后日本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7)的早期,今天的北海道并不归属德川幕府直接管辖,当时在北海道活动的主要是原住民阿伊努人(Ayinum),阿伊努人与日本的主体民族大和民族属于完全不同的人种,据考证可能是早期类高加索人的后裔,他们皮肤较黑、毛发浓密、身材短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
▲林子平「三国通覧図説」中所绘的阿伊努人
阿伊努人以渔猎为生,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到16世纪时,其活动区域已远达库页岛和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长久以来,日本人便视这些“非我族类”的人群为外夷,蔑称之为“虾夷”(エゾ),因而阿伊努人活动的区域,包括北海道、库页岛南部、北方四岛和千岛群岛,皆被统称为“虾夷地”(エゾチ)。
“虾夷地”作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进入日本统治阶层的视野。有意思的是,二战以后,为了证明“北方四岛”自古以来便是日本领土,日本曾以绘于1644年由当时位于日本最北部的藩国——松前藩进献给德川家光的一幅古地图《正保御国绘图》作为主要的文献依据。在这幅图中,清晰标注了国后、择捉、齿舞、色丹诸岛是归属于松前藩的。那么,《正保御国绘图》中的信息是否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呢?
▲「蝦夷土人風俗図巻」中所绘的阿伊努人捕猎黑熊的情景
松前藩的前身是日本战国时代活跃于“虾夷地”的蛎崎家,蛎崎氏经过数代经营,至第五代当主蛎崎庆广时,已成为独霸北海道的唯一大名。庆广善于观察政治风向,天正十八年(1590年),趁着丰臣秀吉出兵关东讨伐小田原北条氏的机会,庆广亲自偱海路“上洛”,谒见秀吉,获得了秀吉的信任。
到了文禄二年(1593年),秀吉出征朝鲜,庆广又统领兵马一路跑到肥前名护屋参战,太阁大人显然被庆广的“忠诚”弄得感动不已,立即允诺了蛎崎家对“虾夷地”的支配权,并上表天皇封庆广为从五位下志摩守,并赐“虾夷岛主”朱印状和桐章。可是秀吉不会想到,这个惯于见风使舵的庆广在他过世后不久,便又投靠了德川家康。庆长三年(1598年),庆广改姓“松前”,成为松前藩的初代藩主,德川幕府赐其“黑印状”,再度确认了松前藩对“虾夷地”的控制权,以及与阿伊努人交易的权力,松前藩由此完全垄断了北海道利润丰厚的农产品与渔业贸易。
▲松前城
(松前藩的本城,位于今北海道松前町)
▲「蝦夷地並びに周辺図」局部图
(注意图中松前藩与虾夷地用了不同颜色标注)
尽管松前藩得到幕府的认可,拥有了对“虾夷地”的支配权,可是它能够确实控制的领地基本就没有超出过北海道最南端渡岛半岛的范围,不要说北方四岛,就连北海道的广大土地都完全不在其掌握。因而,到了18世纪后期,像林子平这样的思想家依然认为日本的北部国境在“熊石”(渡岛半岛西侧的熊石町),也就并不令人奇怪了。可见,当时的松前藩不过是在理论上被允许支配北方四岛,这与它实际控制四岛完全是两码事,战后的日本想要用《正保御国绘图》来声张领土权力,着实有些偷梁换柱的嫌疑。
总之,自德川幕府建立以来,便一直借由松前藩来管理“虾夷地”事务,处理与“外夷”阿伊努人间的交往,上述举措又成为幕府在对外政策上构建“锁国”体制的重要环节,其根本目的在于管控风险,避免与外部世界有过多不必要的接触。
▲松平定信像
(位于福岛县白河市南湖公园)
到了18世纪末松平定信担任老中的时代(1787-1793)【注:老中是辅佐将军处理全国政务的僚属,一般有四至五名,按照席次先后,其中一人为首席老中,将军与老同组成了德川幕府的最高决策层】,整个日本的对外关系进一步收缩,传统上曾颇为热络的与朝鲜间的交往已经趋于停滞,对外贸易的港口被限定在长崎一港,且只允许清国和荷兰的船只进入,其余外国船只一律不准靠近日本海岸。
上述的政策转变,如三谷博教授所言,或许与日本在江户中期经济自主性提高,不再需要过多倚赖对外贸易有关。但无可否认,德川日本已决定走上一条自我封闭和自我孤立的道路,面对急速改变中的世界局势,这条道路必然是危机四伏的,而第一个隐患便出现在“虾夷地”。
正是在18世纪,“虾夷地”的平静开始被打破。当大西洋沿岸的西欧诸国派出船队,不远万里开赴东亚,寻找香料、丝绸、茶叶乃至源源不断的财富时,后起之秀俄罗斯帝国也蠢蠢欲动起来。不过,对于大多数俄国人来说,他们前往太平洋的路途似乎更加直截了当,他们只要在自己的国土上一路向东去,翻越乌拉尔山,跨过贝加尔湖,穿过西伯利亚绵延的森林,放眼望去无不是唾手可得的新疆土。
▲堪察加地区和千岛群岛总图
(1826年,由V.P.帕迪谢夫(V.P. Piadyshev)上校编制)
18世纪初,远东的堪察加半岛已出现了俄国人的身影。1697年,哥萨克头目阿特拉索夫(Vladimir Atlasov, 1661-1711)首次带队“探索”了堪察加半岛全境,在半岛南端,他们已然能够望见海的另一侧千岛群岛高耸的岩石了。归途中,阿特拉索夫在堪察加当地人的部落里发现了一个名叫传兵卫的日本商人,传兵卫似乎是因船只海难漂流至半岛上的,阿特拉索夫向他打听了许多有关日本的情况,最后还带他去谒见了沙皇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大为兴奋,以此为契机,1705年,沙皇下令在圣彼得堡开办日语学校,为搜集日本情报培养人才。传兵卫成为了俄国了解日本这个国家的起点。
此后,俄国稳步扩张着其在堪察加和千岛群岛的影响力。1719年,彼得大帝谕令“探险队员”们仔细勘查千岛群岛,找到通往日本的航道。1721年,由地质学家叶夫列莫夫(Ivan Yevreinov, 1694-1724)率领的俄国探险队勘查了千岛群岛舍子古丹岛在内的14座岛屿,并将群岛北部划入俄国领土。1738年,海军中校斯潘贝格(Martin Spangberg)率领的俄国船队又一路向南直至色丹岛,他们勘查了千岛群岛共29座岛屿,并一一用俄语为其命名。
▲千岛群岛中部得抚岛方位简图
1760年之后,俄国船只造访千岛群岛的频次明显增加了。俄国人在岛上树立十字架,搭建移民定居点,还诱骗当地的阿伊努人受洗,归化俄罗斯。许多千岛群岛的阿伊努人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入了俄罗斯籍,被迫承受苛重的“毛皮税”。1771年,得抚岛与择捉岛上的阿伊努人为了反抗俄人的压迫发起暴动,有21名俄国税吏在这起冲突中被杀。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1779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布诏令,宣布千岛群岛上凡未经圣彼得堡许可的实物税一律废除。
饶富意味的是,就在沙皇俄国在千岛群岛中部做长期经营的打算之时,18世纪后半叶的德川幕府也在着手强化其对“虾夷地”的控制能力。早在松平定信的前任田沼意次担任老中的时期(1767-1786),一些日本知识分子便注意到了俄国正从北部进入虾夷地的状况。天明三年(1783年),工藤平助写成《赤虾夷风说考》一书,在书中,他提出日本应当积极开发虾夷地资源,并与俄国展开贸易。
▲「赤蝦夷風説考」
《赤虾夷风说考》被进献给了田沼意次,启发了他急速转变对虾夷地的政策。天明四年(1784年),幕府开始从松前藩手中收回虾夷地的管理权,直接介入当地事务,并且向北海道乃至北方四岛各地派遣官员,可是上述举措却激化了日本人与阿伊努人间本就十分紧张的关系,幕府对待阿伊努人并不比沙皇俄国更仁慈,宽政元年(1789年)五月,国后岛上的阿伊努人造反,杀死日本官吏与守卫几十人,幕府最后不得不再度依靠松前藩的武装去镇压反乱,暴动直到七月才被平息下去,日本人称其为“宽政虾夷蜂起”。
受这场暴动的影响,继任老中的松平定信头一桩事便是叫停田沼意次的虾夷开发计划。松平恢复了松前藩在处理虾夷事务中的地位,在他看来,与俄国开展贸易不光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十分危险,将严重危害“锁国”体制,现在的当务之急应是如何增强海岸防卫,尽一切可能去防止与俄国船只发生冲突。本着上述思路,松平接任“海边御备御用挂”和“虾夷地御用”两项职务,亲自负责北部沿海的防务。
然而,无论松平定信怎样严防死守,在日、俄两国同时从南、北两个方向不断压缩阿伊努人活动空间的态势下,整个虾夷地作为缓冲地带的价值已不复存在,双方的直接接触变得不可避免。
宽政四年(1792年)十月,一艘俄国军舰在北海道东北角的根室靠岸了,来者是奉叶卡捷琳娜女皇之命前来谋求与日本建立通商关系的俄国使节亚当·拉克斯曼(Adam Laxman, 1766-1806),在他的船上还载着两位特殊人物——因海难流落异国的日本漂流民大黑屋幸太夫与矶吉。拉克斯曼一上岸便被松前藩的人团团围住,他马上表明来意,说此次到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两个漂流民送回母国,因而松前藩起初对待拉克斯曼的态度尚算友好。
▲日本人笔下的亚当·拉克斯曼
可没过多久,当拉克斯曼宣称,他想要亲自护送漂流民前往江户,作为交换,幕府当与俄国订立开港通商条约后,松前藩的官员们紧张起来,他们火速把情况通报给松平定信。很快,一支由两名信使与五百名守卫组成的队伍从江户出发开赴根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执行松平定信的命令,阻止俄人的一切妄动。
信使抵达后向拉克斯曼传达了松平定信的意见:根室不是俄船可以停靠以及讨论问题的合适地点,如果拉克斯曼确实有事情要与日方讨论,可以离开他的船,步行前往松前城。这无疑是拖延时间的伎俩,立刻就被拉克斯曼回绝,不过眼见日方人多势众,拉克斯曼最后还是勉强同意转泊箱馆(今函馆),再由日本卫队护送,前往松前城。
之后的一年中,拉克斯曼便一直呆在松前城,日本人天天好酒好菜招待他,可对于通商一节却始终只字不提。到了宽政五年(1793年)六月,松平定信向拉克斯曼修书一封,表达了其最后见解:俄国乃“素无通信之国”,日本对待这种国家来的船只,不是扣留拘押,便是武装驱离,“此为亘古以来之国法”,通商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时的拉克斯曼也早失掉了与幕府谈判的劲头,只好两手空空离开了日本。
▲「魯西亜船東蝦夷来航図」中所绘的拉克斯曼来访船只
▲大槻茂質「ヲロシヤ船渡来一件」中收录的松平定信发放的信牌
不过,松平在信的末尾有所转圜,他暗示拉克斯曼:日本对外贸易的唯一港口是长崎,如果俄船愿意去长崎,那么通商的问题仍是能从长计议的,他还顺带发给拉克斯曼允许进入长崎港的信牌。松平作出这番表态的原因或许在于不想过多激怒俄国,以免日本蒙受损失,不过这也为此后俄船的再度来访埋下了伏笔。
果不其然,十一年后的文化元年(1804年),第二位俄国特使雷扎诺夫(Nikolai Rezanov, 1764-1807)携带着拉克斯曼当年取回的信牌乘船驶抵长崎。雷扎诺夫要求前往江户承递国书,并开始通商。此时担任老中的户田氏教丝毫没有要改变松平定信确立的“锁国”政策的意愿,翌年四月,幕府全盘否决了雷扎诺夫的所有要求,勒令其离开日本。在发给俄国人的通告中,户田重申:与日本“通信通商之国”只有“唐山、朝鲜、琉球、红毛”四国,除此之外,哪怕是再增加一个国家都是不可能的。
雷扎诺夫的脾气没有拉克斯曼那么和蔼,当发觉自己千里迢迢跑到这个东瀛岛国却被“放了鸽子”的时候,不禁大为光火,他在返回堪察加半岛后便决定派部下伏沃斯托夫(Chwostoff)和达维多夫(Davydov)驾驶武装船只去骚扰日本控制的“虾夷地”。
▲大槻茂質「文化甲子魯西亜国王書翰和解他襍録」中收录的沙皇国书
文化三年(1806年)十月,伏沃斯托夫等人袭击了松前藩设立在库页岛久春古丹的税务所,抓走守卫人员,抢了600袋大米和大批物资。翌年,他们又如法炮制,突袭了色丹岛上的日本警备所,击溃了全部警备队。伏沃斯托夫威胁称,俄国会在1808年再派使节来日本,幕府最好对通商的问题有个明确的态度。
俄人的进击令幕府惊恐万状,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幕府紧急加强“虾夷地”防卫,在原有的南部、轻津两藩兵力的基础上,新调派仙台、会津藩前往北境支援。同时,幕府向全国发布对俄国船只的武力驱逐令,江户、长崎等要害地点也相应加强了警戒,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不过,伏沃斯托夫声称的使节最终并没有出现,日本的临战体制也旋即解除了,然而三年后的一起突发事件却使两方刚刚趋于平稳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文化八年(1811年),一艘俄国测量船在国后岛靠岸,船长戈洛夫宁(Vasily Golovnin, 1776-1831)刚一登陆,便被当地的日本守备队逮捕。
▲「俄羅斯人生捕之図」中所绘的戈洛夫宁及其船员被捕的情景
(画面中身着黑衣,手执卷轴者为戈洛夫宁)
德川幕府怀疑戈洛夫宁同先前的伏沃斯托夫是一伙的,拒绝将其释放。为了迫使日方尽快放人,戈洛夫宁的副手里科尔德(Pyotr Ricord, 1776-1855)于1812年向色丹岛发动袭击,还抓获了岛上的日本富豪——特许供货商高田屋嘉兵卫,上述举动使日、俄两国再度逼近了战争边缘。
幸而,事情很快便峰回路转了。日、俄双方都意识到对方并无扩大事态的企图,特别是此时的俄国正深陷拿破仑战争无暇东顾,也希望能尽早解决争端。1813年,双方达成协议,互换俘虏。与此同时,两边也乘此机会讨论了千岛群岛的划界问题。德川幕府提议,日、俄各以择捉岛与新知岛为界,而两岛之间的得抚岛、武鲁顿岛等地则作为中立地带。俄方对这一提议不置可否,仅表示来年会派使节到择捉岛给日方答复,不过此后俄国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这样,直到四十年后的嘉永六年(1853年)七月,俄国使节普提雅廷(Yevfimiy Putyatin, 1803-1883)紧随美国佩里舰队叩关长崎,日、俄间不再有任何来往。自伏沃斯托夫袭击库页岛久春古丹开始,双方在虾夷地的博弈终于告一段落,日本史书中将这段与俄国周旋的艰难时光称为“北寇八年”。
“北寇”虽然不再来了,但其给德川日本造成的巨大冲击与影响却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俄国频繁进出“虾夷地”的最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幕府将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虾夷地全数领土化的过程。宽政十一年(1799年),以色丹岛为界,幕府采纳户田氏教的意见将东虾夷地收归国有,并于各处配置守备队。文化四年(1807年),幕府再将西虾夷地也收为直辖地,松前藩则被移至本州,不再管理虾夷事务。
▲「従東蝦夷地クナシリ島至魯西亜国カムシカツトカ大畧地図」
中绘制的择捉岛
对于北方四岛中面积最大的择捉岛,幕府于1799年授意御用商人高田屋嘉兵卫(戈洛夫宁事件中被里科尔德捕获)在岛上开辟渔场,并委派常驻官员,竖起“天长地久大日本属岛”的标记,宣示政治存在。尽管日、俄双方没能在戈洛夫宁事件后就千岛群岛的划界问题达成共识,但从之后俄国撤退得抚岛驻扎人口的举动看,其对日本占有择捉岛的事实也表示了默许。
“北寇”的骤然而至也令幕府中的一些人意识到外部世界或许发生了巨大变化,搜集海外情报尤其是与俄国接壤的日本北部地区的信息成为当务之急。在过去, 荷兰作为与江户日本保持外交关系的唯一欧洲国家,其每年向幕府提供的“风说书”始终是幕府了解欧洲以及东、西印度情况的唯一信息来源。然而在应对俄国的问题上,幕府逐渐发觉荷兰“风说书”并不能够提供完整和准确的资讯,日本必须想方法开辟自己的信息搜集渠道。
幕府首先想到的便是从那些由俄国使节送回的日本漂流民口中打探消息。被拉克斯曼送回的大黑屋幸太夫和矶吉接受了兰学家桂川甫周的询问,幸太夫在俄罗斯生活了十一年,掌握了大量一手情报,桂川甫周将询问所得写成书,并于宽政六年(1794年)呈交幕府,书中对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社会与民俗都有详细记述。此后,幕府又组织人手对雷扎诺夫送还的仙台漂流民津太夫采集讯息,编写成《环海异闻》一书。
▲桂川甫周「漂民御覧之記」中与幸太夫、矶吉两人的问答
除了从漂流民处搜集信息,幕府还派出考察队前往北部进行实地调查,行踪远达择捉岛与库页岛中部。随着虾夷地领土化的稳步推进,自1799年开始,幕府一改过去只派遣低级官员带队考察的做法,改由监察官“目付”与将军的亲卫队长“书院番头”组成的高规格考察团前往虾夷地。这其中,考察团员近藤重藏结合自己的实地见闻,比照清国与荷兰书籍中的内容,写成《东西边要分界图考》一书,于1804年呈交幕府。这本书很快成为幕府处理雷扎诺夫来访的重要参考资料。
对虾夷地的考察还催生出一个副产品,它有力推动了当时德川日本对北部地区的实地测绘,并渐次及于对所有日本海岸的测绘。最早展开这方面工作的是伊能忠敬,他在师从“天文方”(相当于中国古代的钦天监)负责官员高桥至时的时候,就反复表达过希望能运用所学到的天文学知识,画出精确度更高的实测地图。
在高桥向幕府请示之后,宽政十二年(1800年),伊能忠敬被获准首先执行对虾夷地的测绘。此后这项工程逐渐扩大至整个日本海岸,虾夷地的测绘工作则交由伊能忠敬的弟子间宫林藏继续完成。到了文政四年(1821年),伊能忠敬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问世,《全图》包含了二百余张分图,其质量之上乘、精确度之高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水平。
▲伊能忠敬「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図」局部图
(图中所绘为国后岛)
▲「蝦夷図」
「蝦夷図」,集中体现了伊能忠敬与间宫林藏的测量成果,1826年,高桥至时之子高桥景保将此图赠与了在荷兰商馆工作的德籍医生西博尔德,高桥景保后因“泄露机密”被幕府处死
总之,自从俄国船只进入虾夷地后,出于有效掌握俄方动向的目的,日本朝野上下涌现出了一批对外部世界充满兴趣的人物,他们积极搜集海外情报,通过询问漂流民、实地勘察或者地图测绘,江户中晚期的日本对外界的认知正变得不断丰富。
然而,有意思的是,知识的增长却并没有驱使幕府想办法改变“锁国”体制,相反的,幕府和当时日本一大批知识分子都主张加大“锁国”的力度,该怎样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选择呢?三谷博教授在《黒船来航》一书中便指出,正是因为日本已经了解到了“西力东侵”的巨大威力,才会决定用强化“锁国”的方式来躲避危险,一直到1853年佩里叩关,日本人才终于意识到,西方的强大力量是躲无可躲的,这才在最后关头走向“开国”。
与同时期的满清和朝鲜不同,日本在西方的压力下实现“开国”,并成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看似幸运,其实与日本早在佩里叩关以前就对如何应对西方有了较为充足的知识储备有关。
而这些知识的取得,与所谓的“北寇八年”是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可以说,假若没有这些前期的知识积累,近代日本的维新之路一定不会那么顺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与1853年的“黑船”相比,或许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进入虾夷地才算是诱发日本“开国”的真正触媒。
两百多年过去,曾经在江户时代立起过“天长地久大日本属岛”标记的“北方四岛”重新成了俄罗斯的地盘,虽然今天的日本人大可不必再目俄人为“北寇”,但要想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中顺利解决四岛的领土争端,恐怕尚需要付出比德川幕府时更多的智慧。
参考文献:
[1][日]三谷博:《黑船来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2]Marius B.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Marcia Yonemo. Mapping Early Modern Japan: Space, Place, and Culture in the Tokugawa Period (1603-186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4]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数据库.
[5]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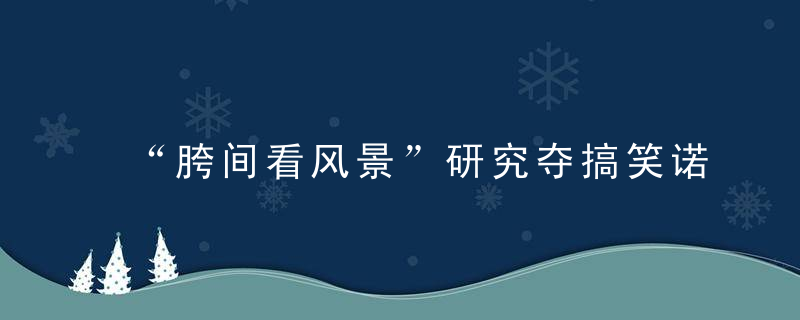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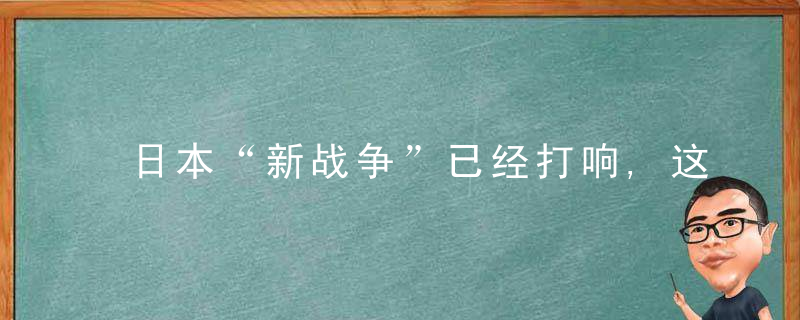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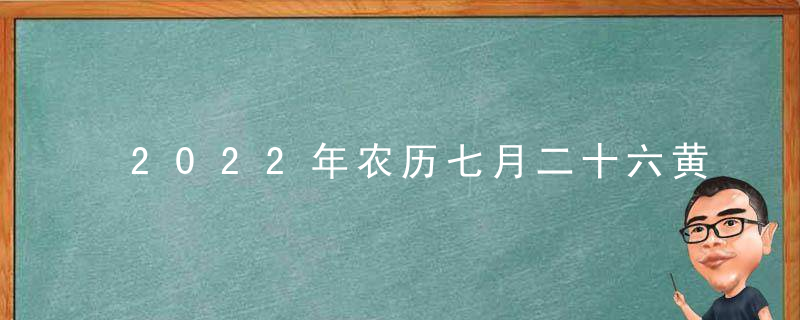


施工.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