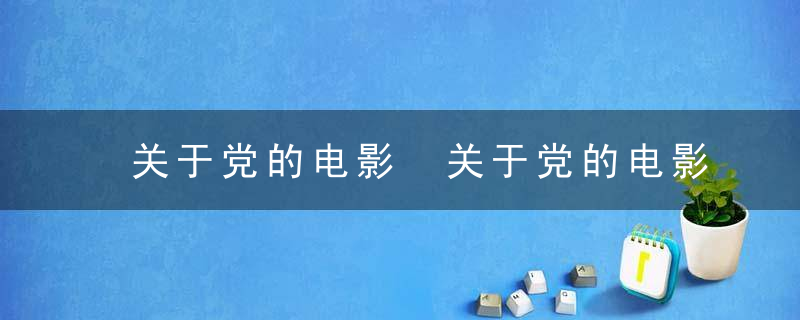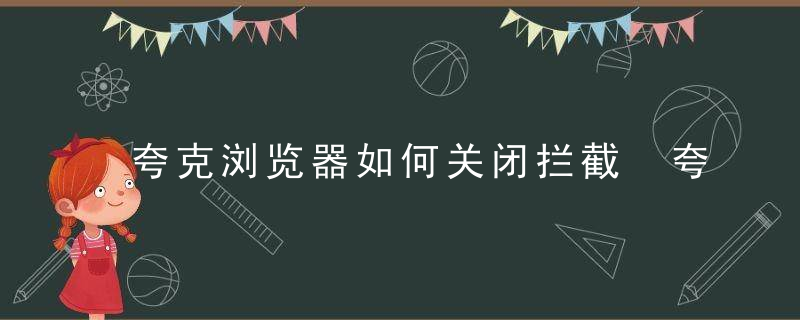干嚼炒米

食物不光关乎热量,还关乎心灵与历史。我干嚼炒米的时候,内心的图景自动切换到科尔沁草原。
现在时兴不吃晚饭,我也逢迎这个时髦,以期降低血脂。但我晚上会饿,学名叫饥饿。有一句成语叫啼饥号寒,说的没有错。饥可以把人逼到哭啼的境地。血液里的血糖下降到一定程度,会让人哭。我不吃晚餐虽未哭,但腹鸣如雷,这算在肠子在肚子里哭,越想睡觉,肚子里的锣鼓队敲打得越厉害。咕——噜噜噜噜,鼓声在腹腔内横着窜完竖着窜。勉强入睡之后,梦又来捣乱,梦中下馆子,下饺子馆,下海鲜馆,饭到嘴边每每吃不进嘴里,比如脚下绊倒,又比如天上有炸弹掉下来。
后来我在睡前吃一点炒米,腹之啼饥与梦中窜馆子的事情都偃旗息鼓。我还是不准备在晚上吃正餐,炒米正好满足这一需求。
炒米是把糜子米炒熟之后干吃的食物,一把把用手抓着往嘴里放,没有汤汤水水,干嚼。我把黄澄澄的炒米放在茶末釉(青中带黄那种颜色)的瓷碗里,手抓一把放进去,一捻捻送嘴里解饿。
解饿归解饿,干嚼炒米耗费时光,要边嚼边读报或读基本上看不懂的物理学书籍。所谓炒米是用铁锅焙米,把生糜子米放锅里,锅底加干牛粪饼加热。牛粪饼火好得很,如木炭一样猛烈。这是指牧区,在城里用液化气炒糜子米其味道营养与牛粪饼与羊粪蛋子作燃料无差别。糜子米的水分焙干泛出微微的焦黄色,熟也。营养学将这一种加热称为“糊化”,食之更容易转化为葡萄糖。但炒米很硬。硬不硬,你站在干嚼炒米者的身边就听到,刷——,刷——,如嚼沙子,或者嚼玻璃。干嚼炒米者不仅牙齿好(这是在表场我自己)咬肌也好(这也是表扬我自己)在动物界,咬肌发达的是食肉性猛兽,如虎豹豺狼,虎可叼一只体重200公斤的公野猪窜过4米宽的山涧,其咬肌非同寻常,咬住人腿喀嚓一下可把腿咬成两截。我干嚼炒米嚼了半年之后,牙齿咬肌虽然比不上老虎,但我自己评估跟狼差不多。一次在单位食堂吃饭,我比较饿了,一口将一块排骨生生咬断,桌对面的人惊得说不出话来,端盘子上别的桌吃去了,他说他不配和有我这样牙齿的人同桌吃饭。
牧区的人并不干嚼炒米,他们也不看报纸和物理学课本。内蒙古人吃炒米一用牛奶浸泡,二用奶茶或红茶浸泡,放进红白糖,奶豆腐,一点点黄油与炼乳,泡到略软不硬食用。干力气活的成年人吃三把或四把米,女人吃两把米,小孩一把可也。“把”就是用自己的手抓米,有准儿。
炒米进胃里膨胀,因此解饿。我以为,炒米应该是军粮,跟新疆的馕差不多。它干燥、保存期长,可以与任何液体相搅拌。炒米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与内蒙古人食用的肉类、砖茶、奶食品构成这个种族的食物基础。我猜想,在蒙古大军征服汉地与欧洲的漫长道路上,行囊中的粮食应该有炒米。军士们在行军中抵御饥饿时,也会干嚼炒米,在战马上或雪地里,或夜里的一切地方。
我祖籍是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那里的人习惯在沙地种植糜子。沙漠里不生长什么东西,但长糜子。我老家的沙子和近年土地沙化形成的沙子不一样,它是洁白的大粒沙子,如同砂糖那样,这里生长的糜子炒成炒米最好吃,香甜嘣脆。赤峰的炒米个小色黄,硬而不脆,也不怎么香。我老家胡四台的炒米个大色白,如美人一般。这么好的炒米是大自然的恩典。如同这里的沙漠是大自然的恩典。沙漠里有沙漠才有的湖水和野鸭,生长沙里的植物。这里的民歌常常提到“沙坨子”。而它最杰出的物产之一就是炒米。
我第一次回到老家——哲里木盟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我大伯家待客的榆木小黑桌上放着一碟子红糖、一碟子奶豆腐、一碟子黄油和一大碗炒米。我当时看不懂炒米在这里搞什么,以为它是生米,怎么会混进点心里呢?尔后捻一把放嘴里“咯嘣”一嚼,从此爱上了它。
一位医生说:“你就是你吃下的食物。”是的,食物不光关乎热量,还关乎心灵与历史。我干嚼炒米的时候,内心的图景自动切换到科尔沁草原,那里有牛粪与红茶的气味,有白沙坨子和轻佻诙谐的哲里木情歌。那里的人红脸膛、宽肩膀,谦卑而激烈。我的亲戚中有黄眼睛、灰眼睛,甚至绿眼睛的人,但我们同属一个家族,是被炒米养大的人们。
关于我们:
本公众号乃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的官方微信,《夜光杯》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副刊,在微信平台,我们将以全新的面貌继续陪伴您。欢迎免费订阅,我们将每日精选两篇新鲜出炉的佳作推送到您的手机。所有文章皆为《夜光杯》作者原创,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