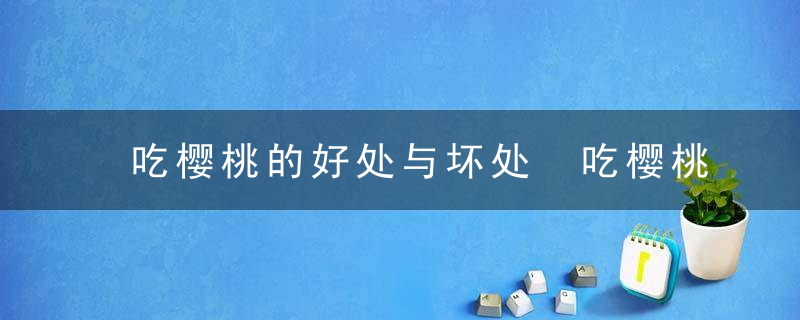《礼记》全译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一书之得名《礼记》,始于西汉。如《汉书·韦玄成传》云:“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欲议曰:《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在西汉,《礼记》亦单称《礼》,或单称《记》。如《汉书·孔光传》云:“上于是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王根,皆引入禁中,议中山、定陶王谁宜为嗣者。方进、王根以为,定陶王帝弟之子。《礼》曰:‘昆弟之子犹子也。’定陶王宜为嗣。”又《通典》卷八十三引戴圣《石渠礼论》云;“闻人通汉问曰:‘《记》曰: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皆不能明。”按《孔光传》所谓“《礼》曰”云云,见《礼记·檀弓上》;《石渠礼论》所谓“《记》曰”云云,见《礼记·杂记上》。魏晋以后,《礼记》更有《小戴礼》之称。如《经典释文·序录》引晋司空长史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我在这里引证陈邵的话,其意仅仅在于指出魏晋时已有《小戴礼》之称,至于“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谓《小戴礼》”的说法,今日学者已悉知其误,兹不具论。麻烦在于,《礼》、《礼记》、《小戴礼》之名,在两汉时,并非为四十九篇之《礼记》一书所专用,十七篇《仪礼》,彼时也有《礼》、《礼记》、《小戴礼》之称。皮锡瑞《经学通论》云:“汉所谓《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而汉不名《仪礼》。专主经言,则曰《礼经》;合记而言,则曰《礼记》。许慎[shèn] 、卢植所称《礼记》,皆即《仪礼》与篇中之记,非今四十九篇之《礼记》也。”分辨颇为明晰。《后汉书·儒林传》中再三提到的《小戴礼》,是指戴圣所传的十七篇《仪礼》,也不是四十九篇的《礼记》。明白了这种二书共名的历史现象,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认识上的错误。之所以产生这种二书共名现象,从内因上讲,主要是由于《仪礼》和《礼记》二书的内容紧密相关。论其本源,《礼》、《礼记》、《小戴礼》之称,本属于十七篇之《仪礼》,后来渐次为四十九篇之《礼记》所夺。故黄以周《礼书通故》卷一云:“自魏晋号四十九篇为《礼记》,亦谓之《小戴礼》,而东汉十七篇之名《礼记》、名《小戴礼》者,又为四十九篇《戴记》所夺,于是别号之为《仪礼》。”二、《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与作者就十七篇之《仪礼》与四十九篇之《礼记》而言,二者在两汉的地位甚不相伟。当时立于学官的《礼》,是十七篇之《仪礼》,不是四十九篇之《礼记》。在两汉时,《仪礼》是经,而《礼记》不是经,只不过是《仪礼》的附庸而已。今之所谓《礼记》者,“礼”,指《礼经》,即今之《仪礼》;“记”,犹如学习《礼经》时的笔记,它显然不是正式教材,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可以对经文进行某种解释、补充或归纳。《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郑玄认为是西汉的经学家戴圣。他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其编者,郑玄的这个说法便是最早最权威的了。现代学者洪业先生对此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今本《礼记》虽与戴圣不无瓜葛,但并非戴圣一人所编。而是在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zhěn)域渐灭,而《记》文之钞合渐多,不必为一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详见其《礼记引得序》。其说颇有益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但尚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盖证据犹不足也。《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礼记》作疏的孔颖达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人就更不消说了。除了个别篇的作者可以指实以外,大多数篇的作者无法指实。孔颖达就老实地承认:“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①。”《汉书·艺文志》礼家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可以说是今本《礼记》的最主要的源头,说到这百三十一篇的作者,班固也只是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既然我们无法逐篇地指实作者,那么,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恐怕还是可取的。“七十子后学者”这一概念所含的历史跨度甚大,可以说上起春秋,下迄西汉(如果采用洪业先生之说,则是下迄东汉),从亲聆孔子教诲的七十子之徒,到西汉的儒者,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指出,《礼记》中有许多“孔子曰”、“子曰”、“子言之”一类的字眼,有的整篇都是“子曰”、“子言之”。孔颖达认为这都是孔子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对此,梁启超曾加以澄清:“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情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因每托孔子以自重。要之,《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需慎择也②。”注:①《礼记正义》卷一;②《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三、《礼记》的内容与《礼记》的地位的日益提高《礼记》四十九篇的内容相当杂,据刘向《别录》的分类,或属制度,或属通论,或属明堂阴阳,或属丧服,或属世子法,或属祭祀,或属子法,或属乐记,或属吉事,共九类,每类的篇数也多寡不等。因其内容杂,所以被人们看作是一部儒家的礼学杂编。从今天来看,它是我们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宝贵资料。其中固然有糟粕,但也不乏精华。举例来说,其《礼运》篇中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深情描述,《学记》篇中关于教学相长、尊师重教的阐述,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略有减色。还有不少章节,富于哲理,意味隽永。继承并进一步发掘《礼记》的积极成分,也是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我们已经知道,西汉时的《礼记》只是《仪礼》的附庸,《仪礼》是经,立于学官,《礼记》则无此殊荣。但就其对西汉社会政治的影响来看,恐怕在当时《礼记》已经超过了《仪礼》,而西汉后期尤其如此。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朝廷在讨论诸如祭祀、宗庙、立储等重大问题时,往往援引《礼记》为说。翻阅《汉书》,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开头举了两个《汉书》的例子,由此可见一斑。王莽改制,其理论根据之一便是《礼记》,尤其是《礼记》的《王制》。即令稍事翻检《汉书·王莽传》,也不难看出此点。至于《礼记》对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和《列女传》中都不难找出痕迹。从以上事实中笔者得出这样一种观感,即在西汉时,《礼记》虽然无经之名,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有了经的实。东汉末年,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这件事可以看作是《礼记》脱离《仪礼》而独立的开始。从此以后,《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仪礼》则日趋式微。曹魏时,《礼记》已立有博士。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①。”这说明当时的学者热衷于《礼记》之学,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到了唐代,《礼记》正式进入经的行列。此时,《礼记》一书,“人皆竞读”②;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对于《仪礼》来说,真是每况愈下。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干脆就废掉了《仪礼》。从此以后,作为经书的《仪礼》,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了。《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从古到今,学者无不认为《仪礼》难读。在西汉,连礼学专家徐襄也只能做到“善为颂,不能通经”③。所谓“颂”,是指具体的礼节动作;所谓“经”,即指《仪礼》。唐代的韩愈在《读仪礼》一文中曾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清代的阮元在《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中也说:“《仪礼》最为难读。”我认为,《礼记》的由附庸变为大国,《仪礼》的由大国而日趋衰落,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仪礼》比较难读来解释。如果说难读,“佶屈聱牙”(jí
qū áo yá
)的《尚书》在《十三经》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但其经典地位却始终岿然不动。我想,原因主要在于《礼记》与《仪礼》二书的内容不同,并因此而影响了人们的对其取舍。《仪礼》十七篇,篇篇都是一大堆繁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有雷同。《乐记》说:“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仪礼》十七篇,除《丧服》一篇外,都是这种“礼之末节”。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仪礼》的内容极少具有可塑性,它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仪礼》的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xǐ] 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则不然,它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它也同时论述了这些末节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主要是讲理论,它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地位日益上升。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引《礼记补疏序》)。”语似偏颇,却也道出了《礼记》日益走红的根本原因。《礼记》的日益走红已如上述,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似乎《礼记》的风头还没有出够。这就要说到《大学》和《中庸》。《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北宋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到了南宋时,朱熹就将这两篇纳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以后,随着朱熹《四书》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而风行于世,《大学》、《中庸》两篇的身价也随之倍增,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家喻户晓之书。这样以来,说到《五经》,有《礼记》;说到《四书》,也涉及《礼记》,真是风头十足。注:①《北史·儒林传上》;②《经学历史》(中华书局本210页);③《汉书·儒林传》;④《孝经,广要道章》。四、《礼记》的郑注和孔疏今本《礼记》为郑玄所注。郑玄(127一200),字康成,尝遍注群经,为一代大儒。《后汉书》有传,兹不赘。在郑玄之前,马融、卢植都曾为《礼记》作注。郑玄与卢植同为马融弟子。马、卢之注不传,清人有辑本,但所得也不多。卢植之注,郑玄注《檀弓》“晋献公之丧”节尚偶一用之,而马融之注,则郑注未尝一引。《礼记》之学,从魏晋到明清,其间除了西晋时曾一度使用王肃注、明代曾一度使用陈澔《礼记集说》外,其余各个朝代,无不奉郑注为圭臬。郑玄的注,文简义明,可以说是索解《礼记》的一把钥匙。但毋庸讳言,郑注也有其不足之处。有些注解错误,郑玄本人也知道,但书已作成,追改无及。例如《坊记》注引《卫风·燕燕》之诗,郑注以为夫人定姜之诗,而笺《诗》又以为庄姜之诗。其弟子问其故,郑答云:“注《记》时执就卢君,后得《毛传》,乃改之①。”王肃的《礼记》注,务在与郑玄立异。王肃的做法虽然是意气用事,门户之争,但所攻郑氏诸点,也并非无一是处。如果我们跳出经学家的圈子,用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那么,郑注的缺点首先倒不在于某些字句的训诂错误,而在于他作为封建社会经学家的某些错误观点和理论。例如,他笃信《周礼》为周公所作,从而笃信《周礼》为周制,而《礼记》中所载制度凡与《周礼》异者,即推之为殷夏之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造成是非颠倒。另外郑注往往征引纬书(汉代依托儒家经义宣扬符箓瑞应占验之书,相对于经书,故为纬书。)为说,而纬书之说类多荒诞,这反映了他的宗教神学思想。《礼记正义》(后来习称《礼记疏》)的作者是孔颖达。孔颖达(574—648),字仲远,一云仲达,两《唐书》均有传。《旧唐书·儒学传》:“太宗以儒学多门,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据《唐会要》,《五经》义疏成书于贞观十二年(638),初名《义赞》,有诏改为《五经正义》。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又经过一次覆审。后来,由于太学博士马嘉运驳正此书之失,太宗又命孔颖达更为详定,功未就而孔颖达去世。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考正之,就加增损。“永徽四年(653),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②。皮锡瑞评论此事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注:①《郑志》卷中;②《唐会要》卷七十七。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经学之又一变也①。”《礼记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凡七十卷。其作者一般只说是孔颖达,实际上作者多人。只是由于孔颖达年辈在先,名位独重,所以署名只有孔颖达一人之名,他人之名皆在“等”字之中。南北朝时,学者传习的都是郑注《礼记》,孔颖达等作《礼记正义》,也不例外。《礼记正义》之作,并非空无依傍,一切从头做起。恰恰相反,它是在南北朝学者所作现成义疏的基础上加以剪裁删理。至于如何剪裁删理,详见孔颖达《礼记正义序》,此不赘。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最大特点是申郑,即不随便与郑注立异。他在《正义》中不止一次地宣称:“《礼》是郑学,今申郑义②。”“此等并非郑义,今所不取③。”充分体现了“疏不破注”这一特色。当然,这种作法,利弊兼有。郑注说对了的,孔也随之而对;而郑注说错了的,孔也随之而错。应该指出,说孔疏的最大的特点是申郑,并不是绝对的。如果郑注有明显违背经文之处,孔颖达则舍郑而从经。这样的情况不少。例如,郑注《坊记》曰:“三岁曰新田。”但这和《尔雅》“二岁曰新田”之文明显相违,所以孔氏就说郑注错了。这种不一味盲从的做法,较之魏晋时某些学者“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的做法就显得态度认真些。孔颖达《礼记正义》的另一大特点是文繁。换言之,就是罗嗦。对于孔疏的文繁,赞誉者有之,非毁者有之。窃以为二者均有道理,并不矛盾。何者?如果繁其所当繁,那自然就是优点。这正如皮锡瑞所论:“孔颖达于《三礼》,唯疏《礼记》,实贯穿《三礼》及诸经。有因《记》一二语而作疏至数千言者。如《王制》‘三公一命卷’云云,疏四千余字;‘比年一小聘’云云,疏二千余字。注:①《经学历史198页》;②((礼记正义》卷五十;③((礼记正义》卷四十二。元元本本,殚见洽闻(dān jiàn qià wén
〖解释〗殚:尽,完全;洽:广博。该见的都见过了,该听的都听过了。形容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出处〗汉·班固《西都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
),又非好为繁博也。学者熟玩《礼记注疏》,非止能通《礼记》,且可兼通群经①。”如果繁其所不当繁,那自然就是缺点。这正如臧琳所讥:“有一二言意已明了者,加之数十百言,意反晦涩②。”注:①《经学通论·三礼》;②《经义杂记》。五、有关译注工作的交代首先交代一下所采用的《礼记》经文底本。我们采用的《礼记》经文出自八行本。八行本是注疏合刻之祖。之所以叫做八行本,是因为此本每半页八行。八行本,又叫越本,这是因为此本初刊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市);又叫黄唐本,这是因为主持此本初刻的官员叫黄唐。八行本初刻于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是《礼记》注疏合刻最早的本子,也是最好的本子。此本在清代是孤本,陈鳣(zhān)《经籍跋文》说它“诚希世之宝也”。阮元在校勘《礼记注疏》时,固已心知八行本之善,他本莫及,无奈此本在当时为海内孤本,阮元但闻其名而未尝一见,盖欲求之而不可得,不得已而求其次,乃以十行本为底本。这是时代造成的遗憾。潘宗周《礼记正义校勘记》说:“《礼记注疏》得阮校而后信为可读,及校此本(按:谓八行本),乃敢言《礼记注疏》以此本为最不贻误读者。”信哉斯言!我们曾经把八行本与今日通行的阮本对校了一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八行本不仅在注文、疏文方面优于阮本,而且在经文方面也优于阮本。例如,《檀弓下》“不殆于用人乎哉”,阮本脱“不”字;《月令》“山陵不收”,阮本误作“山林不收”;同篇“度有短长”,阮本作“度有长短”,而王引之《经义述闻》认为作“短长”为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采用八行本,自然就省掉了不少不必要的校勘记。或曰:为什么不用唐文宗开成年间的《唐石经》本呢?答曰:由于岁月侵蚀和后人磨改,今存《唐石经》已大失旧貌。冯登府《唐石经考异》云:“开成去古未远,犹为纯备。然几经后人之手,一误于乾符之修改,再误于后梁之补刊,三误于北宋之添注,四误于尧惠之谬作,遂失郑唐之旧。”这是一。另外,《礼记》中的《月令》一篇,《唐石经》用的是唐玄宗《御删定礼记月令》,和汉人所传的《月令》在文字上有许多不同。这是二。其次交代一下我们是怎样译注的。除了要遵守出版社规定的全书体例外,在注解时,脑子里始终存在着颜师古注《汉书》时的几句话:“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申,衍而通之,使皆备悉。若泛说非当,芜词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冗,只秽篇籍,盖无取焉。旧所阙漏,未尝解说,普更详释,无不洽通①。”我们也知道这样做有点悬得太高,自不量力;但我们还知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的道理。所以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不自欺,不欺人。至于实际上究竟做到了什么地步,不敢自必,热诚欢迎读者批评。说到《礼记》的译文,近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最早是台湾,接着是大陆,就像雨后春笋似的,令人目不暇接。尽管其中良莠不齐,但不管怎么说,都是走在我们前面的先行者,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情简直就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但俗话说文贵创新,有道是见仁见智,人心不同如其面,所以我们的译文还是我们自己的。至于成败利钝,不敢知,幸读者明鉴,不吝赐教。本书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