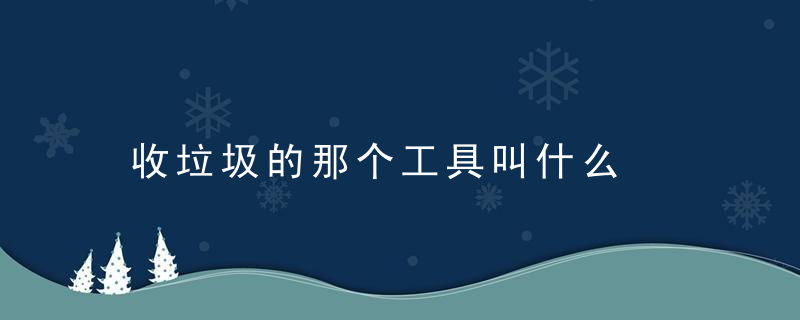鲁迅,那个爱得肉麻的老男人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是铮铮烈骨,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永远一副怒发冲冠之态面对世人
鲜为人知的
是他面对爱情喊出一声“我可以爱!”
是他面对爱人轻语一句“我的乖姑”
窗外师生情
1923年秋天,鲁迅应好友许寿裳之邀,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课。虽然身材高大的许广平经常坐在第一排听课,不过当时鲁迅对这位其貌不扬的女学生并没有留下太多印象。
可许广平却对这位老师印象深刻。“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来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的竖立著,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
即使有同学评价鲁迅为“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但许广平依旧十分赏识鲁迅上课的幽默风趣和渊博学识。她不仅每次上课都坐第一排,有时更是大胆率真提问。许广平对鲁迅崇拜又爱恋的朦胧情愫,就在这课堂上缓缓滋生而来。
1925年3月,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这就是当时著名的“驱杨运动”。许广平是这场学潮中的骨干,为解除内心的迷茫,她主动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在信中,她直言不讳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钦慕之心:“鲁迅先生: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希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坐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
许广平是鲁迅众学生中最有才气和勇气的,这一封高调的“自白书”,让鲁迅和许广平开始了频繁的通信。
爱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不知不觉,突然到来,
何不顺其自然,两生欢喜。
▲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我可以爱
从相识到相知,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之路走得并不容易。
1906年,鲁迅与朱安成亲。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新思潮的引领者,很难想象鲁迅竟会娶了朱安这样大字不识一个,只知封建三纲五常还裹着小脚的女人。鲁迅曾自嘲道:“不是我娶新娘,而是老太太在娶媳妇。”
1906年春,鲁迅留学之际,老太太骗鲁迅恐不久将离人世,十万火急回家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场预谋的婚礼。世人都有疑惑:性格刚烈的鲁迅何以如此顺从母亲?
▲ 右一:朱安
鲁迅父亲早逝,家庭重任落在母亲身上。鲁迅深知母亲不易,对母亲感念尤为敬重,孝顺至极。对于这段无爱婚姻,鲁迅曾这样评价:“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个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应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婚后三日,他便离家而去,直至四十多岁遇到许广平,才遇到真正的爱情。
面对许广平大胆的表白,鲁迅惊慌了,重新燃起年少时对爱情的期待与向往。但理智的他,终知道自己是给不了许广平名分,更不能耽误她的青春。
他多次拒绝,多次阐述自己不配她的理由,由此问出:“为什么还要爱呢?”
“先生,你会真的不懂得爱情吗?你真要为这旧世界牺牲掉全部的生命吗?”
“不,是我不敢,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生怕辱没了你。”
“可是神未必这样想。”
即便流言蜚语缠身,即便鲁迅胆怯害怕,许广平依旧将自己的感情大胆表达:“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 “风子”就是她的心上人——鲁迅。
最终,面对爱情,鲁迅还是战败了。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1925年10月,鲁迅放下了所有包袱,告诉许广平,也是告诉自己──“我可以爱”。
你应该是一场梦,
我应该是一阵风。
相遇不如相爱,相思不如相守。
铮铮汉子的铁血柔情
1926年,鲁迅携许广平南下。鲁迅去厦门大学任职,许广平回广州,当时两人约好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先解决经济自立的问题。结果不到半年,鲁迅就辞掉厦门大学教职应中山大学之聘来到广州。
1927年10月,鲁迅结束广州的教职,与许广平一起回上海定居。
▲ 1927年9月鲁迅与许广平、蒋径三于广州合影。
鲁迅和许广平分隔两地期间,正是热恋期,书信不断。当时鲁迅在厦门教书,信誓旦旦告诉许广平,“听讲的学生中有女生五人,我决定目不斜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直到离开厦门。”许广平看到信后,倍觉爱人幼稚,心底却又甜蜜无比。
鲁迅几乎每天都去邮政代办所等信,还一步步丈量得出八十步的距离,八十步很短,思念却长。写信完毕,为了及时传达自己的心意,他还经常半夜翻越栅栏将信投入的邮筒中,许广平命令他不许半夜投信,怕有危险。
许广平亲手织了一件背心,寄给鲁迅。他立即穿在身上,拍了一张照片,回信里说:“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鲁迅给许广平取了各式小名“乖姑”、“小刺猬”、“小莲蓬”,一如热恋中的男孩,说不尽的甜言蜜语,藏不尽的爱意。
“其实并未大谈,我现在只望乖姑要乖,保养自己,我也当平心和气,度过预定的时光,不使小刺猬忧虑。”
而平日里严肃且令人敬畏三分的鲁迅,在许广平信里,却被称之为“小白象”。
鲁迅后来将两人的信件整理出版,取名为《两地书》。“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生活琐事居多,但相爱之情,溢于言表。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两个人相濡以沫,患难情深。
鲁迅在《两地书》的序言中,向世人展示自己爱情:“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污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好像突然有了软肋,在思念中煎熬;
又好像突然有了铠甲,在流言中勇敢。
此中甘苦两心知
离开广州的念头,大约是从1927年4月开始的。那时候,因为营救学生失败,鲁迅打算辞掉中山大学的教职,最终决定同许广平一起定居上海。
同居,于那个年代,算是惊世骇俗。鲁迅顾虑甚多,颇勇敢的许广平再一次给鲁迅吃下一颗定心丸,她说,“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需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始终准备着独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同居的日子里,照顾鲁迅的衣食起居,无微不至。鲁迅常常深夜写作,冬季茶易变凉。为了让鲁迅喝到热茶,她一针一线缝制了一个让茶保温的茶壶帽。友人回忆,那段时间在许广平的照顾下,鲁迅的头发都不那么乱了,衣服也不再有补丁了。他常对人感叹说:“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许广平还帮鲁迅整理、校对稿子,查阅资料、书籍,编排、保管鲁迅的文稿。让鲁迅全身心投入写作之中。许广平回忆,“从广州到上海以后,虽然彼此朝夕相见,然而他整个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比较二十年前的著作生涯虽只占三分之一,而其成就,则以短短的十年而超过了20年。”
1929年,许广平临产,手术难产,鲁迅没有丝毫犹豫告诉医生救大人。庆幸转危为安,母子平安。许广平出院后回到家中,发现鲁迅把家中的家具全部清洗干净,平日里,鲁迅是从不做这些家庭琐事的。
1934年冬天,鲁迅买到心爱的《芥子园画谱》,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以此纪念两人相守的十年: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临终前曾紧握着许广平的手,给予最后的嘱咐她:“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对于许广平来说,必是不思量,自难忘。
许广平一面抚养海婴成长,一面收集、整理、出版了鲁迅遗著,继续完成鲁迅未竟事业。解放后,许广平把鲁迅著作的出版权上交给国家出版总署,还将鲁迅的全部书籍、手稿及其他遗物捐赠国家有关部门。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相守间,我与你风雨同舟。
别离后,我为你坚守善后。
人世荒凉,唯有你的爱,让我仍温存于这个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