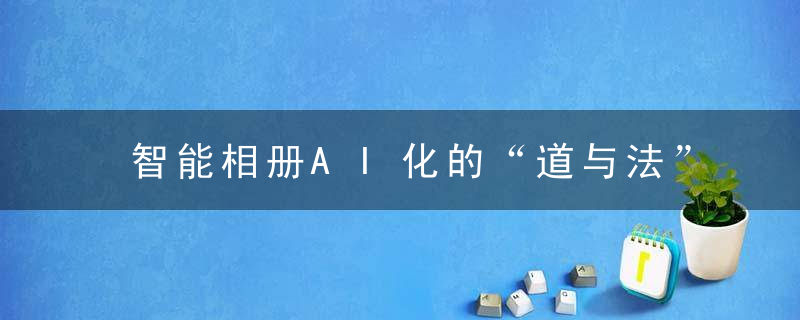跌进码头黑工地的16岁丨人间

《我的诗篇》剧照
他说,他初中没读完就踏进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技术,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比起他见过的那些煤炭黑洞里的活死人、砖厂踩在发烫砖炉上的搬运工来说——自己要幸运得多。
1
2003年的6月,15岁的我正上初三下半学期,家里的一船货在江上沉了船,还搭上了一个学徒的性命。学徒的祖家和客商都来追债,状子雪片似的往县里投,警察终天不离门。
人言是把刀,奶奶是个很要脸面的人,最后把全家最值钱的家当——陪嫁的两只金耳环吞了肚。棺材抬出来后,这件事才算压下来。
第二年,父母躲债去了山西表舅家。从这以后,我就像一颗无根的野草,整日打架斗殴、夜不归宿。在镇上游戏厅里,因为一个短裙姑娘一句挑唆,我把校长的儿子打破了脑袋,看着地上那一滩的血,吓得猛往家跑,把埋在墙子里的钱扒了一半,独自一人悄悄地离开了家乡,逃票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火车行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上午快到广州时,列车员扫雷似的开始查票。他白白净净的瘦脸上横着一对浊眼,好像别人都欠了他钱一样。走过我身前的茶几时,猛不防地一弯腰,三两下就把躲在座位下的我拖了出来,用晴空霹雳般的声音问:“有没有票?”
“我……我买……”我心里又臊又急,憋了老半天也找不到理由。
“叭!”我脑袋晕晕的还没有反应过来,就挨了一耳刮子。
“罚款,60元!”
我被他这么一吓唬,赶忙想到鞋子里鞋垫下还有最后的150元,但那可是我的救命钱,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动”。那列车员不耐烦了:“快点,别跟我耍花招,把钱拿出来!”
我还是僵持着。不一会儿,又过来了一个高大肥硕的列车员,那个白净列车员大概觉得自己有了强大的后盾,先对我轻轻一问:“你到底交不交罚款?”随后声音猛然陡增,严厉地一喝:“你娘,乡下人真他妈又酸又贱!”
我被这句话突地一激,犹如一根鱼刺狠狠地扎在心间。顷刻间,喉咙若有若无有股甜腥味,我瞪着两只圆铃铛样的眼睛,心里有话想说,却说不出口,一把拉住列车员,麻利地把鞋子抽下,翻开鞋垫下的积蓄,把那一张100元面额的钞票甩得刮刮响。
2
出了广州火车站,我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搞得眼花缭乱,心生胆怯,不知道该往何处走。
出站没多久,突然下起豆大的雨点,打在水泥地面上,留下一个个小黑点。降雨虽短暂,雨点打在脸上却辣辣的痛,整个广场上是蒸笼般的燥热,我一手提着布搭袋,一手不停地擦着汗水。
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揾不到工的感受远比一天两天吃不上饭还要恐怖。几天下来,我跑遍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工业区,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叩开一道道紧闭的大门,又一次次满脸失望地离去。晚上就睡在火车站广场上,饿了就嗑馒头,渴了就找水龙头“咕咚咕咚”喝上几口。
口袋里的钱在无奈而漫长的流浪中日益减少,我鼓足勇气去劳动力市场撞撞运气。
一大早,两个招工的就候在劳动市场,正缩着脖子抽烟,看到我一副学生模样,还提着个布搭袋,就知道是从山里农村来的,便过来搭话,问我籍贯。
我心里惶恐,又担惊害怕,可转念一想:身上已无分文,就剩小命一条,怕什么呢? 于是我便搭腔说自己是湖南宁远的。
一个满脸麻子有点矮的中年人说道:“小兄弟,好重的口音啊,我也是宁远的,叫我大东就行,真是他乡见老乡啊!”
我一听口音,的确是宁远的。他问我:“你怎么一个人来广州了,是来找工作吗?”
我想这世道人心叵测,凡事还是留个心眼好,扯谎说:“我有两个哥们在这边工厂打工,在他们那里吃住了十多天,不好意思再住下去,就来这边找活做。”
“喔,那你就到我那里去做一段时间再说吧,我在那里包了一个码头,正缺搬运工人。”他说,“你要是在我那里做得好,一个月也能挣一千多块钱,比其他地方强多了,不过,这搬运工作很辛苦喔,是件卖体力的活儿。”
我心想,反正我在这个城市是孤身一人,当搬运工怕什么!心里顿时充满了信心,决计跟老乡去码头试一下。
于是,我便跟着大东坐着一辆脏兮兮的三轮车,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到了一个到处堆满建筑垃圾的工棚。此时已是中午,万里无云,赤日炎炎。
跟着大东上了江边的码头,码头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两层钢架房,再前面是一排砖砌的平房,房顶是整体的水泥板,对面是工棚和些许捞沙船,工棚后面是一座黄泥土山,山不高,脚下放有装满黄土的手推板车,小山被挖了一大块。
大东走进平板房里,我也跟了进去,屋里又闷热又干燥。房间很小,墙壁上挂着几本计工册,窗户边一张玻璃桌子、几把烂藤椅,地上有两个热水壶、几个搪瓷口杯。我的希望有些动摇,心里涌起些说不出的惆怅与失落,但还是坚定地对自己说:“先做段时间,看看情形再做打算吧。”
正念叨着,就见屋外有个20多岁的姑娘提着一壶水走了进来,容貌还算和善,瘦长的脸,嘴巴上嘟哝着一颗大黑痣。姑娘对大东说:“这么早就回来了,找了几个人?”大东指了一下我,她看见我忙招呼说:“小兄弟,饿了吧?赶快去吃饭吧!”
我确实快饿慌了,跟了那姑娘到工棚的饭桌上去吃饭。夹着那些从锅子里端出来的青菜和豆芽,我捧着碗狼吞虎咽。姑娘倒了杯水给我,“慢点吃,慢点吃,别噎着”,又在间隙里向我打听情况:“小兄弟,刚从学校逃学出来的吧?”我点了点头。
“一个人出门在外,怪单薄的,我们也算是半个老乡,在这里安心做事,放心,我们不会亏你的。”
大东给我安排了床铺,一个屋子里拥挤地躺着9个人,拿着门板往水泥地上一铺就是床。吃完晚饭,我一个人孤独地在河堤上漫步,晚风吹来难得的凉爽惬意。
天空群星如蚁,银河依稀倒悬,远远的霓虹灯依然不舍昼夜地荡漾。我禁不住想念起老家的日出日落——要是在老家的山冈该多好,晚上竹林如海浪般此起彼伏,吹来的是凉风,打开房门是潺潺流水,到处是饱满芬芳的苞谷茎秆。
面前的这条江很大很宽阔,此时江面已然退潮,堤岸边露出沙泥和石头,光滑的石子被星星映照得闪闪发亮。
3
第二天早上,我嗑完馒头就上工了,拿着四齿子的铁锹挖黄土。一同做事的还有20几个工人,他们也只来了一个多月时间——工龄长、做事情熟练的,都被安放到船上装货卸货去了。
天气毒热,大伙都是打着赤膊,皮肤被紫外线晒得黑黝黝的,像刚挖出矿的煤。在农村我虽然没少劳动,可想不到城里的阳光竟然如此炙热,每过几天,皮肤上就开始泛起了热泡,慢慢的,又被晒得粗黄,如同缺水的茄子。
每天装完船,人就累得像狗一样,幸好体力还支撑得住。最折磨人的还是晚上,10个人横七竖八地拥挤在平板房里,汗乎乎的,闷得要命,怎么都睡不着。垃圾里的蚊子成群飞舞,咬人一口,立刻会起一个大红疱。工友们翻来覆去,还是拿着草席到河堤上睡觉。
在这里,工资是两个月发一次,装运的黄土是为水泥厂的老板装的,水泥厂要用黄土掺杂制作水泥板的胚子。那会儿,正好到了比我早来一个多月的伙计该发工资的时候,可是包工头大东却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搪塞,就是不肯发工资。还说什么水泥厂的订单很多,客户合同上的数量还没有满,所以没有付款,等几天再发。
大概半个月之后,因为下了几场大雨,无法上船,大家只得在码头上休息。晚上闲来没事,大伙儿在一起免不了谈论女人。整个工棚除了大东请来煮饭的那个姑娘外,全部是清一色的男人。大伙就讲,船老板请“小姐”到船上干那勾当,又扯到大东也在外面玩,跟他在一起还有个姓王的珠海工头——“就因为他们在外面吃喝嫖赌,连我们的工资都没有发”,说到这里,大伙难免黯然伤神起来,但又都没有办法。
听着大家们聊女人,我忽然想起,来码头前几天,我和几个年轻女孩一起去应聘一个歌舞厅的前台,老板开门见山就问:“你们会做什么?按摩、推拿会不会?”
“都不会。”我和几个女孩异口同声地回答。
老板很得意地笑笑:“那你们说说,至少能做什么?”
那几个女孩面不改色地说:“老板,人家会睡觉嘛!”
结果,老板一拍大腿,立马就带走了那几个女孩,留下我傻愣愣站在那里发了半天呆。
4
一天中午,地上被烤得像烧烫的烙铁一般,水泥厂老板运来一船100吨的水泥,要我们马上卸下来,运送到施工单位。
如果不去搬,就没有工资,大伙只能上了工。人还未开始搬水泥,汗衫就已经开始滴水了,眼睛也被咸咸的汗水腌得红肿,没一会儿就疼痛难忍。船上的老板不住地催促,说如果在江水退潮之前不搬完水泥,就要扣半个月工资。
卸完水泥,我的两个肩膀表皮被擦得稀烂,汗水和水泥灰粘在上面,针扎般难受,只能从煮饭的姑娘那里弄了点膏药敷上,晚上趴着睡在河堤上。
工资一直没发下来,大家心焦如焚地等了两天后,老板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三天中午,珠海工头说老板急需500吨黄泥土,装完黄土就发工资。按照我们当时的装运能力,装500吨黄土至少要10天时间,大伙中便有人闹了,怎么说都不肯上工,珠海工头气坏了,拖住一个名叫阿虎的打工仔,动手打了他。阿虎还了手,珠海工头依仗自己是本地人,拿着手机气急败坏地吼叫,一下子就过来了10几个黄毛的青年人,他们像一群许久没有尝过血腥的禽兽,把阿虎和他过来帮忙的老乡张阳打得头破血流,还把他们按着跪在地上叩头认罪。
此情此景,道义不平。我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出压抑许久的情感,走上去跟珠海工头论理。
珠海工头看着我,凶狠地说:“怎么,小崽,想做侠客啊?闹事的工钱一分没有,把你送去治安队!识时务为俊侯,不然,就是这个下场,呵!”
我理直气壮地还想同他讲理,大东一把把我拉回来:“阿侯,忍一忍啊。”
我一下子把所有愤怒集中到他身上:“你为什么骗我们,我们累死累活地做,工资不但不发,反而这么狠地打人,我们是人啊!”
“你去讲吧,工资没发又不是我不发,你们自个闹事,怪谁?”大东立刻板起脸孔,老乡的热情完全消失了。听到这话,我像被当头打了一记闷棍,所有的希望如同阳光下的泡沫一样瞬间即逝。
许久,大东走到我身边:“阿侯,我们也算是同乡,我怎么会骗你,俗话说得好,‘恶龙斗不过地头蛇’,你怎么能和当地人斗呢!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
随着又说:“虽然你喝的墨水比我多,但你年龄还小,没经过事。要闹的话,等把工钱发了再闹,到时也不会吃亏。兄弟,出门在外,要见机行事。常言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些事是道理说不清楚的,今天这些话,都是我作为老乡苦口婆心对你说的掏心窝子的话。在这里好好干,我不会亏你的工钱。”
我觉得他说这话,好像真的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也便罢了。
此番闹事的结果,无非是闹事人被打了一顿,两个月工资分文没有。阿虎和张阳还被拉到治安队“审理”了一番,最后也被从码头上撵走了。
闹事后的当晚,老板迫于压力,终于给我们发了工资,干满两个月的给500块钱。我还没够两个月,一分钱也没有。
当天晚上,我看到珠海工头请大东进了豪华酒店,大东回来时红光满面,春风得意,嘴里哼着港台小曲。一进门,看到我伫立在那里,便一把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200块钱说:“小弟,老乡我不会骗你,这两百块钱我给你买饮料喝吧!”
不知什么缘故,我问心无愧地接受了,大东扭扭脖子,还回眸一笑了一下,便拍拍屁股走了。
那时候,我又觉得他不是骗我的,是真的对我好。
我拿着这200块钱,心里盘算着:“等发了工资就逃回去。”另外有几个工友也和我想的一样,于是我和他们便一起偷偷商量起这个事来。
5
可是纸包不住火,没想到我们的计划,却从我自己的嘴里漏了出去。
主意定下后,我便和工友们暗暗忍着做事,哪怕船三更半夜来,也要装运。快要到发工资的日子,我便把想法告诉了大东。
没想到听我说完,大东却嘿嘿地笑了:“逃走?你不是想找死?你知道这老板是很凶的,人称‘下手黑’。抓到你不打你个半死?要走,应该光明正大地走。”
“如果明着走,合同未到期,不是工钱没有了?”我说。
“既然要走,要工钱干什么?要不你就把合同做满,这样工钱可以拿到,人也可明着走。”
没想到大东说得这么决绝,我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一晚上,我躺在河堤上,想起家人、老师和同学。我知道,搬运工队伍里许多人都和我一样,想跑回家。工棚里有个年龄比我还小的,因为天热,皮肤磨烂后感染了,腋下还长了一个脓包,也无法及时治疗,现在已经又腐又臭了。
● ● ●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我和那几个计划逃走的工友忽然被抓进了治安队——因为运黄土的老板船上发生了殴杀事件,有人被砍伤。据说是因为两个船老板为争一个“小姐”,最后发生了流血事件。
我和工友们被一个个审问有无参与打斗事件,大家一一否认;然后又被问有无暂住证,大伙说是珠海工头替我们一起办的。没有审出他们想要的结果,于是我们被关押起来,我找治安人员辩理:“我们没有罪,你们凭什么关押我们?”
其中有个领导模样的就斥责我:“小子哎,实话告诉你吧,是你们大老板叫我们把你们抓起来的,你们无故怠工,影响生产,而且没有暂住证!”
这时候,我心里才透彻彻地明白了,一定大东把大伙要逃走的事向老板告了密,现在和珠海工头耍阴招把大伙困住的。
是我,害了大家。
一连几天,大伙每天只能啃几个馒头,体力下降得很快。我们跟治安队抓的一大群盲流人员挤在一起,因为没有亲人或老乡赎他们出去,这群人已经在这里关了几个月了。因为有人把大小便拉在了里面,挤满了几十个人的屋子骚气熏天,
一天傍晚,大东来了,工友们一见到他,个个恨不得食其肉、啃其骨。刚要开口骂,他却说:“叫你们不要经常到外面睡觉,偏要睡,这不是闹事了吗?”
我悲愤地大吼:“是你和上面老板陷害我们!”
大东扭头对我说:“你别他妈不识好歹!我也有难处,珠海工头对大老板说我带了一帮烂仔来做工,个个不安稳!而且我自己也几个月没领到工钱了!你当初走投无路时,要不是我带你到这儿,饿死都没人知道!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也出门在外,哪能昧着天良榨你们的血汗钱?”
说着,他还真的掉下几滴眼泪来,看着他那副模样,我也心软了。
“昨天我好不容易向王老板支了一点工钱,今天到这儿赎你们,各位兄弟,实在让你们受累了,对不住了。”大东说道,带着满脸愧疚的表情。
我们这才终于治安队出来,大东请大伙到小馆子吃了一餐,并表情严肃地对我一行8人说:“听说这儿砍死了一个‘小姐’,治安抓得紧。我跟王老板说了好多好话,才弄到一点儿工钱。现在每个人发200块钱,今晚就逃吧,不然后果更麻烦……反正我也要逃回去的。”
说完,他又讲了一堆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后来我才明白,其实此时,他已经找到另外一帮无辜的人上工了。
当晚,我和工友拿着这200元钱,各自买了车票。我决定去深圳。
6
我早就想好了,我要来深圳投奔发小阿鹏,他初中没毕业就来这里打工了,在一个制鞋厂的流水线上工作。我按照手写的地址,下了公交车走了大约一两里小路,到了一片陈旧的快要拆除的居民小区,穿过一个黑暗的甬道,从居民楼小道绕到后面,才到了他的住处——一处废弃的平板瓷砖厂房。
阿鹏说,以前这里是个棉被场,场子倒闭后,当地人把这些单位房租给外来务工者。阿鹏的那间房子很宽敞,洗澡的水龙头和厕所就在平板房后的锅炉房旁边,我终于得以在水龙头下,稀里哗啦地冲了个清爽的澡。
晚上,我和阿鹏聊起自己这段时间出来谋生时的遭遇和不如意,他说,他初中没读完就踏进了社会,一没文凭,二没技术,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比起他见过的那些煤炭黑洞里的活死人、砖厂踩在发烫的砖炉上的搬运工来说——自己要幸运得多。
第二天大清早,阿鹏就带我跑了几家厂,找了他的亲戚和朋友,遗憾的是,他们都无能为力。阿鹏不甘心,对我说:“我们厂很差劲的,生手进厂一月才百把块钱,熟手工才7、8百。你喝过墨水,我本不想让你进来受这个罪,现在没办法,你若不介意,我向主管讲一下,让你进厂先干几天,慢慢再转厂,怎样?”
我赶忙花40块钱买了香烟,和阿鹏一起,带上烟,找了厂里那个膘肥体壮的主管。但那主管却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什么都不要生手。阿鹏气得和他大吵了一架,骂他是冷血动物,没有人性,没想到竟然直接被炒了鱿鱼。
走出工厂,我实在忍不住,抱着阿鹏的肩膀放声大哭起来,对他说:“是我连累了你,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阿鹏轻描淡写地掩饰过去:“这家厂我早就不想待了,咱们另找,你不要过意不去!”
● ● ●
不久,阿鹏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在一个周日上午,我又鼓足勇气去了人才市场,近4个小时里,我很紧张,心里就四个字:放低目标。接二连三地参加了6个招聘文员的公司面试,都要会打字、接听电话、填写表格、发送文件、接待来客等等。我内心忐忑,只怕应聘不上。
在一家电子公司的摊位上,一个清新秀丽的女行政员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傻愣愣地走过去,因为没有准备简历,招聘负责人便让我在一张申请表上填写工作经历。那位美丽的行政姑娘还借给了我一支笔,对着我和蔼地微微一笑。
表格填写完毕后,招聘负责人让我先回去等通知。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次应该没戏了。
在后来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居然接到这家电子公司的面试通知,我心里盘算着,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声情并茂的“求职书”。
第二天上午,我早早地就来到了公司办公楼下,接待我的正是那天招聘会上的陈小姐,我忙不迭地叫“陈姐”,她忍不住咯咯一笑,露出好看的贝齿。她看了我递交的“求职书”,对我写的自己辍学后的打工经历和遭遇大为赞赏。并且告诉我说,他们部门经理看了招聘表后,夸我的字写得好,在这个制造手机接口和背光灯的工厂里,的确需要一个文员抄写文件给总办。
终于,我成为机电车间品检部的一位文员。
走出气派的写字楼,我哽咽着对陈姐说:“陈姐,谢谢你的帮忙,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她笑着对我说:“小兄弟,我理解你的心情。只要你好好做,就对得起我了。走,我带你办饭卡和热水卡去。”
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的日子终于安定了下来,时光在指间的空隙里悄然溜走,转眼间,我已经在这个城市打工10年了,也慢慢学会了倾听这座城市不同的声音。
黎明就消失在地平线下的环卫工,凌晨托着曙光去菜市场蹲点的菜贩,骄阳似火仍站在街角拉二胡的流浪汉,黄昏骑着三轮车在巷口吆喝卖凉皮的大爷,傍晚临近开始吹弹拉唱卖笑迎客的小姐,黑漆漆夜幕掩盖下伺机窃人钱财的窃贼,午夜时分孤零零游荡街头的少女……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春秋故事,或浓或淡,或深或浅,冷暖自知。
而我们都一样。
编辑:许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