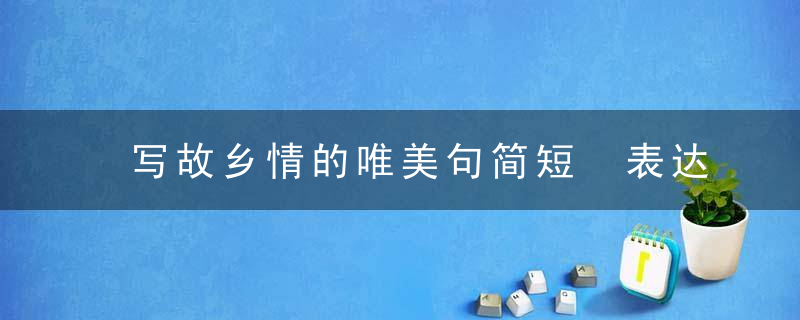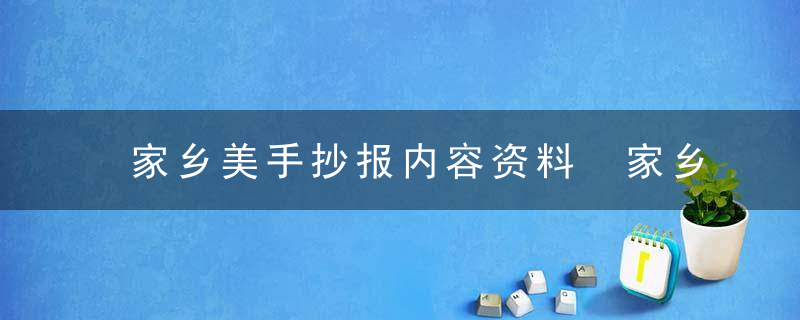死亡不是失去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文/牛皮明明
01
又一个诗人走了,这个时代可以称为诗人的人实在不多了。
12月的寒风凛冽的上海,打开手机:著名诗人余光中病逝,享年89岁。
几年前,在杭州的一次活动中,见过余光中先生一次。
八十多岁的他,身形消瘦,80来斤,发丝如雪,耳垂很大,双眼深邃。午后,阳光打在他身上,显得很干净。举手投足间,十分儒雅,又不失幽默。
那一次活动,本来应该和余光中先生合影的,结果想着合影的人太多,以后还会参加诗歌活动,总还会遇见,结果竟成遗憾,不然还能发个照片给大家看看。
我一个诗人朋友,曾经和余光中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任教,给我讲了一段余光中的趣事。
中山大学就在高雄港边上,学校靠着山与海,操场边是成排的礁石,后山常有猴子,猴子常会调皮地闯进教室。
余光中年轻时喜欢看电影,特别是武侠片,总沉浸在武侠世界侠客的豪气里。
有一次讲课,教室突然闯进来一头猕猴,跳到学生的课桌上撒泼。男生们吓得手足无措,女生们吓得花容失色。
余光中一个箭步上前,右手伸出食指和中指,指着猕猴大吼:大胆泼猴,胆敢撒野,还不快快滚出去!
那只猴子被吓了一跳,踉踉跄跄窜了出去,课堂里大家哄堂大笑,都说余先生比猴子更像猴子。
结果到了第二天,那只猴子又来了,这一次,他乖乖蹲在教室后排,来“听”余光中讲课。
余光中倒是不再赶它,还把它当成特殊的“学生”。
一堂课下来,猴子整整“乖”了一堂课,余光中就去奖励了它一把花生,拍了拍它的脑袋说:孺子可教也。
教室里,学生们又是哄堂大笑。
杭州女诗人舒羽,是我姐姐,2012年的重阳节诗会,又恰逢余光中先生生日。一行几人去了浙江绍兴的王羲之故里,到了鹅池。
大家提议拍照,余光中伸出手,做出一副鹅的样子,逗得大家纷纷效仿。
如今,在大家回忆里,余光中先生还是儒雅又俏皮的样子,而如今前尘如海,古屋不再。
月夜看灯才一梦,雨窗欹枕更何人?就像看见昨天出门,还看见他还在来着,转眼就再无法相见了。
那一代,两岸的饱学文士逐一凋零,现在呢,两岸诗人、文士,喝酒得多,谈诗的少;谈钱的多,用情的少,吹牛的多,读书的少。
02
余光中1928年出生于南京,族人命名“光中”,光耀中华之意。祖籍福建永春,母亲原籍江苏武进,所以自称“江南人”。
余光中的前半生,充满了坎坷,遇到两次战争。第一次是中日战争,炮声一响,母亲就带着九岁的余光中逃亡到南京。
一路上为了躲避日寇追捕,母子两人睡过草地,钻过狗洞。睡过佛寺大殿的香案下,也睡过废弃房子的阁楼上。
母亲安慰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而余先生却说:其实,大难不死即福,又何必说后福呢?
国破山河,颠沛流离,后又辗转重庆,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而苦难不过是一场风掠过沙地,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后余先生又辗转台湾,走过一生,匆匆忙忙一归客,常寄愁心与明月。
在台湾的文人的圈里,余光中是唯一不上牌桌的人。也不抽烟,不喝酒。喜吃苦瓜,出门也是一杯清茶就够了,素简到了极致。
1972年1月21日,余光中在台北厦门街家里,这一年,是他别离大陆整整23年,23年不见故乡一茶一饭,也不见故乡一丝尘埃。
正如古诗所说: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余光中便是这样的征人,不知梦归何处,因为孤独所以写诗,因为思念,所以情绪饱满。
二十分钟写下了《乡愁》,这首诗先刷了语文课本,又在今天刷了朋友圈。
余先生写《乡愁》,只用了二十分钟,却用尽了几十年的情。然后四十多年来,这首诗感动了亿万个炎黄子孙,并且也将继续感动下去。
乡愁,一直是中国人最质朴的情感。
是李白诗中的“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也是杜甫诗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是袁凯诗中的“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故乡还在,人呢,却成了雪中的他乡之客,常把异乡当故乡。
1985年,余先生57岁,到高雄市定居,任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他总是西装、领带,儒雅之风。
而熟悉他的人,却懂余先生的幽默。他的女研究生毕业后,给余先生祝寿。他和学生们打趣:
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女学生们笑得前仰后翻。
内心细腻的人,总是能从苦难中获得勇气和力量。不管人世间多么嘈杂,总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自足,而表现出儒雅和风趣。
03
1992年,余光中64岁,他消瘦的身影在告别了43年后,再次踏上大陆的土地。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余光中离开大陆时,还是那歌楼上听雨的少年,归来时却是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余先生后来演讲中说: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浪子老了,唯山河不变。
2001年4月余先生首次到山东,终于看到黄河。在诗中,他常常写黄河,在梦里也常梦见黄河。
但是在生命的64年里,他却从未见过黄河,也从未到过祖国的北方。
那天,余先生蹲下身去,摸了黄河水,还叫女儿也摸一摸。触手的是水,也是故乡的滋味。
回到车上,同行的人都忙着刮去鞋底粘上的泥浆,但余先生不舍得,把鞋子上泥土带回了台湾。
泥浆干成了黄土,余先生小心地存放在盒子里,摆放在书架上。这就是诗人,别人看起来不重要的,他却看得比命还重。
后来余先生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书房里就传来隐隐的黄河水声,像是听到故乡。
而今天,生活在大陆这头的我们,我们的乡愁更抽象,也更具体。更复杂,也更迷离。
我们的镜头和目光,跟不上故乡消亡的速度。
即使我们的目光保持静止,而眼睛里看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奔走在回到故乡的路上,而远方的故乡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
余光中壮年时,含泪写了遗嘱式的诗篇《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现在,余光中先生走了,他用一生别离之痛,点亮一颗星,也点亮了诗。
当诗人告别没有诗的年代,高贵的灵魂选择在白昼漆黑如墨之中凝望。群蚁奔忙着无望的奔忙,诗行又重新成为最好的悼亡。
对于余先生来说,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只是走出了时间。
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听听那冷雨,他已在故乡!
/ 牛皮明明 /
前报社记者,曾徒步西藏。
现自由作家,写走心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