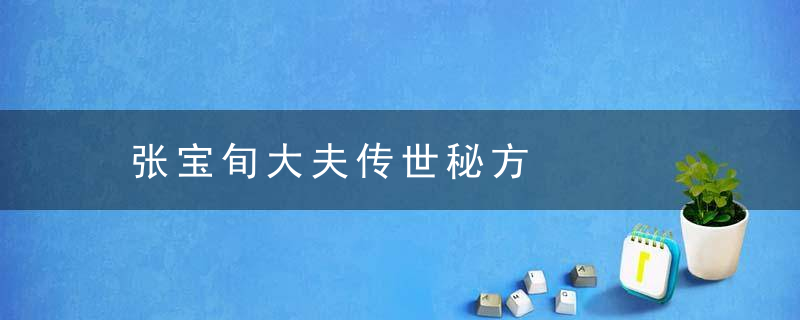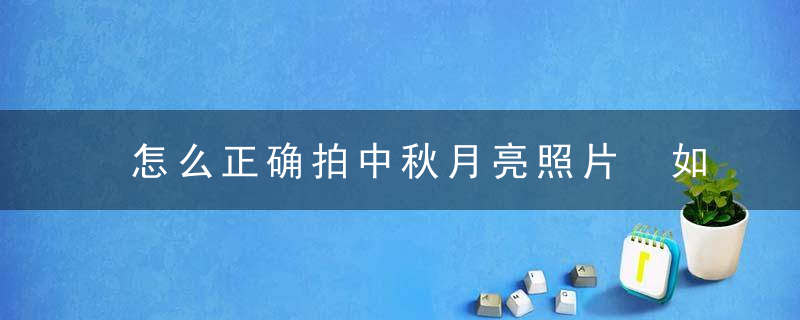说《水浒》系列之《也说宋江》

宋江因为招安路线,被钉上了“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苏州才子金圣叹更是一连给宋江封了“狭人、甘人、驳人、歹人、假人、呆人、俗人、小人、钝人……”的恶谥。黑宋江的人大概都共享一种预设:宋江上梁山以后便打起了“杀人放火受招安”的算盘,为了自己的顶戴官袍而葬送了梁山弟兄。
这样的评价预设了宋江上山是投机,招安是背叛。因为在革命队伍里开小差,所以是革命的叛徒。这种思路基于一般的性恶论假设,而忽略了宋江具体的个体性情,以及内在于其性情中的文化心理结构。
《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一回,宋江知道阎婆惜与张文远通奸后“半信不信,自肚里寻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起做什么?”要注意,这句话不是宋江说的,而是宋江想的。说可以有口无心,但想则体现了人的意识甚至潜意识。在宋江心里,阎婆惜既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就不必当一回事,即便是红杏出墙,也无伤大雅。在这种“血缘性纵贯轴”(林安梧先生语)的格局中,纵向的差序的父母要高于横向的平等的夫妻。宋江是这一格局自觉的维护者。假如阎婆惜是指腹为婚的村姑翠花儿而不是阎婆撮合的妇人,想必也不会有杀惜这一出。
至于招安,这究竟是宋江上山后算盘一划拉的私利,还是宋江平日里出兹在兹的认同,小说里其实也有交代。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武松欲投二龙山,宋江临别说道:“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得做大官。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饮酒话别之后,宋江还特意提醒“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把招安和戒酒看得同等重要,说明宋江对武松的期望并非泛泛而言。应该说,这个时候,宋江还并不具备上梁山的可能性,招安不可能是自许,而只能是对他人的善意期待。虽然有些鄙陋,但这也如同欧阳修劝梅圣俞“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是君本位思想固有之鄙陋,而不是宋江欧阳修个体人格之鄙陋。
不同于鲁智深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不同于林冲的“身世悲浮梗,功名若转蓬”,宋江其实生活在伦理的重重叠加中。小说里的宋江总是接连不断地与家人书来信往:“我不瞒你说,我家近日有书来,说道清风寨知寨小李广花荣知道我杀了阎婆惜……”而《石将军村店寄书》里的一封家书更是宋江的命运转折。拒绝上山之际的说辞“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尚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一日,如何敢违他的教训,负累了他?”父母在,不造反,也自是殷殷可感。至于浔阳楼上的反诗,如果和之前对武松说的“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对勘,便发现更多地是一般性的书愤,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不平则鸣。至于接父上山,除了进一步说明“孝义黑三郎”并非浪得虚名之外,更是造反不可能永远持续的决定性因素。
不知列位看官注意到没有,晁盖做了梁山头领之后,梁山依然未改剪径打劫之勾当。《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一回,戴宗路过梁山泊,被“旱地忽律”朱贵麻倒,险些被拿去开膛破肚。便知晁盖治下的梁山依然是打家劫舍的乌合之众。宋江上山后情形才改变,真正有了点“替天行道”的作风。宋江的招安路线,和宋江对梁山的改造,是一个整体,应该联系起来看。
对于宋江来说,“替天行道”毕竟是梁山聚义之正当性的一个替代品。“替天行道”一词在《水浒》中最早见于九天玄女对宋江的托梦:“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圆满,作为上卿。”在造反并非天然有理的传统社会中,在新型革命伦理付之阙如的传统思想中,宋江只能向天借魂。“九天玄女经”就是“天”的化身。因为对天命只是“借命”而非“造命“、“革命”,所以造反也终归是暂时的造反,“借魂”终要“还魂”。传统思想中并没有不断革命的话语,梁山的造反便要永远遭遇正当性危机。招安投降也好,重心转移也好,传统政治的逻辑就是弑父者终归要为人父。
《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它呈示了新旧交替时代的古今之争,虽然是不完全的古今之争。宋江身上的悖论也是古今之争的悖论。然而我们没有必要害怕悖论,也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评价终结悖论。悖论不可终结,古今之争仍在路上。我们毋宁“保持两者之间的张力”(列奥·施特劳斯语),以俟文明在有意的紧张中仇必和解,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