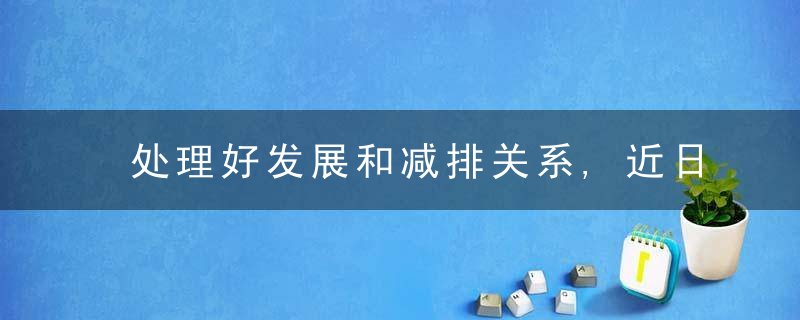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达到这种关系

一位企业家,事业有成,性格霸道。作为地道的霸道总裁,他喜欢上了自己一位下属,可一再被拒绝。
这对成功又自恋的总裁来说,实在是不寻常的经历。
他难以忍受“见而不得”的痛苦,于是找我来做咨询,状态看上去很消沉。
因为被心爱的女孩拒绝而落寞,这可以理解。
但诡异的是,他在给我讲述这件事时,我却忍不住想笑,并且还是带着点开心的那种笑。
作为咨询师,这种时候,我需要区分,这是我的情感,还是我捕捉到了他的情感。
而在接下来的交谈中,同样的喜悦又出现了几次,由此我断定,这是他的感受。
于是,我告诉他:你遭遇了一件伤心事,你表现得也非常落寞,可你给我讲这件事时,我多次感觉到了喜悦……
话音未落,他就开心地笑了,在接下来的咨询中,他又多次笑了出来。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被心爱的女孩拒绝,他反而会开心呢?
我们就此进行了讨论,最终的结论是:作为性格强势的成功人士,他长期生活在“全世界我最大”的错觉中。
当这个女孩坚定地一再拒绝他时,他才意识到,他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之外也有别人存在。
当真切体验到有别人存在后,他的自恋虽然受到打击,但同时也发现,自己没那么孤独了。
并且,他真切感觉到,女下属虽然坚决拒绝了他,但对他是尊重而友善的。
因为这个故事,我想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并不想活在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中,那样太孤独了。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善意的“你”,当确信“你”存在后,我就可以放下防御,把“我”交给“你”。
同时,“我”惧怕的是,在“我”之外,还有一个敌意的“它”。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向“它”低头,而如果被“它”逼迫而低头,那就会产生巨大的羞耻。
熟悉我文字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我使用的是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中的话。
这段话还可以这样表达:
自体一直都在寻找客体,“我”一直都在寻找“你”。
这里的“我”或者“你”,是种抽象的概念。
所谓“我”,就是一个人的内在世界,
所谓“你”,可以理解为整个外部世界。
而这个外部世界,还可能是敌意的“它”。
一个人把外部世界感知为“你”,还是“它”,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马丁·布伯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这本《我与你》,足见此书在哲学史中的地位。
我们来谈谈书的内容。
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字是“我”,而“我”是不能单独存在的,必然呈现出了关系——“我与你”或“我与它”。
当说“我与你”时,“我”与“你”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亲近无间的,中间没有中介物,相当于“当面对证”。
“我”带着自己的全部存在与“你”的全部存在相遇,这里的“你”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棵树,一本书,是当下的生动和真实。
而当人们说“它”、“他”或者“她”时,对方并不是直接呈现在“我”的面前,中间有人为的转述和加工,有想法和经验的阻隔。
而“我”也不是全身心的投入,其中有很多隐瞒和保留,带有明显的企图。
马丁·布伯称之为“想法的灌木丛”。
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讲过一个故事。
他上课时,有位学生每次必定坐在第一排,对他的授课频频点头微笑,于是,他对这个学生产生了好感,常会在课上课下和对方探讨一些问题。
就在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造之才”时,对方提出了一个请求,说自己正在申请美国常青藤名校,希望钱教授可以帮忙写推荐信。
钱教授欣然答应,可是就在他把推荐信交给那个学生后,这个学生就此消失了,再也没来找过他。
钱教授顿时明白了这个学生与他建立链接的目的,他将这种人称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这个故事中,那个学生与钱教授建立的链接,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功利性。
目的达到后,链接也就断了,这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它”的链接。
在这种链接中,“我”与“它”是二元对立的。
“我”独立于世界之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实现目的的工具。而至于对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应,“我”毫不在乎。
人不可能毫无功利性,就拿高考来说,大家都希望能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因此,学生与教材的链接就是“我与它”的链接。
无怪乎考试一结束,很多人就会把教材撕得粉碎,或烧成灰烬。
不过,我们与真正热爱的事物之间,却是“我与你”的链接。
正如马丁·布伯说,“我与它”所反映的是一个经验世界,而“我与你”却塑造了一个关系世界,“我”与“你”比肩而立,心神交汇,休戚与共。
有快递员给我送了份快递,他走之后,我发现尽管事情刚发生,但他的样子已非常模糊。
因为,我和他没有真正相遇。
对我而言,见面那一刻,他只是一位快递员,满足了我当时的一种需要,我没有拿出我的全部存在去碰撞他,他对我而言自然就很模糊。
马丁·布伯说,一切真实的生活,都是“我与你”的相遇。
这时,“我”与“你”之间没有概念体系,没有先验知识,也没有幻觉想象,此间,连记忆本身也转换了模样,从碎片变身整体。
有天早上,我在书房里整理书稿,我的猫阿白爬到我腿上。
由于它的毛会粘到裤子上,以往我会把它抱回到地上,可那天我突发奇想:就让它进行下去吧。
于是它安然地趴在我腿上,我默默地看着它,突然感觉有什么奇妙的东西,在我和它之间发生了。
过去,尽管阿白的样子很清晰,但我与它仍然是一种需要与被需要的链接,我喜欢它的可爱,它也一直扮演着可爱。
而那一刻,我忽然触碰到了阿白的存在——全然存在。
过去大多数时候,我与阿白都处在“我与它”的链接中,我的头脑不间断地对阿白做出评价。
比如它爬在我的腿上时,我会评价“裤子粘上猫毛不好”,并因此把阿白抱下去。
强行介入这种链接,同时也切断了彼此之间的能量流动。
人的头脑总会专注于评价,在这样的链接中,人其实是活在概念中,并没有活在生活里。
在我看来,为人处世的关键不是头脑有多聪明,而是要让封冻的能量流动起来,它自然也会指引你走向归途。
心理学家邬斯宾斯基在临终前说:“靠头脑什么也发现不了”。
而马丁·布伯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建立“我与你”的关系,必须远离“想法的灌木丛”。
鲁米有一首诗,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与你”的相遇:
有一片田野,
它位于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
我在那里等你。
当灵魂躺卧在那片青草地上时,
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
观念、言语,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语句,都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在马丁·布伯看来,每个人都生活在双重世界中:“它世界”和“你世界”。
这两个世界是能彼此切换的,然而“它世界”的牛人,到了“你世界”有可能风光不再。
拿破仑在“它世界”中是一代枭雄,当他遭遇滑铁卢才感叹道:“我就是一座钟,静默存在,却不懂自己。”
而梭罗在“它世界”中默默无闻,但后来在“你世界”中,却被后人顶礼膜拜。
为了自身的生存,我们要心怀“野心”,犹如章鱼般通过竞争将自我伸展,延长自己的触脚,去建立各种各样的“我与它”的链接。
但饱满的链接也必然充满攻击性,甚至有利用、诱骗、私心与嫉妒。
缺乏“野心”,不伸展自我,人活得憋屈;
而任由“野心”膨胀,一味扩张自我,有失为人之道。
究竟该何去何从呢?
我的南极之旅,让我找到了答案。
当时我们几个人乘坐橡皮艇,在壮观的冰山下巡游。看着飞鸟翱翔的身影,我的心突然有所触动,然后,我安静了下来,而周围的世界一下子鲜活起来。
就在那几个小时,我完全敞开了自己,感受到了灵魂的富饶。
几位同行的团友说:“武老师,你怎么突然间显得神采焕发?”看来,人一旦进入“我与你”的关系,就会产生明显的变化。
生命是这样的过程:人,本是“它世界”中一个孤独的能量体,需要在“你世界”中借助镜子,照亮自己,当能量彻底被照亮后,就会开悟。
而“野心”与“良心”的关系也是这样。“野心”在“我与它”的层面,“良心”在“我与你”的维度。
没有“良心”的“野心”是丑恶的、被诅咒的,但如果“野心”能够在“我与你”的维度上被“良心”照亮,它就能受到祝福。
我很喜欢鲁米的这几句:
你生而有翼
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行
形如虫蚁?
何为“虫蚁般的匍匐”?就是处在“我与它”的链接中。
马丁·布伯说,在“它世界”中,人是以“自有生命体”出现的,而在“你世界”中,人则变成为“人格体”。
“自有生命体”就是凡俗大众,而“人格体”则是超凡脱俗的人。
不过,没有人是纯粹的人格体,也没有人是绝对的自有生命体,每个人都会有突出的倾向。
如同马丁·布伯认为的,世上没有两种人类,然而人类却有两极。
在一些关键时刻,例如恋爱婚姻、养育孩子时,我们需要抛弃目的性和功利性,以“人格体”去建立“我与你”的关系。
王小波和李银河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
王小波第一次看到李银河,两人聊了很久,突然王小波问她:你有男友吗?
李银河回答:没有。
“那你看我怎么样?”王小波就这样俘获了李银河的心。
我读过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觉得那是最好的文字,比他最引以为傲的小说还要好,因为那文字中的心性太真实了。
看重对方的心性而非其他,只有在“我与你”的相遇中才能发生。
真爱,必然发生在“我”与“你”的自发反应中,反之则会成为悲剧。
一位女士回忆她十几年的婚姻时说,在这场婚姻中,她每天都拼尽全力,不是讨好丈夫,就是反省自己,但爱却依然渐行渐远。
太使劲的婚姻不是相遇,而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
我向你展示,我是好的;
而你必须给出证明,让我确信,我是好的;
否则,我就觉得自己是坏的,转而觉得你也是坏的。
而在爱的相遇中,应该是:
我觉得我是好的,所以无需证明;
我对你好,但不期待你如何回应我,也不控制你。
如同纪伯伦说的:“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对爱而言,爱已经足够。”
在马丁·布伯看来,只要存在预判和期待,构建的就是“我与它”的关系。
但如果有个崇高目标做前提呢?比如我想构建一个真善美的世界,于是强行把你拉进这个世界里?
这一样是“我与它”的关系。
即使嘴上说着“我爱你”,但只要心里有预判和期待,就是“我与它”的关系。
有人在恋爱中,很容易因为一件小事就上升到“你爱不爱我”的高度,但根本上是,是希望能控制对方。
我们总是用“爱”作为掩饰,进行控制、利用甚至剥削。
作为中国的心理工作者,我探索的主要是中国式关系,这其中也有很多迷雾。
比如,我们在生活中,总是在为关系中的“强加”去正名。就拿“听话教育”来说,父母有时候甚至没有理由,只因为“我是你父母,所以你要听我的”。
理想的家庭结构,可以归结为一句:夫妻关系是定海神针。
在一个家庭中,夫妻关系应该排在第一位,亲子关系则排在第二位。
夫妻关系深厚,他们经常能达到“我与你”的维度,相反,有问题的家庭总是处在“我与它”的关系中。
在一些父母普遍的意识中,亲子关系才是第一位的,而他们所谓的亲子关系,也不过是高高在上的控制和管教。
同时这些家庭中,夫妻感情普遍不好。
一个婴儿的出生,本是来拯救家庭的——成年人已经被切断了感觉,只剩下僵化的头脑。
此刻我们有了向孩子学习的机会,然而,我们总将婴儿弄得和自己一样,匍匐前行。
最好的关系是,我没有失掉我的主体性,你也没有失掉你的主体性,彼此都能绽放,与其他能量建立链接,并将这份链接上升为“我与你”的相遇。
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中讲了一个故事:
一个3岁男孩在一间黑屋子里大叫:“阿姨,和我说话!我害怕,这里太黑了。”
“可你又看不到我。”阿姨回应说。
“没关系,有人说话就带来了光。”
对于幼童来说,没有回应之地就是绝境。有了回应,就有了光,进入了“我与你”的关系。
一个人的生命是否丰盛,关键在于,他与其他存在是否具有活生生的关系,是否生活在生活中,而不是僵化的概念中。
最后,我想以马丁·布伯在《无声的问题》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
你必须自己开始。
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
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
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
那么对你来说,
生存依然是没有意义的。
✦ 以上节选自武志红为马丁·布伯的《我与你》所作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