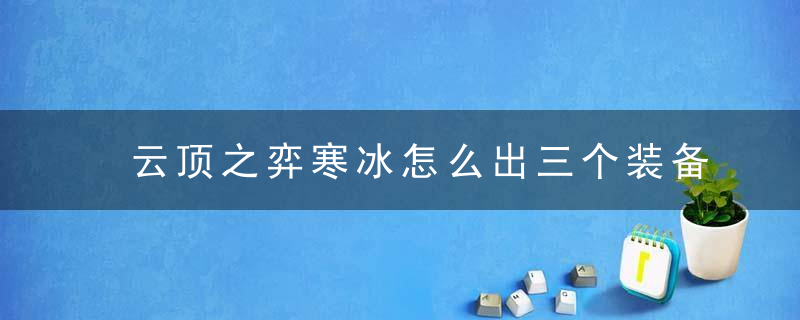姜文你能不能给我道个歉,能不能

我爱聊天,但非常害怕和姜文聊。我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
一位导演对我说过这样一番话,让我出了一身冷汗。
他说:“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也得是酒。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最后还是葡萄。有一些导演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知道电影应该是酒,但没有酿造的过程,上来就是一口酒,结束时还是一口酒。更可怕的是,这酒既不是葡萄酿造的,也不是粮食酿造的,是化学原料勾兑出来的。小刚,你应该把葡萄酿成酒,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我听到过很多对我电影的批评,大多是围绕着“商业”两个字进行的。这位导演的批评却超越了这些表面现象,说出了问题的实质。
这位导演名叫姜文。
姜文是巴顿,
我是《加里森敢死队》里藏心眼儿的小队长
我给姜文拍过《北京人在纽约》,他给我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很少来往,平均一年打不了一个电话。我爱聊天,但非常害怕和姜文聊。我觉得跟他说话特别费劲——累,跟不上他,愣往上跟又很做作,掌握不了话语权,谈话显得非常被动。
电影对于姜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也是非常令他伤神的一件事。他认为应该由最爱电影的人来从事这一职业。这种爱应该非常单纯,不顾一切,不能掺杂别的东西。对照这一标准,我总有不好意思的感觉,像做了对不起电影的事,把拍电影庸俗化了,因为我基本上还处于把电影当饭吃,为了保住饭碗必须急中生智、克敌制胜的档次。这可能和我的处境有关,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押在上面,奋不顾身只为登顶。我首先考虑的是,如果输了,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就像一场战争,不同的人都投身其中,大家也都很玩命,但巴顿那号人从心里热爱战争,想法非常单纯,目的只有一个——在战争中成为最牛的胜利者;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虽然打起仗来也很敬业,却个个心怀鬼胎,留着后路。巴顿如果战败了,叫战犯,属于统战对象,能进政协;加里森敢死队那哥儿几个如果战败了,就被拉出去枪毙了。巴顿是不怕付出惨重代价的,重在过瘾;加里森敢死队的哥儿几个却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为了保住小命,必须确保胜利,还不能牺牲。两类战争的参与者,境界完全不同。坐在一起聊战争,巴顿会把话语权牢牢把握在手,小哥儿几个只有听的份儿。
拍《甲方乙方》时,巴顿的首选是姜文,请不来才换成英达。抬起杠来,英达、姜文的聪明智慧非常够用。因为这一点,他们在谈话中永远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姜文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你不能这样吧?”每次我听到这样的句子,直接反应就是,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了。事后,我又问自己,我哪样了?久而久之,我萌生了一个愿望,迫切地想听到他在把所有的聪明智慧都用上时,说一声“我错了”。
姜文和马晓晴干起来了
1991年,拍《北京人在纽约》时,我们住在纽约长岛奥伊斯特贝小镇。一天晚上,晚饭前,几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播放了一段仅有几十秒钟的电影预告,是影片《桂河大桥》。马晓晴和姜文为影片的主演是不是大卫·尼文发生了争执。
马晓晴坚持认为《桂河大桥》的主演是大卫·尼文,姜文则断然予以否认。他告诉马晓晴:“《桂河大桥》里没有大卫·尼文,但这部影片的导演叫大卫·里恩,得过奥斯卡奖。这部电影我看过七遍。”
姜文 马晓晴
他们向剧组的录音师李学雷求证。学雷是电影学院毕业的,看过无数电影。学雷说,好像是大卫·尼文主演的。姜文鼻子都气歪了,一口咬定,谁说是都没用,绝对没有大卫·尼文的事儿。为此,姜文和马晓晴打赌,赢家有权对输了的人做任何事情。
剧组的人也分成两派:以郑晓龙为首的一大帮人坚信姜文不会有误,站在姜文一边;我和艾未未站在马晓晴一边。我当时还没看过《桂河大桥》,但我希望姜文输。我答应开车拉马晓晴去租录像带,条件只有一个:马晓晴若是赢了,让姜文当着大家的面说“我错了”。
我们开了一个小时的车,来到曼哈顿。艾未未把我和马晓晴放在他的地下室里,自己去租带子。十几分钟后,他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就像要告诉马晓晴她得了癌症一样。未未说:“晓晴,咱们输了。我没有在录像带的封面上找到该死的大卫·尼文。”
《桂河大桥》电影海报
当时,马晓晴几乎丧失了回奥伊斯特贝的勇气,叛逃的心都有了。那天晚上,我们陪着她在一家名叫CBJB的摇滚乐酒吧耗到午夜才回去。
回到剧组后,我们发现大家都没睡,几乎全体等在客厅里。印象中,我是溜着边回到卧室里去的。
艾未未陪着马晓晴走到人群中。
马晓晴对姜文说:“你赢了。”
姜文说:“那就按说好的,我可以对你做任何事情。”
大家都很兴奋,不知道姜文要如何处置马晓晴。
姜文让马晓晴坐在椅子上,对她说:“我就是想告诉你,心里没数的事,别跟人打赌,尤其是别跟我在电影上抬杠。”
事后,马晓晴说:“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
我对她说:“我也是太想看姜文认一回输,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以后一定得知道自己稳赢再和他抬杠。”
从那以后,我也落下一个毛病:凡是姜老师说的话就深信不疑,凡是姜老师做的事就拍手叫好。我觉得他就不可能错,他太聪明了。
淤出来的聪明
终于有一天,我找到了姜文的破绽。每次我见到他,都想对他说,但见了面,又把溜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我觉得这话说出来可能会得罪他,还是别给自己找不痛快了。分手后,我又后悔,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他。毕竟姜老师也诚实地指出过我的软肋,在我找不着北时,给我敲过一次警钟。
几年前,一个和姜文很熟的朋友对我说,他曾听到姜文对电影《活着》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据说姜文是这么认为的:“活着”是一个动词,电影里被当成名词使用了。福贵为了“活着”,内心应该是非常主动的。他听到家乡土改枪毙地主的消息,预见到了自己的下场。为了“活着”,他应该主动放弃,利用一场赌博把土地和家业输得精光,从此沦为贫农。结果,他如愿以偿,躲过一劫,活了下来。
把“活着”当成动词,由此把握福贵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葛优演的福贵断然不会想到的,看得出来姜老师是何等聪明,对“活着”的理解又是何等充满智慧。每到这时,我都在想,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导演得省多大的心。但细一琢磨,我又觉得不大对劲。如果福贵真的这么有智慧,这么主动,我们还能被他的苦难刺痛吗?
我这个人自身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最好”;姜老师则不然,他自身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能够节制他的才华”。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敌人就是淤出来的聪明。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姜老师有失误,但不能掩盖他对中国电影的贡献。过去、现在、将来,他无疑都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