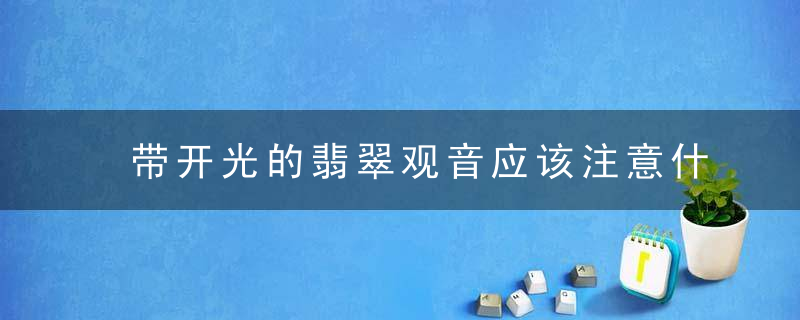学问

“功名富贵”与“治国平天下”两种价值定向在士大夫身上一般是可以并行不悖地暂时共存的。当然,两者并不随时随地都能相互包容而不致发生撞击。“治国平天下”是基于儒家内核文化而产生的道德规范,它要求社会成员理智地压抑个人的欲望和本能,服从社会群体谐调发展的需要,以“仁学”(即所谓人与人之间普遍的、实际上有等级结构的爱,或可谓之古代人道主义)的理性去消融任何个性要求,将国家(及其君主)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长期历史沉淀,它已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原始心象”),深深地扎根于整个文化教育之中。即使如此,在心理的深层,仍潜伏着欲望、本能等无意识暗流,可以被压抑,却不能被消灭,时时还会从海底上升到水面,偶露峥嵘。
宋明理学,就是针对商品经济发展刺激起来的“人欲”,企图靠“内省”压抑“情欲”的再一次尝试。传统社会“功名心”所包容的这种内在的矛盾,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下,可以因人因时而异,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寻求简单的“统一”将会使人失望。同是江南士大夫,甚至同属复社成员,也并不是都如此疯狂地热衷于利禄,追逐、角斗于官场,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特别是到了亡国之祸临头,大难从天而降,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士大夫身上依稀看到了儒家人格原型。
晚明畸形的“人才过剩”,既造成了角逐科举官场的病态,也撞击出一种与之离心的力量。
例如归庄,自叹“读书二十年,做秀才十年,不曾一望见场屋”,历经折磨,幻想破灭了,“今心已呆,气已尽,却不复知有所谓愁闷也”,总算从“功名富贵”中解脱出来。由于时势使他与科举、官场相隔离,他的心理较少受到污染,还保持着一种鲜明的儒家色彩。他自许“壮夫薄雕虫,《草玄》亦可已。我有救时策,他日献天子”,已经不汲汲于当时的功名追求。他在送其好友黄淳耀、周上莲会试时,殷切赠言“今日所急者经济,经济尤要者兵农”,望他们“守其素履,以报国家”“必以匡国家、安社稷为心”,即反映了中国古代士大夫高尚的人格与传统的理想,同时也多少暴露其不谙世情、富于幻想的弱点。
归庄像
因此,这些人一旦涉足官场,目击了种种黑幕惨状,就迅速由狂热跌入悲观失望。由此,我们既看到有玩世不恭、视政治为私利工具的吴昌时,也看到有视富贵如浮云、官爵似敝屣的“清流”。
最典型的便是常熟瞿式耜。崇祯初他由进士授官户科给事中,与当时许多人一样充满了憧憬,连连疏奏,提出了许多治国主张。终因烈宗忌刻,又牵涉进了老师钱谦益的纠纷中,丢官卸职,锒铛入狱,差一点送了命。由此,他几乎怀疑自己由科场到官场是一场噩梦:“忆从早岁误桑蓬,灭没翻身浊浪中。”“浮生空自叹飘蓬,眨眼都抛役梦中。”这种心灰意懒、视功名似浮云的心情,一直到明亡后他南下桂林、勉力支撑永历危局时,依然非常强烈。他在给常熟家人的信中,一再表示“吾生平不爱官爵,且受过几许风波患难”,“宦兴索然”,不“贪位慕禄”,只求做一个“太平百姓”,对晚明政局绝望至极,愤叹道:“其实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
瞿式耜
更有一人后来看破红尘、入禅削发的,这就是晚明“四公子”之一的桐城方以智。他原是一个“好言当世之务,言之辄慷慨不能自止”的贵公子,在桐城组织“泽社”,在金陵结交天下名士,又与陈贞慧等起草《留都防乱公揭》名震当世,很是顾盼自得。想不到崇祯十三年赴会试,恰逢其父为时相所忌,以失律罪下狱。方以智在长歌当哭之后,淡然于功名富贵,唯求归隐,以著书自娱。明亡后,又遭到阮大铖的残酷报复,流离于南方各地,归隐于深山之中。永历政权曾多次召授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十次上疏辞退,坚不出仕。瞿、方两人在广西相遇,成为莫逆之交。桂林为清兵攻破后,瞿壮烈殉国,方则万念俱灰,削发为僧。但方以智并没有虚度余生,在隐、禅期间写成了《东西均》等皇皇巨著,著作等身。
方以智著 《通雅》
方比瞿更超脱,始终不愿任职,名谓“著书自娱”,实则在经历九死一生之后,熔儒、道、禅于一炉,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对天、地、人深邃的哲学思考中,颇有发明。他关于“合二而一,一分为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更是旷古未有的独创,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这是又一种“移情”,较之前一种,功利主义的遗习已脱落得了无痕迹,似乎很有点否定“超我”的意味,显示出“自我”意识的崛起。因为它已属于一种置具体的世情国事、经世致用于度外的个人独创的精神活动。这也许要归功于道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唯有道家还具有一点“自我”意识,肯定人的个性价值。
可惜的是,我们在后面将要看到,明亡之后,固然有不少士大夫摆脱了晚明功名官场的污浊气,不时显露出纯洁高尚的灵魂,但更多的却是瞿式耜这样的“殉情”型“移情”以及另一种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新功利型“移情”。这再一次证实了儒家的内核文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有顽强的生命力。
顾炎武
对明朝前景的绝望,对顾炎武为代表的士大夫遗民打击没有比之更惨痛的了。然而正是这一不堪回首的事实,迫使他们做出了另一种历史抉择。这种抉择是在对有明一代士大夫的价值观做了认真清理之后产生的。对此,顾炎武在给门生潘耒的信中说得最完整: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
对时代的强烈失望诱发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历史感。面对有明三百年惨痛的“亡国”“亡天下”的事实,他们鄙薄一切对现实功名利禄的追求,只想苦苦思索“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热望由此寻找到“有以救之”的“柳暗花明”境界。此岂顾炎武独然。梨洲先生命其书名曰“明夷待访”,不也正是这种意思?因此,当顾炎武读到《明夷待访录》,抑制不住喜得知音的兴奋,即致书于黄宗羲:
“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
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全面的一次“历史反思”。无论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还是颜习斋、李恕谷、陆世仪、张履祥,虽然主要都还是从检讨有明一代的治国得失入手,思路追迹所及却是自秦始皇以来的历史。可以说,这是在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之光照进中国之前,在传统思想的范围内对中国传统史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面反省。传统社会的各种制度,如郡县制度、胥吏制度、井田制度、钱粮制度、科举学校制度、选举用人制度等等,都在他们面前受到历史思辨的审判。
黄宗羲
他们看不到在此之外还存在另一个世界,没有任何新的社会模式或思想资源可以借鉴比较,只能在古籍中向更早的历史资源求助。表面像是要回到“三代”去,但他们并不是倒退,历史的思辨使他们天才地猜测到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许多致命弊病,设想过各种校救的可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
这种反思,在具体的对策上,只是重复存在过的,企图化腐朽为神奇,并不足取,但在批判的思路上,却天才地揭示出许多病灶区域,对后人不无启发。二百年之后,近代革命家孙中山、章太炎等从这里找到了所谓“启蒙”思想,也证明了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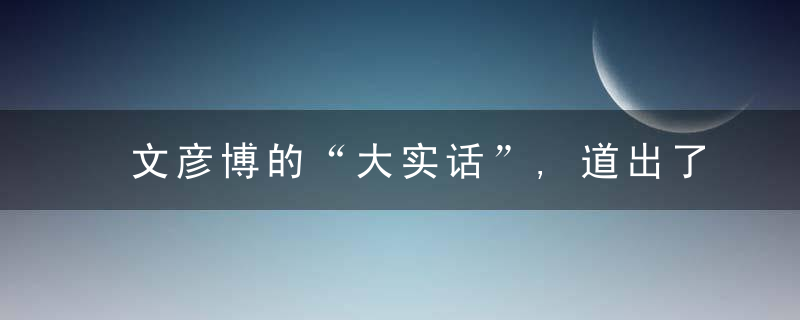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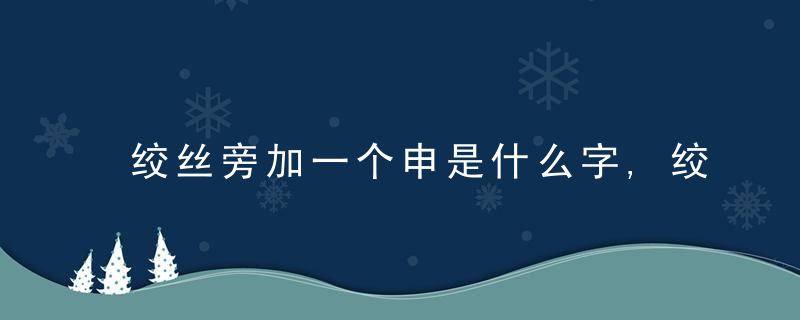




,沙和尚.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