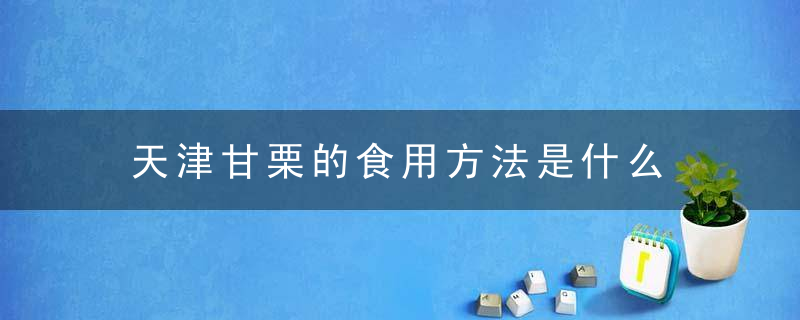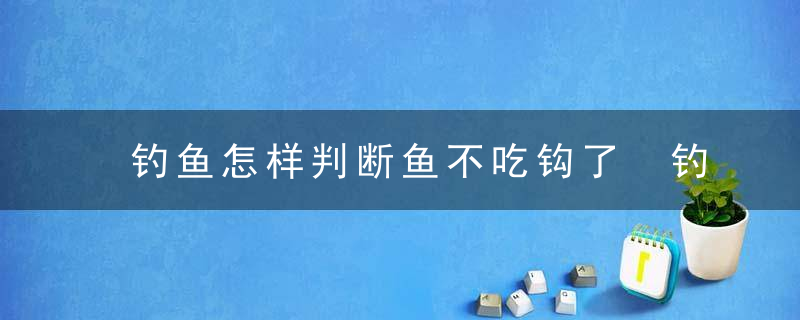打工诗人|为最底层作证

作者:苑苏文
实习生:余梦箫
陈年喜与父亲
炸裂诗人
陈年喜这两年过得并不好。
金矿老板前年拖欠的工资仍没着落,他却在去年初查出了严重的颈椎病,这病和他16年的职业——爆破工脱不了干系。
日复一日,他攥着剧烈振动的钻头在大山深处打眼,然后装填炸药,轰炸后被粉尘包围。他技能娴熟,能用别人一半的炸药爆出更好的石料,但付出的代价是轻微失聪、尘肺、风湿,和要命的颈椎病。
钻头把他的颈椎骨节震错了位,如果不治疗,他将面临瘫痪的命运。去年4月,陈年喜颈椎的第四、五、六节处在医院被植入了金属。手术花费共计10万元,其中2万来自于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团队的捐赠。
46岁的陈年喜是陕南商洛地区丹凤县人,写诗已经有20年,即使在平常偶尔吆喝两声的秦腔中,他也会把歌词稍作变动,使其变得有讽刺意味。“我最后吼起了秦腔《铡美案》/一生气/我把陈世美的小老婆也铡了”。
而让他坚持创作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心灵的需要,我需要把我内心的声音发出来,第二个我有自己的野心。”
陈年喜时常在远离城市的矿山中一呆就是几个月,夜深人静时,他会在破旧宿舍唯一的昏黄灯泡下阅读文学杂志。“矿上的生活特别特别寂寞”他如是强调,而在那些劳累而无法入睡的时候,唯一的慰藉便是读《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或是《百年孤独》、《资本论》。文学让他的灵魂远离矿山。
孤独酿就了陈年喜旺盛的创作欲,但写诗却无法支撑起他的生活。从高中开始,陈年喜曾经在杂志、报纸上发表过200多首诗歌,稿费最多的一次是50元钱,那是一首20多行的诗歌,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
这与爆破工职业的收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私营煤矿,爆破工的收入和爆破出的材料挂钩,好的时候,他一个月能挣到8000元。
去年8月,陈年喜的父亲瘫痪多年后去世,而她的母亲两年前被查出食道癌晚期。家里还有一个正在县城租房读高中的儿子,每年学费和生活费是2万元。
“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他在诗中写道,“它坚硬铉黑/有风镐的锐角/石头碰一碰就会流血”。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陈年喜被迫出走,在遥远的山脉中寻找矿石。“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他在诗歌《炸裂志》中写道:“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 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 轰地炸裂一地”。
一场矿难后,老井怀念逝去的同事
走进他们精神世界的深海
12月底,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放映开始前,陈年喜身穿矿工服,头戴安全帽和头灯,朗读了一首《意思》。
“……前年/小宋查出了矽肺病/走的那天/他老婆用他最后一月工资/请来了镇上最好的乐队/让英雄武二哥美美送了一程/去年/老李让顶石拿走了一条腿/成都的麻将摊上/从此多了一只/独立的鹤子……”
小宋和老李是矿工们命运的缩影,陈年喜把他们从几千米深的漆黑矿洞带到了聚光灯下。在他面前,观众坐满了这座巨大放映厅里600多个座位,他背后,是17米高、24米宽的巨幅无缝银幕。
打工者诗人的生活被用高清摄像机记录了下来,再用巨幕放大在观众眼前。“人的精神世界,是摄像机无法探入的地方,但它是一片深海,是诗歌生长的地方。因为有诗歌这一媒介,我们可能比许多影片更加能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我的诗篇》导演之一秦晓宇说。
这部纪录片中的另外五名打工诗人,都在时代的巨变下书写心灵。
吉克阿优
2007年起,中专退学的彝族小伙吉克阿优离开大凉山,前往山东、北京、东莞等地打工,他曾做过三年鸭绒填充工,写下了“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我的诗篇》团队跟拍了他的一次春节返乡,镜头下,逐渐遗失的古老习俗让吉克阿优感到忧心。
篝火旁的两段对话揭示了大凉山深处彝族文化的传承危机。家族一位长老感叹“死前要把头巾缠好”,因为“等我们老死了,也就没人会缠头巾了”,而年轻的晚辈谈论着外面的世界,在“留下来干活”和“出去打工”之间纠结,就像年轻时的吉克阿优。
工厂里的邬霞
在深圳,制衣厂女工邬霞穿着臃肿的工作服,仔细熨烫着一件吊带裙。“我要先把吊带熨平/挂在你肩上才不会勒疼你/然后从腰身开始熨起/多么可爱的腰身/可以安放一只白净的手/林荫道上/轻抚一种安静的爱情”,打工之余,她写下300多首诗歌,其中这一首《吊带裙》最为人们熟知。
邬霞出生于1984年,是个爱美的姑娘,出租房的衣柜里装满了她收藏的廉价吊带裙,其中最便宜的一件是在夜市花20元钱买下。她14岁就跟随父母到深圳打工,全家8口挤在一套50平米的出租房中,前几年,她的父亲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症,肝囊肿、肾囊肿和轻度老年痴呆,一次治疗要花十多万元。而邬霞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一个月能收入三四千元。
但这一切,到了邬霞的诗中,却变成了“我不会诉说我的苦难/就让它们烂在泥土里/培植爱的花朵”。
广州街头的乌鸟鸟
80后打工者乌鸟鸟曾凭着《狂想》系列诗获得第二届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三等奖,但这并不能帮助他在广东的人才市场找到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面对老板们的“你做这个事情(写诗)究竟能不能赚到钱?”,“马云那样才是成功”的质疑和嘲笑,他只好悻悻离去。
在商业社会中,以诗谋生几无可能。曾是叉车工的乌鸟鸟走出人才市场,扛着行李,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被迷失笼罩。
纪录片中的老井
矿工老井的生活与黑暗和压抑捆绑在一起。他今年47岁,18岁开始写诗,21岁时成了一名矿工。在安徽一个地下800米的国有煤矿里,木讷的老井一天工作结束后,脸会被染得漆黑。人们评价他用诗歌与地心对话,在一首叫《黑典》的诗中,他写道“地心深处狭长、弯曲/幽闭的庙宇指向乌黑的宗教”。
老井书写煤矿中的死亡。在《逼视》中,他写道:“这块脸盆大小的矸石/推开钢梁和钢丝防护网的支撑,窜下顶板/砸中了一颗忙碌的头颅/他猝然倒地,变成一根秋后原野上静卧的秸秆”,而引发矿难的元凶瓦斯,在他的诗中被描述成“煤层、石峰间的老魂灵——/无色。无味。无情。”(《瓦斯》)
对于最后一位出场的90后打工诗人许立志,纪录片只拍摄到了他的葬礼。秦晓宇清楚地记得,2014年4月,当他在博客中发现许立志的诗歌《流水线上的兵马俑》后,立刻决定把这首诗作为他正在编撰的《工人诗典》的收尾。但当八月份,《我的诗篇》纪录片邀请许立志参与拍摄时,他却有一个“小小的回绝”,表示自己不再写诗了。
2014年9月30日,国庆节前一天,许立志从他工作的富士康工厂边的高楼上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全球最大制造工厂,拥有工人十几万名,在那段时间中,曾有十几人连续跳楼自杀。
许立志曾写过诗句:“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做螺丝”,他在流水线上工作了3年,长期日夜颠倒的高强度工作,让他得了偏头痛,“并腰弓”和失眠。
纪录片截图
许立志死后,《我的诗篇》摄制组拍摄了他悲伤的亲人和葬礼。在黄昏下的海面上,他的哥哥许鸿志亲手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在深蓝的海水下,粉白色的骨灰逐渐溶散,画面中出现了他最后写的诗:“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这恰好对应了在诗歌《远航》中,许立志写道:“我想在凌晨五点的流水线上睡去/我想合上双眼,不再熬夜和加班/此行的终点是大海,我是一条船”。
为底层立言
去年6月,《我的诗篇》获得了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但这部制作精良的纪录片却只能通过众酬电影的方式与观众见面。
在公益组织壹基金的帮助下,截至目前,这部纪录片已经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进行了放映,而支持其放映的“众酬发起人”也已达到了数百名。12月19日的放映,就是2015壹基金公益映像节城市展映的一部分。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诗歌是一个奢侈的东西,但对于这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打工者来说,诗歌给他们安慰和寄托,是必需品。”放映会上,壹基金副秘书长沈旻说道。
纪录片的宣传海报
而纪录片只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和秦晓宇所策划的推动工人诗歌文化建设的“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
2014年3月,吴晓波偶然看到秦晓宇的一篇描写工人诗歌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对这一群体的存在感到非常意外,之后,他给秦晓宇写信:“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随后他们一起策划了《工人诗典》,收录了50余位工人的诗歌。还有图书出版、纪录片、微纪录片、诗歌朗诵、研讨会、诗歌奖等一系列活动。
2015年2月2日晚, 19位打工诗人聚集在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朗诵了自己的作品,他们从事炼钢、采煤、铁路、建筑、爆破、制衣等形形色色的工作。也是在同一天,通过众酬的方式,许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在京首发。
秦晓宇认为,工人诗歌的价值在于“为底层立言”。“哪怕他们仅仅书写了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广大的命运的同路人来立言,在为底层的生存作证。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古老的见证功能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
在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下,这些打工诗人也在寻求命运的改变。吉克阿优仍在充绒,同时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邬霞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但她的大女儿即将入学,她要面对异地教育的昂贵学费;求职失败的乌鸟鸟打算做一个杀猪匠;十多年前,老井有望被调回地面,但他选择继续做矿工,这会为他从事煤矿诗歌创作带来灵感。
颈椎尚未彻底恢复,陈年喜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当爆破工。
能出现在12月19日纪录片在北京的放映,是因为一个“二合一”的机会。陈年喜如今身负与四川电视台的娱乐节目《诗歌之王》的一纸合约,给歌手写歌词,需要一个月上台两次,而距离不久的24日,正是他在北京录制节目的时间,“两个事一起办吧”。
也曾有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个去福建当保安的机会,但因为与节目有冲突而搁浅。在节目中,他被冠名“炸裂诗人”,与歌手罗中旭合作,后者作曲,演唱他的诗歌。不少普通电视观众成了他的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