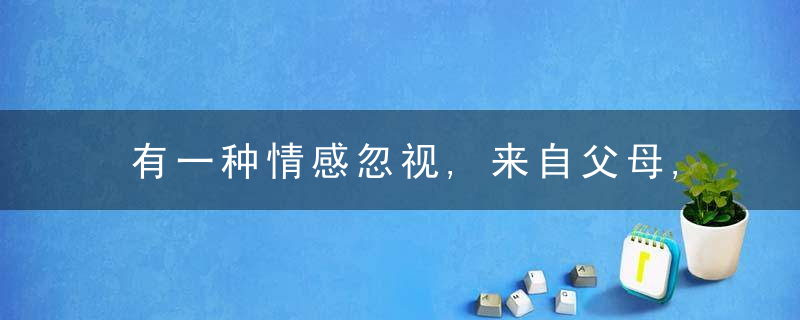传统与个人才能

T.S.艾略特(1888—1965)
美国现代著名诗人,现代诗歌运动的领袖和代表人物。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所著《荒原》扭转了整个世界的诗歌倾向,因而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开山之作。在诗歌理论上他同样有别人不可企及的建树与创见。
【传统与个人才能】全文
一
在英语写作中我们很少提到传统,尽管我们有时倒也从反面用它,抱怨缺乏这种东西。我们无法追踪这种传统或者某个传统;至多我们只是使用它的形容词形式去说明某某的诗是“传统式的”,甚至“过于传统式的”。很有可能,除了用于谴责语外,传统一词便很少出现。但在其他场合,这个词倒也微具褒义。可使受赞许的作品产生某种古物复现似的可喜联想。真的,除非你能将这事与那门可敬的考古学问安然结之一处,传统这词在英人的耳中听来便不舒服。
显然传统一词在我们对当今或已故作家的鉴赏评介当中并不是很常见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不仅具有它自己的创作思想,而且具有它各自的批评思想;另外他们对自己在创作才能上的不足与局限虽能记得,但对他们批评习惯上的这方面问题却每每忘记。看过法语当中刊出的大量批评文字,我们于是懂得了,至少自认为懂得了法国人的批评方法及其习惯;而我们的结论(按我们的自觉意识便向来不强)也无非是法国人的批评精神比我们强,甚至这点反而使我们得意起来,仿佛法国人不如我们来得天真自然。或许他们就是这样;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批评这事实在是和我们的呼吸一样少不得的,再有我们也绝不会因为将我们读某书时的一些观感道了出来,或者因为读其批评文字时对自己的看法作了一点批评便将使自己变得没有价值。在这件事上至少有一点必将得到阐明,这即是每当我们赞美某位诗人时,我们往往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即撇开其他方面不论,而专门强调他与别人的特异之处。在他作品的这些方面我们仿佛觅到了一些具有个性的东西,一些足以代表他本人的特殊品质。于是我们便自鸣得意地在这类地方大做文章,指出这位诗人在哪里哪里与他的前人不同,特别是与他较近的前人不同;我们费尽心力去寻觅这类东西,将其孤立起来,以供人欣赏。殊不知,如其我们在对待一位诗家时不抱这类成见,我们必将不时发现,不仅他作品当中的那些最好地方,亦即他的最有个性的部分,也往往恰是他的已故前贤们赖以成就其不朽声名的得意笔墨。况且这里我指的绝非是,一个人可塑性强时期的少年试笔,而是他鼎盛之年的真正力作。
不过,如其说传统的唯一形式即在盲目追慕步趋前一代人的业绩,而且小心翼翼,唯恐不及,那么这种传统也就显然不值得提倡。我们便亲眼见过不少这类简单潮流很快消失在沙漠之中;而创新总比重复更好。事实上传统一词具有异常宽广的含义。传统无法简单继承,你如要想保存传统就必须付出巨大辛劳,传统首先牵涉到一种历史感,而这种历史感对于一位已经年过二十五岁而仍想继续写诗的人几乎可说是绝对不可缺少;这种历史感还意味着对过去事物的一种了解,即不仅了解过去之已经过去,而且过去之仍然存在;这一观念迫使那写作的人于其濡墨伸纸之际不仅必须将其同代的事物熟烂于胸,而且必须另有一副宽广见识,即仿佛自荷马以降的全部世界文学,乃至包括他自己所属国家的那一部分文学此时此刻全都具有一种同时性的存在,并构成着一种同时性的秩序。正是这种历史的观念,实亦即是一种既是永远的又是当日的,以及永久的与当日的兼而有之的观念,才使得一位作家具有传统意义。同时也正是这个才使得他对他自己的历史地位,对他的当代性等获得某种清醒意识。
任何一位诗人、画家或其他艺术家,单独来看,都不具有多大意义。他的重要性,他的艺术价值,都只能在他与已故诗人与画家的相互关系中方能见出。你无法单独对他估价;你只能将他放置在已故者中,以便进行比较对比。这点我以为乃是美学批评(不仅是历史批评)的一项原则。在这事上,哪些他必须加以遵循,必须求得一致等等都不是单方面的问题;真正的情形是,每当一件艺术品新被创制出来,这件东西便立即与在它之前的全部艺术制作都同时发生关系。那现有的许多制作本身之间存在着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个秩序却要受到这个新的(真正新的)艺术品的修正。原有的秩序在新作到来之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秩序的延续,一经新的成分进入之后,这全部秩序便多少有必要加以小量改变,这样每一艺术品之于全部艺术之间的种种关系、比例与价值等也就再度得到协调;而这个也即是旧与新的融合。谁如果赞同这个秩序理论,赞同欧洲文学以及英语文学形式的这个秩序理论,那么他对古之必然受今改动与今之必然受古指导这一现象便会心平气和,不以为怪。再有诗人如能看到这点,他对自己的巨大困难与严重责任也就不难有所认识。
说来不无奇怪,他还将认识到他无可避免地会要受到过去旧标准的裁判。不过也只是受裁判,而不是被肢解;不是裁判它与以往的作品孰高孰低,孰长孰短;当然更加不是依照已故批评家的义法规章去加以评断。它是这样一种评断,一种比较,即由两个事物彼此互相衡量。对于一部新作来说,仅仅求得与传统符合即是完全未能符合;因为这样就会了无新意,因而也就算不得一件艺术制品。我们倒也并不完全认为新的作品只要能够符合传统便是具有价值;但是能否符合传统则也是它所具备的一项检验标准——当然这标准在应用时必须小心谨慎从事,因为我们对是否符合传统这事有时谁也无法确切把握。在这点上我们最多只能够说:某个作品似乎符合传统,因而也许具有个人特色,或者某个作品似乎具有个人特色,因而也许符合传统;但是我们很难处处那么准确,仿佛某件事物一定是非此即彼。
关于诗人与过去的关系如果表达得更加浅近一些便是:首先,对于过去的一切不可全盘接受,囫囵一团,不加区分;其次,不可只按一二心爱作家去形成自己的写作风格;最后,不可只将某一个人偏爱的时期奉为自己的写作标准。这第一点是行不通的,第二点是人年轻时的不成熟做法,而第三点也只能作为一种可喜甚至有益的补充。一位诗人必须时刻不忘当前主流,但这主流却未必一概出自名家之笔。他必须充分了解这一明显事实,即艺术从无所谓进步,但艺术所用材料则可不尽相同。他必须清楚,那欧洲的思想,他本国的思想——这个思想他终有一天会认识到远比他一己的思想要重要得多——总是要不断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亦即发展在其过程当中却从不对过去事物采取简单抛弃的做法,既不认为荷马与莎士比亚老悖无用,也不认为梅达里恩匠人的石画原始过时。另外这种发展,尽管如何精致,甚至肯定更加复杂,但从艺术的眼光来看却说不上是什么进步。即使从心理学的角度观察也与进步关系不大,至少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说穿了不过是因为利用了某种经济与技术成就而显赫得稍微复杂一些罢了。但是这今与昔的区别则在于,真正有意识的今乃是对于昔的一种知觉,而且那知觉的方式之妙与程序之深都是昔对其自身的知觉所难以比拟的。
有人讲了,“那些已故作家已经和我们相隔过远,因为今天我们懂得的东西早已大大超过他们。”一点不假,他们正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我非常清楚,对于一般显然归在了我的名下的那一部分作诗主张往往有着这样一种反对说法。那说法是,那套主张对于渊博(亦即迂腐)的要求实在达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而这种要求一经拿到任何文学殿堂去检验一下许多诗人的生平,便将立见其妄。甚至只需看到学问过大必将窒息和破坏诗典一点,这事也就不难明白。不过我们虽也一再强调一位诗人总是学问愈大愈好,仅仅是不可大到使他变得无法也无暇感受,但是我们却不赞成将知识学问只局限于单纯实用一途,即只能用以去应付考试、应付客人和应付那更为糟糕的虚假宣传。有些人确实能求到学问,另一些欠机敏的便只好去下苦功,莎士比亚曾经从一部《酱鲁塔克》中学到不少历史,但许多人即使读遍英国博物馆的藏书也未必便胜过他。这里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一位诗人必须尽量培养和获取他对过去的意识,并在自己的全部生涯中去不断发展这种意识。
创作的过程实际上即是一位作家使他的目前种种向着那更有价值的事物不断屈从的过程。一位艺术家的进步表现在一种不绝的自我牺牲之中,一种不绝的个性消亡之中。
这个非个性化的过程及其与传统感之间的关系等都有待于进一步去加以说明。但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一过程,艺术才可以说是有条件向着科学靠拢。因此,为了说明问题,我认为这里不妨为你打个比方,即那效果将不下于把一段铂丝引入到一个盛有氧与二氧化硫的器皿当中。
二
严正批评与明敏鉴赏的对象只应是诗作而非诗人。如果我们所注意的不过是报章评论家的纷乱喧嚣以及一般人的随声附和,那么进入我们耳际的只会是成串的诗人姓名;但是如果我们所追求的并非是蓝皮书上的知识,而是诗的鉴赏,因而要去寻找一首具体的诗时,我们却未必轻易能觅到它。上文我已就一首诗与其他人的那些诗作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意义稍加说明,提出诗这一概念应当视作历来全部诗作的一个活的整体。这样我的非个性化诗论的另一方面便将是诗与诗作者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上面譬喻,这点已经初步讲到,即是一位成熟诗人与一位不成熟诗人在心智方面的差别主要并不在谁的个性更强,谁的趣味更丰富,或者谁比谁更“有话说”,而是要看谁是一副更为精良完善的媒介,因而在它里面一切独特或复杂多样的感受都能够自由如意地形成种种新的化合。
这个譬喻即是说去起催化作用。当上述两种气体与一段铂丝相遇后,便将产生出亚硫酸。这种化合只有在铂出现时才会发生;然而这新形成的酸中却无铂的痕迹,另外铂本身也显然并未受到影响,仍然保持其惰性、中性与无变化的特点。诗人的心灵即是这种铂丝。这副心灵可能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对一个人的经验起着作用;但是一位艺术家愈是高明,他身上所体现的那个善感的人与创作的心灵也就愈加超脱;这副心灵对作为其素材的激情的一番消化与转化也就愈加彻底。
你必将注意到,进入到这种具有转化作用的催化剂中的经验或元素不外两种:情感与感受。一部艺术品对其欣赏者所发生的作用乃是一种特殊的经验,与其他非艺术性的经验在性质上很不相同。这种经验可以由一种情感构成,也可以由多种情感构成;再有借助于某个词语或形象以表现其作者意向的一些感受还可以增添进去,借以造成那最终效果。另外伟大诗篇也完全可以并不直接使用任何情感,而是单凭感受著成。《地狱篇》的第十五章(也即描写布鲁奈托·拉蒂尼的那章)即是一个著例,这里作者只不过将情节本身可能提供的情感作了充分发挥;然而这章诗的效果,虽与其他艺术品同样纯正,却是凭借大量细节方才取得。诗的最后四行完全是一个形象,一个近乎于形象的感受,而它的出现绝非出于一般的发展敷衍,而是“突如其来”,不求而自至。然而细揣作者心理,这一形象也有可能本在诗人心中,只是蓄而未发而已,直到后来一切齐备,这才适时抛出。实际上诗人的一颗心灵正是这样一副容器,其中所储感受、词语与形象乃是何等丰富,然而非待足以形成某一新事物的各种因素全都齐备,便绝不轻言创作。
我们只需从那些最伟大的诗篇当中取出若干典型诗行进行一番比较,便不难看出那里面种种结合的类型曾是何等丰富多样,另外许多半带伦理性的“崇高”标准又是何等迂阔不着边际。因为归根结底,并不是那些情感,那些组成部分的强度与“伟大”,而是那艺术过程,那在熔化发生时所出现的压力等的强度,这才是那最主要的。波罗与弗朗西加的对话一节的确使用了某种明确情感,但是那节诗里的强度则与一般经验所给予人们的那类强度印象绝不相同。再有这章诗也并不比第二十六章,亦即尤利西斯的水行的那章更加强烈,尽管这后者没有凭借任何情感。实际上情感的炼制转化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类型;阿伽门侬的遭弑或奥赛罗的剧痛所造成的艺术效果较之但丁诗中的一些场景显然更为逼似原型。在《阿迦门侬》中,那艺术情感与一名目睹者的情绪几无区别,至于在《奥赛罗》中,那艺术情感简直就是那主角自己的情感。但是艺术与现实的区别往往是绝对的;在艺术的结合上,阿迦门侬的遇弑与尤利西斯的航行几乎会是同样复杂。不拘哪种情形,这里都有着一个诸元素的融合问题。济慈那首颂歌中所包含的许多感受实际上与夜莺并无多大关系,但是不知由于夜莺这个名字动人,还是它的名声响亮,那里的种种情感还是被很好地归到了一起。
上面我极力攻击的那个观点也许即是所谓的灵魂本体统一说一类的玄学理论:而我的意思也无非要说,一位诗家并不存在着什么“个性”须待表达,他所具有的只是一种特殊工具,亦即仅是媒介而非个性,在它里面种种印象经验往往会以不同于一般,甚至意想不到的方式去进行着新的结合。一些印象经验对其本人可能非常重要,但在诗中却无地位,另一方面一些在诗里变得很重要的印象经验,但对某个个人,对他的个性也许只起微弱作用。
为了加强上面业已阐明(还是弄糊涂了?)观点,我将引诗一节作为佐证,这诗故意取得偏僻一些,以便更好引人注意:
我想我该狠狠责备自己,
因为我对于她过于迷恋,
虽然我必采取非常手段
为她报仇雪冤。难道春蚕
也是为了你才不辞辛苦?
为了你竟不惜毁掉自身?
难道许多爵爷宁可爵爷
不当,也要用钱供养美妇,
也要去贪求那片晌之欢?
为何你要故意歪曲正道,
使人一命悬于法官一句
判词?说得好听些吧,为何
不让养马聚众,为她报仇?
在这一节诗中,那积极的情感与消极的情感全都结合到了一起(这点从它的上下文来看极为明显):一方面是美的强烈的吸引,另一方面是丑的同样强烈的诱惑,而丑又不但与美对比,而且破坏着美。这种对比情感的平衡便出现在与这段讲话相协调的那个戏剧场景之中,而仅仅场景本身则与那平衡不够相称。这个我们不妨称之为戏剧提供的一种结构性情感。但是那整个效果,那主导情调的取得则是来自这样一个情况,即一些飘浮感受与那剧中不很明显的情感具有某种天然联系,因而一拍即合,共同构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情感。
因此个人的种种情感,生活当中具体事件引起的那些情感并不能使一位诗人写出出众或精彩的作品。一个人的具体情感可能相当单纯、粗糙、甚至平淡无奇。但是他诗作中的情感则异常复杂,只不过不是一个人日常生活中那些复杂情感的复杂。造成诗作怪诞这种错误的原则之一便是企图寻索新的情感去加以表达;结果新的不曾寻来,只找见了一些乖谬东西。诗人的职责并不在于去发现新的情感,而主要在利用一般情感,将其提炼成诗,借以表达在实际情感中很少存在的种种感受。一些他不曾体验过的情感将与他熟悉的那些一样可以供他使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认为“在平静中追忆起的情感”这一公式实在有失确切。因为诗既非是情感,也非是追忆,也非是按其原义所谓的平静。诗乃是一种凝聚专注,一种得自凝聚专注的崭新事物,它来源于那计数不清的广阔经验,这些对忙于实际事务的人几乎完全不是经验;另外这种专注的发生既很少是自觉行为,也很少是熟虑结果。这些经验并不是靠“追忆”得来,它们在最后的聚合过程当中虽也可能出现所谓“平静”,但也仅是一种附带现象。当然这绝非是问题的全部。在诗的写作上,确有相当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和要熟虑的。事实上那不高明的诗人正是在该有意识时他无意识,而在该无意识时他却意识十足。这两种错误都容易使得他太“个人化”。诗并不在宣泄情感,而恰是要逃避情感;不在表露个性,而在逃避个性,当然这里所说的需要逃避的真正含义也只有那有个性与情感的人才会懂得。
三
显然心灵是个神圣事物,不受外界印象控制。
这篇短论不拟涉入玄学与神秘主义领域,而仅希望得出一些对爱诗的人有所裨益的实际性结论。将人们对诗人的兴趣引向诗篇本身乃是一项值得嘉奖的举动:这将有助于对实际诗作得出更为公正的评价,不管是好诗坏诗。有不少人对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情感颇表赞许,也有一部分人对它的技巧长处很有眼力。但是真正读得出哪里表达了重要情感(这种情感的生命力只在诗的本身,而不在它作者的身世)的人则为数不多。艺术的情感乃是非个人的。这种非个人化的获取只有当诗人将其自身全部交付给他所致力的作品才有可能。另外也只有当他不仅生活在当前,而且生活在过去的当前,只有当他不是知道哪些是陈旧事物,而是知道哪些已经具有新的生命,只有这样他才能懂得如何去做。
高健 译
【品评鉴赏】
艾略特以其长诗《荒原》,而荣登现代派诗歌的宗师宝座。其诗论《传统与个人才能》则以逃避个性与情感,整合传统与创新而显赫。
作为一篇创作的经验之谈,作者尽量避免情绪色彩,以冷静的理智平静地阐述诗歌创作与鉴赏的要肯,这使全文观点明确。因为是诗人,艾略特得以避免生涩、冗长、繁琐的概念堆砌,对每一个旧有的概念,都加以自己独到的理解与诠释。同时逻辑简洁,构成一种明快的思维节奏。也因为是诗人,他不太思辨,而是以对生动的诗歌例证的分析,精到而富有说服力地阐述观点。这使这篇文章,立论扎实骨肉丰满。作为一个诗人,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一改诗歌修辞的习惯。语言平白晓畅,比喻贴切自然,显示出一种朴素而活泼的文风。这在理论文章中是尤为难得的。
正如他对诗歌的理解:“诗不在宣泄感情,而恰是要逃避感情;不在表露个性,而在逃避个性。”他的这篇创作谈,也以情感的节制,对个性的超越,而成为诗论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