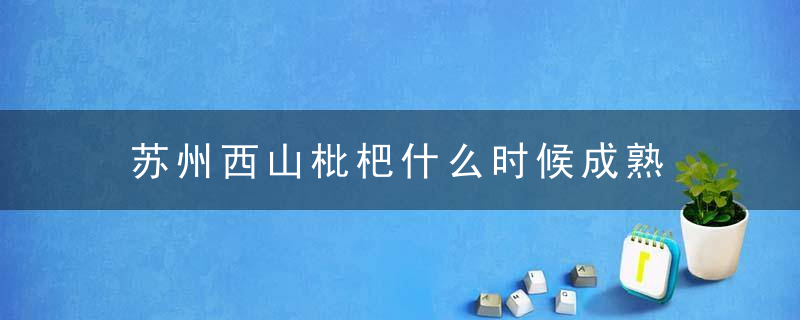夏日萤火虫 林少华

读过拙译《挪威的森林》的人,想必记得书中关于萤火虫的描写。“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呢?情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成的老式水门也出现了。……水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数百只之多的萤火虫。萤火虫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不过,较之过去的数百只,渡边似乎更在意敢死队送给他的一只:“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忽有所悟似的,蓦然张开翅膀,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那微弱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色中彷徨。”
我则相反,较之那一只,更在意过去那数百只。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家里又一次搬家,搬到一座叫小北沟的小山村。小山村只有五户人家,三面环山。北山坡住着三户,东山坡一户,西山坡一户即我家这户。南面三百米开外是铁路、公路,铁路、公路一百米开外是小河,小河再往南一二里开外是连绵的山岭。
东北乡下,家家房前屋后都有一块种菜的园子,我家的大部分在房前,就叫南园子。南园子尽头有条小路——纯粹是羊肠小路——沿西山坡底端呈抛物线形向西拐去,沿路西行大约二里有一座名叫“上家”的铁路小站。花三毛钱上车,半个小时后即是县城。早晚各有一趟客车停靠。小山村和北山后面两个生产队(屯)的乡亲们,早上总有几人沿这条小路去火车站,晚上又从火车站沿这条小路回家。
顺便说一句,沿小路走过我家南园子篱笆之后,再往东走有一道壕沟,下雨时山水咆哮而过,把壕沟冲得又陡又深。于是,北山坡三户中一位名叫张喜的老地主把自家园外一棵大榆树砍倒刨平,横在壕沟上做成独木桥。他跟我爷爷说修桥补路可以增寿。但不出两三年——记得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竟悬梁自尽了。后来乡亲们说这老地主真聪明,赶在“文革”前走了,若不然非被红卫兵打死不可,估计是修桥修来的福分。说实话,那位老地主使得刚在小学语文书上学过《半夜鸡叫》的我产生了困惑:无论如何我都没办法把面容和善砍树架桥的他和语文里的地主周扒皮联系起来。
言归正传。小路绕过的西山坡中间那里约略瘪了下去,状如一个巨大的椭圆形浅盘,里面长满了蒿草,间有几棵榆树。“盘”外隆起的北侧同我家南园子之间长着一棵歪脖子老柞木,浑身疤节,很粗,两个小孩几乎合抱不过来。老柞木斜对着我家门前通道。早上开门,常见几只喜鹊在枝头对着我们喳喳欢叫几声。黄昏时分,就有一群乌鸦从天外飞来落在枝头聒噪一阵子,所谓“枯藤老树昏鸦”,大约就是这番景象了。
不过,西山坡最有兴味的景象还是夏天的萤火虫。不知是不是窝风的关系,那里的萤火虫格外多。始而三五只,继而七八只,很快就数不清有多少只了,成群结队往来盘旋。由于飞的速度慢,形成不了“滑行”的光线,但光点已足够可观了。尤其无月无风的暗夜,即使不能说是“宛如正在燃烧的火星”,也可谓正在跳跃的繁星了——就好像银河的一角忽然降落人间。而且越落越多,越多越亮。最多最亮的时候,可以隐约照见草丛中一簇簇白色的山芹花,照见小路山坡一侧一丛丛淡蓝色的野菊花,照见小路另一侧玉米叶上攀爬的一朵朵牵牛花骨朵。
也有时飞进园子里的黄瓜架,飞到窗前门前,三三两两,飘飘忽忽,闪闪烁烁。黑的夜幕,亮的光点,神秘,幽玄,令人想起教科书图片上那茫茫宇宙中点缀的银星。一次我记起古人借萤火读书的故事,就趁萤火虫暂且伏在那里歇息之机猛地伸出双手,捂住几只装进小玻璃瓶,松松地扣上瓶盖。然后把小瓶放在书页上。只见那几只小家伙贴着瓶壁往上爬,肚皮的萤光正好对着瓶外书页上的字,勉强照亮四五个字。作为故事诚然感人,但实行起来相当吃力,很快作罢。
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大约是2002年最后一次回老屋探望父母的时候。由于农药和西山坡另一侧开石场的关系,数百只萤火虫群早已消失,仅在一个极黑的夜晚好歹在院子樱桃树下瞧见一只,而且光色很弱很淡。回想起来,确如“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色中彷徨”。
两年前的暑假我从相距不远的大弟家再去找那片西山坡的时候,那里已变成采石场的废料堆放场,几大堆青石渣拔地而起——西山坡消失了,被铲平了,掩埋了,那可是有萤火虫的西山坡。记忆中,父亲那天傍晚就是在西山坡下急切切奔回家来,手里举着一封信大声招呼我:“通知书、通知书来了,吉林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几天后我就是沿着西山坡下的那条小路走去小站,上车奔赴省城……
夜光杯2018年07月17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