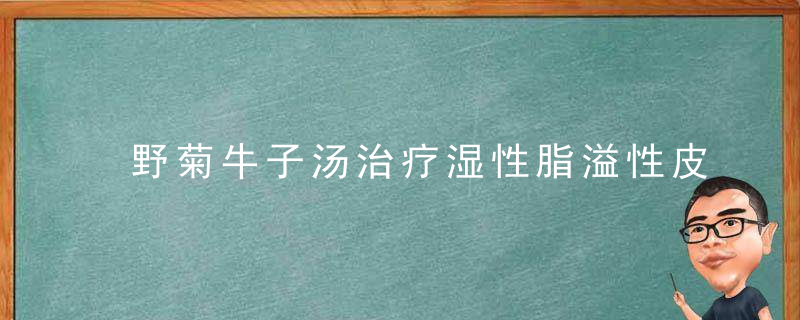月夜听荷 【猫眼看人】

我在月夜听荷,是喝酒后的举动,我趴在了残荷之下,听到了爆炸一样的声响,我听到了巨大的声音,其实只有心的一颗,骤然分裂,向相远的方向散去。我趴在那里,有长长久久的时间,听到了蛙鸣,听到了残荷把风撕裂的丝丝声响,还听到了星星坠落的声音像水滴落入陈年的深井。落的过程有一万年,滴水的声音就像琴音。这多么像你走在大理石阶梯上的声音啊,我就是坐在那里开始想你的。
想你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是日头落下去,无可挽回的那一片斜面与三角吗?
我和你,似乎已经相识了一万年,我们坐在旧年的网蛛前,历数往事,竟是相逢相适相知过的。那一处从月夜深处扑散开来的笛声,或许就是我们共奏的和鸣呢?可是,吹笛的少年长大了,世界一片寂寥和荒芜。
荒芜和寂寥了的,岂止是笛声呢?那残荷的叶片顶上的那一种嘈嘈切切,看似热闹的一种静寂,何尝不让人孤独到心殇?我愿意把自己的心捧在手上晒月亮,月亮因为骄傲的太阳不屑于月亮的逢迎,是否有了一种糟糕的心思呢?不然它何必在那么深静和涵和深夜,自残了圆满,变得那么瘦削如一枚生锈的金色鱼钩呢?
仿佛和我的来路一样的月夜呀。我说,那从深山里吹出来的风,为什么一直浩浩荡荡吹到平原的草屋的茅檐,苦痛的尘世,将酒公布给贫脊的心灵和丰盈的人生。同时还有珠算。
我们相逢在秋气浩淼的湖边,这湖,应该有一个什么名字才合适,叫相思吗?略显率虚,叫盈圆吧,还觉无力。不如就叫水吧。水是湖的本质吗?但似乎又不拘于些。铿锵之水,你在去往云朵与深海的劫难当中,你在走远的时候,你会捡拾过我的影子吗?你真的收藏过一个孤零的魂魄,并将在合在精美的书页中间而从此忘记翻看而我就一直寄生在了你的那些偶尔划过的睫毛的深影里吗?或者那不是影子,只是重瞳的错光呢。
你说,你要把理想置放于秋千架上,白云苍狗,童谣在郊外发出太阳的味道。砖块收集了陈年的酒香,把质感泡成药。我听到你在梦中哭泣,反复把那页写着我们共同经历的日志翻出残荷一样的声响——于是,这残荷的声音,是一种无可忍受的噪声呢还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天籁?
我爱的你,你的眼神正在远离。在逃跑的那么快,那么矫健,那么彻底,你将消遁于我的人生,把时光诡异的把戏再演一次给我看,给我的人生还有你的人生。你平躺于音乐响起的光明,把大地上最初一次震动传送给我,然后放下发烫的铧。
你说,很受伤。
我把泥土抓起来,放在我们中间。不是要塑你的形象吧,你早已经烂熟于胸。我是要把泥巴捂在你说的那个受伤的缺口上面。它在哪里呢?它只是一个时代共同的创口吗?那么我需要太多的泥土。我去哪里寻找这么多的资源?亲爱的,一想到正在流血,我开始焦躁,想把头碰到那个锐利的铧尖上。
在这样的普遍创伤的时代,谁会有一双流血的刀刃都捏住的大手呢?那顶我头上的那片巨大的枯荷就不是。
留得枯荷听雨声,听到的何止是雨声,那仿佛如泪滴嗒的,也经过了枯荷的放大呢。我从那么远的地方起来,看到花盛放,闻到沁香,听到展放的植物的强声,又被炫光所迷惑,坐在了这里,发一些概吧,我是否还可以捡起业已扔进了树丛的草鞋,继续往我不知道的地方瞎走一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