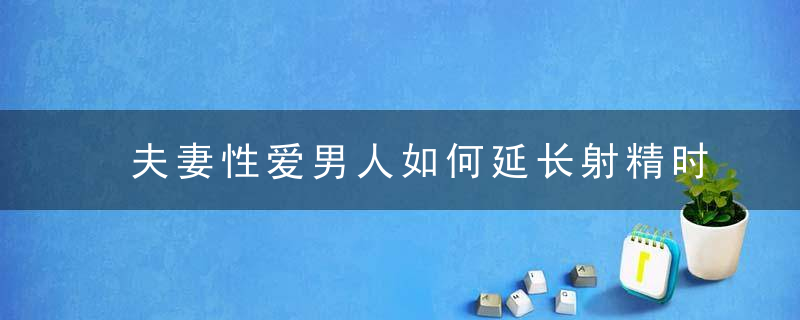我们写作,是因为别无他法

本公号属于经济观察报·书评
编辑/日京川
为了写作你每天走在
喧嚣旁边,走在经久的大海旁边。
—阿方索·科斯塔弗雷达
意大利作家切萨雷·帕维泽在他的对话体作品《与琉科对谈》中写过一则卡吕普索与奥德修斯的故事。
奥德修斯被困奥吉吉亚岛,卡吕普索想让他留在岛上当自己的丈夫,她可以让他获得不朽成为神明,但奥德修斯拒绝了,依然坚持要向着一直以来寻找的岛屿进发,帕维泽重现了两人的拉锯对话,卡吕普索反复劝说奥德修斯“接受眼前的地平线”,否则“你将永远走不出你所知道的这个命运”,而奥德修斯依然坚持要离开向着一直以来寻找的岛屿进发,直到对话终了的时候才揭开这场征途的真相其实是对自我的挖掘:“我把我的岛屿一直带在身上。我要寻找的东西在我心里”。
对哥伦比亚小说家胡安·加布里埃·巴斯克斯而言,他在2018年春天出版的新书《空白地图之旅》中记录下的正是他始终带在身上的岛屿。在这本从他在多家大学担任小说课客座教授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文集中,文学史上的小说经典逐一亮相,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创作者,与文学纠缠一生的终点都是对自己、对每个人类个体的认识与发现。
胡安·加布里埃·巴斯克斯
岛屿之旅的原点是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在瑞士伯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期间,曾为这位德语作家写作传记的加布里埃·巴斯克斯近距离接触过他的手稿,那是一种叫作Kurrent的古老的字体,最多也只有两毫米高,小到需要用放大镜才能分辨阅读。瓦尔泽曾经在所有能找到的纸上微雕一般用这种字体创作。
我们的哥伦比亚作家面对细细密密的手稿,问出了也许所有小说家都曾在某个生命场景里问过自己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我们正在做的这件事?这从人类最私密的命运里浮现出来的、用词语构成的迫切,心甘情愿把一个又一个小时交托给这项艺术,它有什么用?而他所读出的来自手稿的回答是:我们写作,是因为别无他法。所以尽管失败,尽管经济匮乏,尽管没有旁人的尊敬,甚至连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难满足,我们还是要继续写。
《空白地图之旅》中的十三堂小说课讲稿里谈论的便是这样因文学而起的执迷,在作者心中,小说是存在于不同时空的伟大名字挖掘人类共有的空间写下的故事,因此手持空白地图也毫不担心迷失方向,他熟捻地带着读者踏上旅途。
一
由《与琉科对谈》改编的电影《他们的约会》(2006年)
作为一位西语作家,加布里埃·巴斯克斯的旅途从塞万提斯启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班牙,4月23日不仅是众所周知的“世界读书日”、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逝世纪念日,更是传统的“圣乔治节”,以互赠玫瑰与书为传统。节日前后,大街小巷摆满书摊,间或有插满红色玫瑰的花筒在街角出没,加上各式各样的读书活动,堪称读书人的狂欢。
而这场狂欢最经典的保留节目当属一年一度由马德里文学艺术协会举办的《堂吉诃德》不间断接力朗读活动,今年由2017年塞万提斯奖得主塞尔吉奥·拉米雷斯开场,从23日当天下午6时一直持续到25日下午2时,朗读者不乏各界名流,但更多的是属于普通市民的舞台,完全符合富恩特斯的建议:当被问起全世界都应该读的五本小说有哪些,这位拉美文学爆炸主将扳着手指回答道:“《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堂吉诃德》《堂吉诃德》”。
伍尔夫曾说,每年读一遍《哈姆雷特》记下感受,串起来就是我们的自传,因为无论我们在成长中学到了什么,都会转头发现莎士比亚恰好全讲到了。属于加布里埃·巴斯克斯的《哈姆雷特》毫无疑问是《堂吉诃德》。年复一年的重读让他发现,并非小说是人类最好的发现,而是人类是小说最好的发明——人类被忽视的性格、命运与境况成为只有小说能抵达的地方,让我们真正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别人的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
在他眼中,小说式的观看方式与委拉斯开兹的名作《宫娥》中画家本人在镜子里的目光相仿,作家在书中观看世界,也如米兰·昆德拉所言,教会读者对他人的生命产生好奇,试图去理解他们与自己真正的不同。在创作的过程中,小说家甚至比它的作者更早看清,也看得更为辽远。
堂吉诃德身边的人将他的病症归咎于骑士小说,文学作品(无论是创作它还是阅读它)赋予人的想象力把风车变成巨人,叹之笑之,却也令人从中得以想象出另一个自己、另一段人生,因而现实生活也多了几重神奇。加布里埃·巴斯克斯讲起博尔赫斯笔下那个因为急着把书拿上楼意外摔下去的图书管理员。
小说中他出院之后在火车上又把此前的“罪魁祸首”——《一千零一夜》——拿出来消磨时间,紧接着在一场打斗中丧生。而这个故事还有另一种读法,主人公其实死在了手术台上,从来不曾出院,原书的结尾不过是死前一刻他脑海中想象出的场景,这是他本希望选择的热血生活和梦想中死去的方式(而不是因为失足掉下楼梯)。
二
《跳房子》英文版
1962年,阿根廷小说家科塔萨尔送了一册法国诗人亨利·米肖的书给他的文学同胞皮扎尼克,在扉页上他写道“蛇社一致决定将这本书送给阿莱杭德娜·皮扎尼克”,底下有他一人模仿的不同字迹的签名:奥利维拉、玛伽、罗纳德……是的,这正是阿根廷人惊人之作《跳房子》中虚构的文学俱乐部的全体成员。那是《跳房子》问世前一年,皮扎尼克是科塔萨尔身边极少数的几个读过手稿的人,彼时彼刻,这册米肖诗集上的题献仿佛只有对方会懂的私人玩笑,另一个平行空间里的巴黎。
对于爱书人而言,共同热爱的作品里总是有太多可以分享的密码,比如,今年马德里开年以来的气候极为诡异,直到四月才将将从一个极为漫长冬天中拖拖拉拉地走出来,大雨经久不停,加上几位朝夕共处的友人集体失眠,终于有一天大家纷纷表示这简直好似《百年孤独》中连绵不休的大雨和莫名蔓延的失眠症,一时间马孔多的影子垂垂降下来,生出一种共谋的喜悦。
《盐的代价》英文版
读加布里埃·巴斯克斯的新书也常让人遇见这样会心一击的喜悦。阿根廷小说家皮格利亚所言不假:文学评论是自传的一种形式,一位作家以为自己在写他的阅读经历,其实写下的却是自己的人生。
在关于《尤利西斯》的一篇中,作者回忆起第一次阅读这部巨著的经历,那是令他对天职有所顿悟的作品:虽然读得一头雾水一知半解,却让他意识到阅读、创作、研习与小说有关的种种功课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事情。
二十多年后,加布里埃·巴斯克斯已成长为巴尔加斯·略萨眼中拉丁美洲新一代作家的代表,出版了一千四百多页的小说,回望年少时代对《尤利西斯》的痴迷,这部书对他而言犹如一座城市,有的街区熟悉到好似自己建造,有的时常路过,有的令他迷失方向,还有的他再没有去过。
他眼中的乔伊斯,诗意存在于语言的碎片里,哪怕是后来艰涩如《尤利西斯》或《芬尼根守夜人》,文字背后依旧是1907年写下《都柏林人》末篇的诗人乔伊斯。
《尤利西斯》第十六章插图
读书的年岁越久,阅读经历与人生记忆越是难解难分,因而读到加布里埃·巴斯克斯回忆起他与皮格利亚的最后一次对话颇是心有戚戚。
那是在哥伦比亚,后者去世前一年:“他对我说,对他而言,一本书首先意味着阅读它的记忆,读一本书的时候他的人生在什么场景之下。一个人可能想不起一本书的内容,但是如果这本书真的重要,你会永远记得是在哪里读的,记得读它的那一刻你的生命中正在发生什么美好或不够美好的事情”。
想来确是如此。每每忆及最接近幸福的图景,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莫过于伊舍伍德的小说《单身男子》中两人相对躺在沙发的两端:“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书中,同时完全意识到对方的在场”;到了需要裹起大衣的年末,街上弥漫起热红酒香气的时候也会想到海史密斯《盐的代价》里平安夜那天的特芮丝坐在一堆枝繁叶茂中间,手里搂着树,旁边坐着令她着迷的人。她把脸埋进树枝里,鼻息间尽是深绿色的木香,干净仿佛野外的森林。
正如加布里埃·巴斯克斯在序言的末尾写到的那样:“只有爱书的人懂得,有时候一本书才是我们逝去的时光的唯一见证,重读这本书是重返那段时光的唯一方式”。
三
马德里城北的查马丁车站是这座城市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地铁、郊区火车和长途列车都于此交会,再四散开去。虽每日往返却总是跟着人群匆匆,隐约记得在地铁与火车站台之间的换乘大厅墙面上看见过“相遇”的字样,也并未多想,只当是和许多公共场所一样,为了方便人们不至走散而配备的“相遇点”标示牌。
直到某一天,在换乘时定睛看了一遍四周的墙,才惊觉原来此前一瞥见看见的“相遇”二字根本是刷在上面的四个短句:“我们四处游荡,并非为了找寻彼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四处游荡是为了相遇”。一瞬间像是老友重逢,定定地说不出话来。
这句话来自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的小说《跳房子》的经典开篇,所有的偶然里一场最必然的相遇,写在日常车站的墙面上亦如此契合,仿佛浑浑噩噩的周而复始也可以从中得到安慰和一丝希冀的光芒。
人与书的相遇大抵也如此吧。加布里埃·巴斯克斯的这张空白地图,看起来毫不显眼的破旧羊皮纸,但只要念上对的咒语,就会变成《哈利·波特》里的活点地图,那些曾经、正在和将要影响我们的伟大作家的名字在永不消逝的文学魔法城堡里四处游荡,从不找寻我们,却注定与我们相遇,成为我们心中的岛屿。
本文原载于经济观察报书评,原文名《十三堂小说课的岛屿幻想曲》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