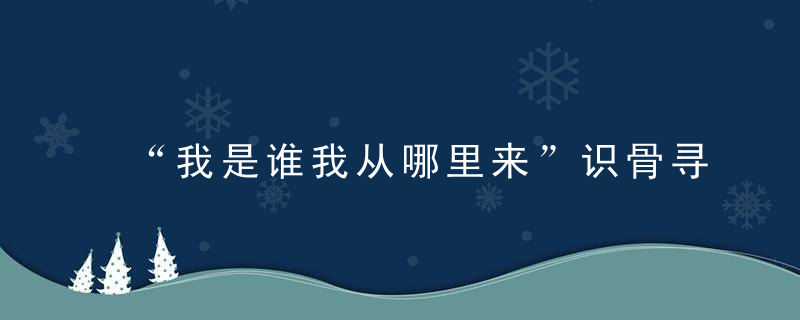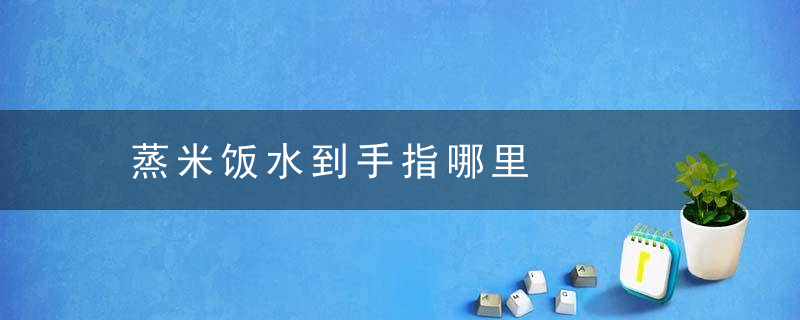中国人这么白,为什么被称为“黄种人”

来自启风居
我们先说一点题外话。
谢霆锋唱过一首名叫《黄种人》的歌,里面有这样几句歌词:“黄种人来到地上/挺起新的胸膛/黄种人走在路上/天下知我不一样”,听上去很是激昂向上。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生活在亚洲的是黄种人,在欧洲的是白种人,在非洲的是黑种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能被称为黄种人,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因为在中国文化中,“黄色”不仅代表了黄帝、黄河、黄土地,还是被帝王们长期垄断的高贵颜色——我们从电视剧里也能看到,明清时代的龙袍都是黄色的。于是,我们从来都不会看着自己的肤色,怀疑一下——这怎么能算是黄色呢?
美国学者奇迈可的著作《成为黄种人》,解释了亚洲人,尤其是东亚人,被称为黄种人的原因。他在书中指出,西方人定义人种时,只有白色才是高贵的象征,至于分配给东亚人的黄色,其实意味着疾病,甚至死亡。由此,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事实——黄种人这个概念的出现,充满了西方人的种族偏见。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在七八百年前,西方旅行家刚刚登陆东方时,东亚人一度被他们称为“白人”,只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东方日益落后于西方,我们才一步步被丑化成所谓的“黄种人”。和黄种人所指几乎相同的“蒙古人种”一词,包含了更多的歧视意味。在西方人眼中,蒙古人种不仅有着丑陋的外表、残暴的本性,还会出现“蒙古褶”“蒙古斑”等人类返祖现象。
让人惊奇的是,这种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种族划分,却让近代中、日两国精英深信不疑。很多时候,这种划分甚至成为他们发起救亡运动的驱动力之一。
诞生于种族歧视下的“黄种人”
本书简体版的副标题是“亚洲种族思维简史”,显然是借鉴了前些年在罗永浩推荐下,风行一时的《美国种族简史》,但其实台版副标题更切合主题,就是“一部东亚人由白变黄的历史”。在《成为黄种人》中,作者首先就举了很多例子,说明在早期西方旅行家的观察中,东亚人是“白皮肤”的。比如13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他著名的游记中,称中国人和日本人是“白色的”;14世纪,另一位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来到中国,记录下,中国人整体是“貌美”的,中国南方人的肤色是“苍白的”。一直到16世纪,葡萄牙药剂师多默·皮列士,依旧是说,中国人“像我们一样白”,日本人和琉球人也同样是“白人”。那时,东亚人被看作唯一能和欧洲人相媲美的人群。
单纯从肤色看,东亚人的皮肤虽然不是黄色,但也完全不同于欧洲人的白色,那西方人为什么要称东亚人为“白人”呢?事实上,这种描述针对的不单单是肤色,也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西方人对自己白皙的皮肤感到自豪,在他们看来,欧洲是“被上帝祝福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只有信奉基督的人才会被赐予白皮肤。
而曾经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东亚的人们,被认为是传说中的东方基督徒。早期的西方旅行家们,都希望能找到这些基督教友。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让欧洲人满怀信心——16世纪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开始信奉基督教,日本人成为西方人眼中“被发现的最好的人”,以及比中国人更“白”的人。
此外,如奇迈克解释的那样,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发展,还处在世界前列,两国人被称为“白人”,也代表了西方人对东方财富的赞扬和羡慕。
但是,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发展,上面这两点原因很快就都消失了,东亚人失去了作为“白人”的资格。先是西方人的传教活动遇到重重阻力。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发现,经过整整15年的努力,广东全省还是只有100名中国基督徒,他对中国人肤色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他失望地写道,中国的小孩儿刚生下来时都是白色的,但是他们长大后,肤色会越来越暗,同时变得丑陋、肥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日本,1614年,德川幕府对基督教发出禁令后,日本人的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被改写,成为橄榄色和黄褐色。至于文化和财富,东亚很快就完全落后于西方,不可能再得到什么称赞了。
17世纪后,东亚人的肤色在西方人笔下,变得多种多样,但无一不是又暗又深的颜色,比如棕色、红色、黄褐色、古铜色、深绿色,甚至黝黑色。华盛顿的一名助手,在看到中国水手后,觉得他们在肤色、外貌、头发,以及身体特征上,都很像北美的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是所谓的“红种人”。这些表示颜色的形容词,通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等不同语言的相互翻译,更是多了一半以上含义,以至于东亚人的肤色,成了一个没人能说清的视觉难题。西方人需要一个统一的颜色,来为东亚人的肤色定性。
完成这一使命的人,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他最重要的贡献,是发明了通行的动植物命名法——“双名制命名法”,就是给每种植物起两个名字,一个种名,一个属名。18世纪中期,林奈在他几经修正,从13页扩充至1300多页的名著《自然系统》里,形容亚洲人肤色时,用了一个表示黄色的拉丁单词,代表丑陋、死亡和幽灵。同时在西方医学中,黄色皮肤还通常被看作是黄疸病的病状。显然,黄色在这里不再仅仅是对肤色的描绘,还包含了对东亚人精神面貌的不良印象。
德国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完善了人种学说,率先使用“黄种人”名称,而且毫无科学依据地发明了一个名词——“蒙古人种”,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被归在里面。他宣称,白人是“最高等级、最为文明开化、最完美的人类”,东亚人和非洲人则被认为是“退化得最严重的种族”,和白人分别处在进化坐标的两端。西方人对东亚人肤色的记录空前一致起来,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1834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史》里,就毫不客气地将中国人定性为“眼睛很小,鼻子扁平,肤色蜡黄”,一点都不好看。
几种被西方人胡乱命名,用来证明黄种人进化不完全的疾病
在讨论了东亚人是怎么从“白”变“黄”后,奇迈可还对“蒙古人种”的概念发展进行了梳理。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鲁门巴哈,法国生物学家乔治·居维叶也提出一个人种划分法,即白种人是高加索人种,黄种人是蒙古人种,黑种人是埃塞俄比亚人种。此外,有关人种数量的说法还有很多,有人说有2种,也有人说是11种,最多的有人划出了37种。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居维叶这个人种三分法被长期保留下来,至今还被津津乐道。
在这里,大多数中国人都忽略了“蒙古”一词在西方的特殊含义。西方人印象中的蒙古,包括了所有曾经侵入欧洲的东方游牧民族,他们席卷欧洲,带来巨大灾难。重创东、西罗马帝国的“上帝之鞭”阿拉提、缔造蒙古帝国的成吉思汗,以及大败奥斯曼帝国的帖木儿,都是欧洲人最为惧怕的蒙古人领袖。当东亚人被和他们划上等号时,形象自然变为丑陋和残暴的。或许唯一让人欣慰的就是,居维叶把黄种人的文明程度向上提了一等,使之成为白人和黑人间的“中间”种族。在他看来,黄种人虽然没有白人那么文明,但也不像黑人那样野蛮,最大的问题是文明长期停滞。
一种标准解释是,中国和日本曾在基督教地区发展之前,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制度,但他们“在很多个世纪中都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表明,无论是在智力,还是能力上,黄种人和白种人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在三个主要人种中,只有白种人是“真正勇敢、自由、慈悲和仁慈的”,受到上帝祝福。按照这个人种逻辑,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既然生来就在智力、能力上有着种种不可改变的差别,那么他们地位不平等,有的做奴隶,有的做奴隶主,也就理所当然了。
为了证明黄种人,或者说蒙古人种进化不完全,身体上存有缺陷,西方人通过一些有限地观察,命名了三种有着歧视含义的病症:“蒙古褶”、“蒙古斑”和“蒙古症”。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几个名词,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看看西方人曾有过怎样的种族偏见。
先说“蒙古褶”,它又被称为“蒙古褶皱”或“蒙古眼”,指一个人眼角皮肤生有褶皱,长着一双小眼睛。西方人很早就在各种旅行笔记中,提到东亚人的眼睛都是“又小又黑”,是狭窄或者凹陷的。比如1687年,曾有中国人来到伦敦,他们被形容为“眨巴着狭窄眼睛的家伙”。葡萄牙传教士克鲁斯写有《中国志》一书,他干脆断言,如果在中国看见有长着一双大眼睛的人,那么这个人的祖先一定来自外国。最后,医学家们拿出了符合那个时代需要的“科学”解释:作为东亚人特征的小眼睛,是由头骨形状决定的,他们下陷的鼻子和突出的颧骨,使面部皮肤出现了多余的褶皱,这些褶皱从上眼皮垂下来,覆盖了内眼角。对于欧洲人来说,只有在童年时期,或者患上眼部疾病后,才会出现这种褶皱。于是,西方人的“大胆假设”好像被证实了:蒙古人种的进化程度仅仅相当于高加索人种的“童年阶段”。
至于“蒙古斑”,是指一个人出生时臀部带有的斑点,提出者是德国医师贝尔兹。贝尔兹长期在东京帝国大学任教,还当过明治天皇一家的“御医”。他在日本工作期间,通过大量观察,发现所有日本新生儿臀部上都长有深蓝色的斑点。索尔兹认为,欧洲白人是不会受到任何颜色污点影响的,于是发表论文,将这种斑点的意义无限拔高,作为蒙古人种和其他人种最重要的区别。不久,有人发现一些欧洲新生儿身上也有斑点。为了维护有关“蒙古斑”的种族歧视理论,索尔兹等人立刻修正说:当年蒙古人西征,使部分欧洲人的血液受到污染,所以在这些人及其后代身上,也留下了“蒙古斑”这种返租现象。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蒙古斑”是非白人血液中多余的色素,是猴子尾巴退化后,残存的一点痕迹。
然而,最具侮辱性的不是“蒙古褶”,也不是“蒙古斑”,而是“蒙古症”。1866年,英国医师唐首次将先天痴呆病称为“蒙古症”,其患者被认为具有东亚人的典型特征:说着孩子般的语言,或者去模仿他人。中国人所说的汉语,确实被当时西方人看作是“缺乏语法形式”“像孩童或聋哑人的语言”。《成为黄种人》里特别引用了一个当时的流行说法,“一些痴呆者也是黄色的,面如土色……而许多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确确实实是黄色的”。于是,在几乎一百年时间里,“蒙古症”都被视为一种只有高加索人种,或者说欧洲白人,才会患上的“贵族病”——得病后,返租成为人类进化的上一阶段,即蒙古人种阶段。也许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当年所谓“蒙古症”,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唐氏综合症”。
通过医学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4种所谓“内眦皱襞”中,只有1种在东亚人身上是常见的;“蒙古斑”也不仅仅是出现在东亚婴儿身上,印第安人、黑人、白人都会有,在中国被俗称为“儿痣”;更不用说,所谓“蒙古症”不可能是白人“独享”的病症,只是一直要到20世纪前半叶,唐氏综合症和人种、肤色无关的观点,才被人接受。
但是,这些说法经过数十年、上百年的讨论,进入了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各种书籍,早已深入人心,不再是科学结论所能改变的了。简单搜索就能发现,中文互联网上,还有大量文章在讨论,诸如自己孩子身上有“蒙古斑”,是否意味着有蒙古血统这样的问题;以及求问自己是不是长着“蒙古眼”的人们。由此可见,当年人种歧视理论的影响之大。
被污名为“黄祸”的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对同一时期的中、日两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奇迈可《成为黄种人》的最后一章名为“黄祸”,讨论近代西方对黄种人的恐惧,及中、日两国由此产生的反应。这一章意义重大,内容却有些单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参考前面提到的那本《病夫、黄祸与睡狮》。
简单来说,在“黄种人”和“蒙古人种”这两个概念出现后,欧洲人被蒙古人侵略的历史记忆就被复活了,发展出流行一时的“黄祸论”。1895年,就是东亚发生了甲午战争的那一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让画师画了一幅“黄祸图”。在这幅画上,代表英、法、德、俄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女神,头顶十字架,在天使的指引下,和来自东方的敌人对峙。这些东方敌人,就是骑着龙的佛陀,龙代表中国,佛陀代表日本。“黄祸图”上面还写着一句很富煽动性的话:“欧洲各民族,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这幅画被威廉二世遍送欧洲各国君主,提醒他们要时刻防范东方黄种人的侵略。
近代欧洲人对于黄种人的恐惧,一是由于日本的极速强大,先后战胜中、俄两个领土广阔的邻国,其中俄国还是一个欧洲白人国家;二是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让欧洲人看到了中国人在反对洋人时的爆发力;三是当时中、日两国都有劳工较大规模地向外移民,被认为挤占白种人的生存空间,造成人口上的威胁。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阻止东亚人的移民活动,那么蒙古人侵略欧洲的历史就要在19世纪重演。美国才长期实行排华、排日政策,也和“黄祸”理论的流行有关。
对于突然流行起来的“黄祸论”,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力驳斥,指出这种说法的荒谬;另一方面也尝试加以利用,希望能借此提升中国人的自信。梁启超在1897年时说,黑色、红色、棕色等人种,他们血管中的微生物,以及脑容量,和白人相比,都相差悬殊。只有黄种人和白种人的差别最小,白种人能做的事,黄种人也都能做。至于所谓“黄祸”,梁启超更别出心裁地积极解释说,西方人很害怕中国人,以至他们经常要用“黄祸”两个字来相互提醒。梁启超将“黄祸论”解释为一种西方对中国实力的变相肯定。
同中国人的诉求不同,在变法后发展起来的日本,希望得到白种人的平等对待,而不甘于和中国人一起被划为低等的黄种人。日本学者田口卯吉在《日本人种论》中声称,西方人将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归为蒙古人种和黄色人种,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大和民族和中国人是不同人种,而和印度、波斯、希腊、拉丁等地的白人同种。欧洲各国对日本人一厢情愿的说法并不认同。十几年后,到了“二战”时,日本改以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领袖自居,充分利用“同种论”,宣扬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放被奴役的黄种人,为侵略战争寻求合理性。
由奇迈可《成为黄种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黄种人”“蒙古人种”概念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东亚人的思想观念。直至21世纪的今天,我们身边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黄种人自居,并感到自豪。其实所谓“黄种人”概念,完全是建立在想象基础之上的,如奇迈可反问的那样,“难道现在不该是停止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吗?为什么我们还要称呼某些人为‘黄种人’呢?”
其实,不只“黄种人”、“白种人”不存在,就是“人种”“种族”概念都并不真实。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国博讲解员河森堡的著名演讲《进击的智人》中,他曾说到,全球各地肤色不同的人,都是同一种人。因为他们不存在“生殖隔离”,个体之间都能繁衍后代。那为什么会有“种族”概念的出现呢?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在《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中的结论,很值得分享给大家。他说,“种族”是一种与客观事实无关的文化构造,一些人可能会关注皮肤的颜色,而另一部分人则关心眼睛的颜色。事实上,基于生理特征所作的区分,并没有科学依据。因此“种族并不存在,它们是被虚构出来的。种族范畴的所指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说法正同和奇迈可关于“黄种人”的研究前后呼应。
随着科学发展和政治观念的进步,现在西方人已经不太使用“人种”及其衍生概念了,那我们自己更没必要再去使用“白种人”“黄种人”这种伪科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