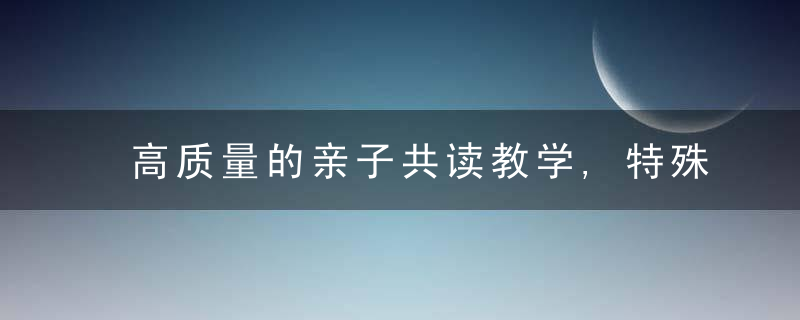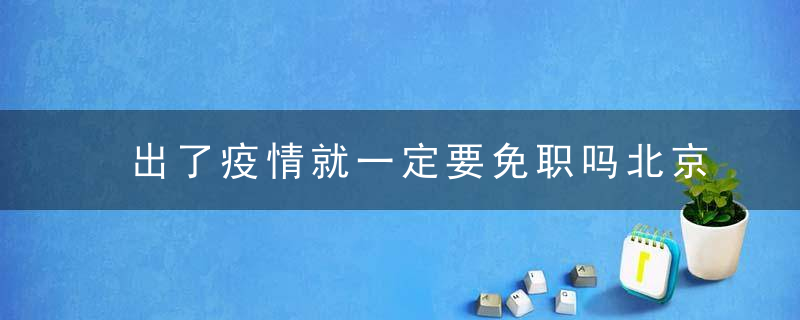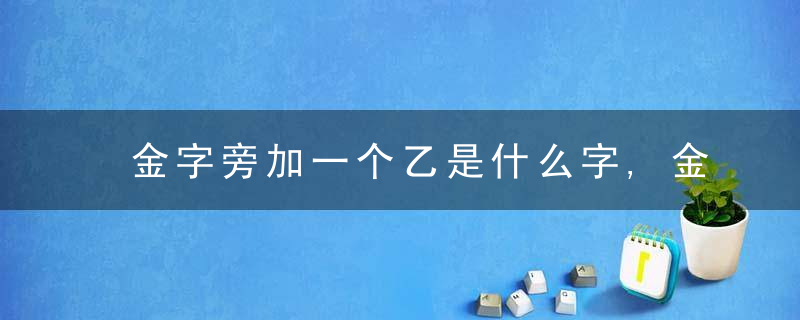如果父母永远无法接纳我本来的样子,我该怎么办

昨天一直被儿童节的欢乐气氛包围,可爱的孩子和慈爱的父母是最主要的过节群体,他们的彼此陪伴和笑脸,是尘世幸福的最佳证明。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在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面。
人们经常把生孩子当成一种“生命的延续”,但这件事最不可控的一点就是,即便确知ta是两个人基因的叠加,但ta仍是一个全新的个体,有可能展现出和父母双方都大不一样的性格禀赋、健康状况或人生选择。在很多时候,这将成为家庭中一系列痛苦的根源。
对于父母,一个和自己的预期相距甚远的孩子会让他们措手不及、难以招架——比如,一对身高正常的父母,如何面对一个侏儒孩子的人生?当得知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又该怎么应对?而对于孩子,发现自己并不是父母想要的“那个孩子”,又会遭遇多大的身份认同危机?如果父母永远无法接纳自己本来的样子,“我”该如何与家庭和社会共处?
《背离亲缘》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用十年的时间走访了300多个拥有“异常”孩子的家庭,这些“异常”包括生理疾病或障碍——听障、侏儒、唐氏综合征、自闭症、精神分裂症、重度身心障碍;也包括在社会上总被视为异数的神童、遭奸成孕、罪犯、跨性别。这些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并且总是经受着异样的目光。走近他们的生活,就是摒弃旧有的恐慌、歧视、异见的过程。在安德鲁·所罗门的讲述中,我们能随他看到痛苦,看到残酷和多样,但也看到最深沉的爱,并且不由地重新思考对生命的判断与认知。
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美国政治、文化、心理作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临床心理学教授、康奈尔大学威尔医学院精神病学讲师。曾获得生物精神医学学会人道奖和大脑与行为研究机构的生命贡献奖。作品有《走出忧郁》《背离亲缘》等。
面对身体障碍: 修复,还是接纳?
安德鲁·所罗门最早的调查从听障家庭开始,那是在1993年,他受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的一项委托。当时他想得很清晰,认为听障就是意味着缺乏“听”这项能力。
但当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走访,这一简单明了的想法变了。他发现,那个无声的、要靠手语或者解读唇语来交流的世界,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丰富。甚至,对为数不少的听障儿童来说,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听不见,而是父母不惜一切努力,想让孩子在有声世界里正常生活。
在听障女孩米莉安的家庭,她和父母关于口语教育还是手语教育的矛盾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米莉安失聪时是1961年,还没有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父亲菲力克斯和太太为女儿选择了口语教育——这要求她花费大量的时间,通过学习挤压脸部肌肉和移动舌头来练习口语。在他们家中,手语是被禁绝的,“要是米莉安比划了手语,我们会打断她的手”。这是父母为了女儿能顺畅地融入社会所做的选择,看起来无可厚非,而米莉安的唇语也学习得很好,足以进行日常交流。
直到15岁时,米莉安参加了一次冬季听障奥运会,这是她第一次沉浸在以手语为主的环境当中,她找到了此前不曾体会到的归属感,并从此进入了聋人的社交圈。很晚才开始学习手语的她,成年后选择在所居住的加州小镇开设犹太聋人社区中心,与人沟通时大约八成用手语,二成用口语。再后来,她结婚生子,孩子也是听障。与自己的父母不同,她让他们自小学习手语,因为这条路对于他们来说更容易,也很快乐。
基于安德鲁·所罗门《背离亲缘》完成的同名纪录片Far from the Tree.
回顾自己的语言学习历程,米莉安认为“要是我小时候可以比画手语,所有语言都能学得更好”。这一观点能够得到相应的印证。因为人在幼年时期的语言习得关键期非常短暂,主要集中于18-36个月这段时间。对于听障儿童来说,学手语要比学习口语顺畅的多。而一旦儿童过了关键时期还未学会任何语言,就无法发展完整的认知能力。——因为第一语言的重要性,很多在听障家庭长大、以手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听障孩童,反而比父母是听人、家里说英语的孩子更有可能学会顺畅的书面英文。
很多聋人会长期沉陷于因听力缺失而自卑的情绪里,非常想要改变它。但也有许多人——比如米莉安,在聋人社会真正找到了自我。在人工耳蜗植入术诞生之后,她的父亲曾想让20几岁的米莉安动手术,后来又提出要给每个孙子100万来植入人工耳蜗,但都被米莉安拒绝了,她热爱聋人文化。安德鲁·所罗门在聋人的圈子中看到,“一般文化总感觉听障儿童缺乏某种东西,即听力;聋人文化却觉得他们拥有某种东西,也就是这种美好文化的会员资格”。
所以对于拥有听障子女的父母来说,这意味着一个选择:是接纳,还是不惜代价去改变?它也让我们可以借之讨论更大的问题:是否应“治愈”或消除所有“缺陷”?人类社会能包容多大程度的多样性?
延伸阅读
《残障:一个生命历程的进路》
作者: [英]马克·普里斯特利
译者: 王霞绯 / 李敬
版本: 人民出版社 2015年7月
该书讨论残障人士在社会生活中的经历,即社会是如何排斥他们享有充分参与的权利的,而他们又是如何抵抗这些排斥的。
类似的选择难题,安德鲁·所罗门在侏儒的家庭中也看到了。侏儒们是备受歧视和嘲弄的族群,在生活中他们不仅要遇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和健康问题,也永远要承受异样的眼光。他认识了出身纽约望族、曾是芭蕾舞者的丽莎,她的女儿萝丝是侏儒症患者。丽莎虽然也会因为女儿无法像自己那样生活而伤感,但她还是尽己所能给女儿最多的爱和扶持,萝丝甚至在和身高正常的孩子一起参加的骑马比赛中得了奖。
然而,当她们与其他侏儒孩子的家庭交流时,看到有家庭选择让孩子接受骨骼延长手术——这种手术会反复打断骨头、延长肌肉,以此增加身高,一向很有争议。丽莎说:“我更害怕的是那个年纪的孩子正在不停培养自我认同、找出自己是谁。他们要怎么活出最好的自我?像这样不停地东修西改,不可能做到。”
但做出丽莎这样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安德鲁·所罗门在书中使用了一对概念:“垂直身份”与“水平身份”。前者是指会一代传一代的身份特质,比如种族、肤色,以及通过共同的文化规范传下去的语言、国籍、价值观等;而后者是指那些与父母不同的后天性状,例如肢体残障、神童、自闭症……这些人必须要从同伴而非家庭获得身份认同。对于绝大多数父母来说,接受孩子的水平认同是很难的,他们会因此误解自己的孩子,甚至视其为羞辱。
电影《心灵驿站》剧照。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性格安静、身有侏儒症的男人,在遭遇众人的指指点点和嘲笑后选择远离人群,另外获得人生温暖的故事。
于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最大的痛苦往往存在于父母而非身有障碍的孩子。作为一个同性恋人士,安德鲁·所罗门从听障和侏儒家庭中看到了自己。他爱他的母亲,但他的母亲不希望他是同性恋,因为她全心相信自己所认为的幸福是最好的。她难以接受自己是“男同性恋之母”,这让她不自在,她想改变他的性取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想控制自己的生活。从这一点,他感觉到了自己与聋人、侏儒等身份之间有共通点,他们都属于微不足道的少数,但“与众不同让我们成为一体”。
当面对修复还是接纳的选择,安德鲁·所罗门更倾向于接纳。在他看来,“若一个人的核心自我被视为病态、不合法,他可能难以区分这样的自我和更严重的罪行有何差别。把身份认同视为疾病,会导致真正的疾病,让它变得更加猖狂。”
爱一个人,也可能觉得对方是个负担
但是,养育听障和侏儒孩子,在这本书所涉及的十种家庭中,实在要算是十分“容易”的。他们虽然有一定的身体障碍,可在智力发育水平和情感沟通上与常人无异。相比之下,如果孩子是一个自闭症儿童,或者在青年阶段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又或者自幼就有多重重度身体障碍,只能靠重度医疗介入维持生活,那想说“接纳”和“爱”才真正无比艰难。
在《背离亲缘》中,安德鲁·所罗门虽然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文字用心讲述“努力接纳孩子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但更让人感动的却是,他从来不回避艰辛和痛苦,不塑造没有瑕疵的情感和道德神话。
自闭症是近年来受到较多关注的病症,媒体和书籍都给予了许多报道。安德鲁·所罗门不满于两种最常见的故事类型:
现在有两派传说,走向相反,但造成的问题却几无二致。一派传说源于自闭症父母的各种奇迹记录,其中最为极端的,是记叙美好的男孩女孩从病痛当中走出,仿佛一切不过是冬霜,春阳一出自会消融。……这样的故事给人错误期待,完全抹杀了家中有人诊断出自闭症所面对的煎熬。另一派传说的主要剧情是孩子并未好转,但父母却不断成长,最后不再想要改善他的状况,反而加以歌颂,而他们对于这样的转变也十分满意。这同样粉饰了很多家庭面临的困境,也可能让人看不清自闭症的各种真实缺陷。
电影《雨人》剧照。在关于自闭症/孤独症患者的影视作品中,他们似乎总要展现出某种特别的能力,或上演“奇迹”的人生。
在他的书中,我们看不到那些具有绘画天才的自闭症儿童,读到的往往是痛苦不堪的母亲父亲,比如把自闭症女儿送到安置机构的妈妈贝琪说,她终于愿意正视自己不喜欢去探视她,养育女儿的经历,经常让她觉得“任何曲线相似的物体都可以取代我”。在女儿送去安置后的三年,丈夫因抑郁症发作住院两次,而她自己因抑郁症住院三次。又比如表示如果重来仍然愿意嫁给丈夫的南西说:“但不要有这两个小孩。我爱我的孩子吗?爱。我什么都会帮孩子做吗?会。我生了孩子,做了这一切,也爱孩子。但我不会再做一次。我觉得,要是有哪个人说他会,一定是在说谎。”
他呈现出真实的、并非毫无保留的爱,不责难父母的矛盾情绪。“爱一个人,又觉得对方是个负担,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延伸阅读
《让爱重生:自闭症家庭的应对、接纳与成长》
作者:罗伯特·纳瑟夫
版本:东方出版社 2017年4月
作者罗伯特·纳瑟夫博士是一位心理学家,也是一位自闭症患儿的父亲。他同时从个体经验和专业领域,讲述了自闭症家庭所要面对的许多现实问题。
如果不切近地感受到少数族群生活的艰难,不真正地体会过每天去照顾生病孩子的生活压力,那么站在道德的高点上,呼吁接纳、权利,是容易的。但真实的生活呢?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1997年出生的艾希莉,患有静止性脑部病变,她的身体功能十分有限,一辈子都无法说话、走路、自行进食,也无法翻身,只能睡觉、醒来、呼吸,以及微笑。尽管如此,艾希莉的父母还是用心地照顾她、陪伴她,把她称作“枕头天使”,因为她总是躺在枕头上。
但有多重身心障碍的艾希莉在长大,她的体型变大,体重越来越重,这让照顾她的工作变得更为艰难和繁重。她的父母找到医生,希望通过注射激素延缓她的成长,好让搬动她变得容易,减少褥疮和感染的概率;并且提议摘除她的子宫和乳蕾,避免将要带来的月经和经痛。他们最终说服了院方的医疗道德,手术顺利地进行了,艾希莉将永远保持儿童体型。
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案例公开后,引发了轩然大波。女性主义者和身障社运分子对此谴责:假如艾希莉是个正常儿童,而父母要求执行残废手术,绝对会被关进牢里,那正是他们该去的地方,而那些医生应被吊销执照。艾希莉的爸爸不得不隐姓埋名,但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认为像这样的集体理想和意识形态,完全不顾“个体是否得到裨益”。而安德鲁·所罗门也认为,对于艾希莉这样的孩子来说,手术所剥夺的成长,并不比生活的艰难更让她没有尊严,有些运动人士觉得这手术并不是为了艾希莉好,而是为了减轻她父母的压力,“但这两件事原本就是一体两面”。
这与他对待听障、侏儒、唐氏儿家庭的态度有所不同。在这部厚重的书中,安德鲁·所罗门讲述了近百个不同家庭的故事,但极少使用数据,从不使用图表,因为“数字隐含着趋势,故事则承认其间充满分歧”。而分歧,不同,才是更真实的生活。
今年年初在国内上映的电影《奇迹男孩》,讲述了天生面部畸形的男孩奥吉的故事。
即便深受歧视,也同样会歧视别人
安德鲁·所罗门说,他在书中述说了“一则则关于韧性的英雄史诗”,完成这本书的过程,就像“上了一堂关于接纳的课”,让他明白了艰难的爱绝不下于轻易的爱。书中的那些父母,经受了自己从未想象过、无论如何都想要避免发生的事情,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爱自己的孩子,也爱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在一个健康、顺利的家庭中,爱是自然而然的,那么在这些家庭中,爱确实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特异的孩子能凸显父母的秉性,“原本只是不称职的父母变得糟糕透顶,原本称职的父母则变得极为出色”。
但就阅读体验来说——或许因为关于爱的故事经常得见,此书给人印象更深的始终是那些具体的艰难,和人们如何对待差异的态度。
在日常生活中,畸形的形体、怪异的秉性总是让人避之不及,安德鲁·所罗门自己也说,他“自幼就畏惧疾病与障碍”,看到太异常的人,总想别过目光。是完成这本书,探访数百个障碍儿家庭的经历,才帮助他摆脱这种近乎本能的冲动反应。
《背离亲缘》(Far from the Tree)英文版书封
而他在采访的过程中还发现,“并不是只有自诩为主流的人才会做出负面的判断。我的受访者除了书中跟自身有关的那一章以外,听了其他章节几乎都有些不舒服。听障者不希望别人把自己和精神分裂症患者相提并论,有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父母觉得侏儒令人不自在,罪犯受不了自己居然跟跨性别者有共同点,神童及其家人不愿意和重度障碍者出现在同一本书中,有些因强奸而出生的孩子则觉得如果把他们和同性恋运动分子混为一谈,无异于小看了他们的心理煎熬,自闭症者则指出唐氏综合征者的智商都比他们低。”即便这些人都深受社会歧视之苦,也忍不住要分出你低我高。
如此真实的反馈让人无奈——没有歧视的尊重和包容,也许只存在于理想和童话。在《背离亲缘》中,虽然十种不同的艰难状况让他们同样成为少数和边缘群体,但他们所面对的又各不相同。将他们置于一书的安德鲁·所罗门并未混为一谈,他的研究打破了清晰明了、单一的思维逻辑,也让我们很难简单地概括出整本书的“核心价值”。是爱?是生命?是病痛和障碍?是差异与社会认同?大概都有。
能否准确的概括不是重要的事。这部厚重的作品的最重要意义或许在于,它通过文字将我们带去人生与社会的边缘地带,让人在陌生中有所反思,动摇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便我们不是侏儒、听障、自闭症、跨性别者……谁又没有缺陷或特异之处?我们是否总是倾向于不假思索地,害怕那些“奇怪”的差异,并努力将其根除?虽然医疗进步让一部分身心障碍趋于消失,但在社会层面,我们是否有可能走向更大程度的包容?看起来遥远而“与众不同”的故事,距离“正常人”的生活和自我认同,也不见得就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