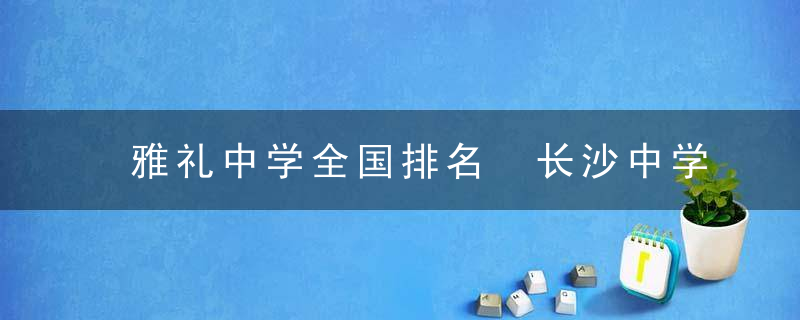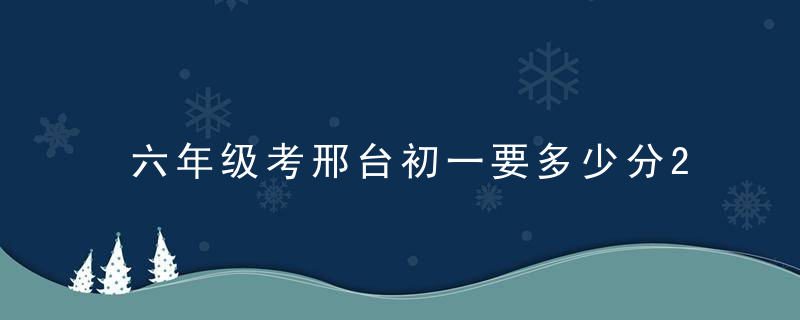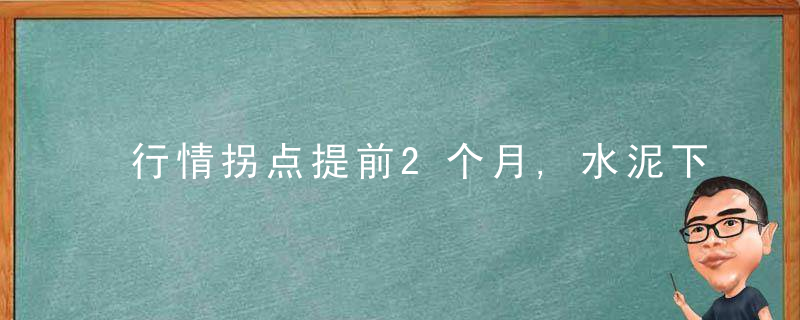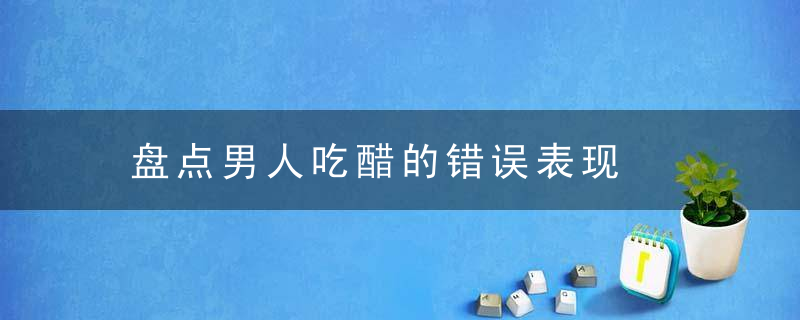一个北京姑娘跟我说,千万别跟北京人说高考容易

敲开隔壁的门,理直气壮地要求邻居停止使用抽水马桶的时间又到了。
说的是高考。
根据一位每到此时总在处理这类事情的警察概括,有的家长将杀虫剂用在青蛙身上,为了消除夜半蛙鸣对孩子的影响;更偏激者,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从20米外的高空向下泼水,目标是一头雾水挂在半空的空调安装师傅……
环保局、城建局、城管局、交管局乃至海事局,纷纷体贴地公布了噪音污染投诉热线。寺庙神像前祷告的香客里,多了不少学生和父母。
我是乡下来的,每回见到这严阵以待的阵势,想起高考前夜我们一群乡下孩子头一次寄宿在县城的考点,聊天聊到凌晨,总有一种对自己命运破罐子破摔不负责任的负罪感。
(一)
自北京奥运会以来,我第一次见到倒计时牌,是在安徽的毛坦厂中学。
忘了是去年的哪一日,但不难推算:校园里所有的电子屏幕都在提示,“距离高考仅剩204天”。
毛坦厂中学外号 “亚洲最大高考工厂”,生源不佳,但通过争分夺秒的苛刻训练,将一些原本升学无望的孩子送入大学。当地每年送考生赶考的车队浩浩荡荡,是高考前一景。毛坦厂镇有一棵“神树”,只有它知道自己安慰过多少快要崩断的神经。
6月3日晚,毛坦厂镇,考生们放飞孔明灯,灯上写着他们的心愿。第二天,他们将各奔前程,参加7日开始的高考。赵迪摄
一同去造访的人十分好奇,问长问短,不断将毛坦厂中学与大城市的中学作对比。我反而见怪不怪了,甚至有一种故地重游的错觉,因为跟我读过的中学过于相像——都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小镇上的“最高学府”,都接收了不少高考复读生,连让外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作息制度也那么相似。
我们当时每天早晨五点起床集体跑步,然后是早自习,晚饭后还有两节晚自习。各科老师还很喜欢占用自习课补课——如今回想起来,他们堪称业界良心,不会为此收一分钱。没有食堂,每个人的课桌同时也是饭桌。学生出校门要请假,每个月可以回家一次,“军事化管理”。每一次考试成绩和排名都要公布,在校园的几面外墙上,公示着每个学生的“最高机密”。每场考试,学生的考号就是上次考试的名次,假如考号一直是“一号”,连监考老师都知道你是个苗子。
因此,对我来说,毛坦厂中学真没什么稀奇的。我经历过的一切,它只是放大了一号,最多算是集大成者。最早听到外地的此类中学,我曾怀疑它们都是在拷贝老家山东的那些中学。山东考生众多,自身缺乏足够的高教资源,是高考竞争最为激烈的大省,或许这类中学的生存之道都是相通的,查不到谁是始作俑者。
我的班主任书法不错,他的杰作是一张表格。每次大考后,他工工整整地手抄榜单,制成表格。不仅登记最新成绩和排名,还有一栏是“目标”,比如第二名第三名的目标可能是第一,第二十名的目标也许是进入前十。它一定有威慑力,因为班主任把他的发明贴在黑板的一侧,国旗右下方的位置,并且字体大小得当,确保最后一排的人抬起头时也会看到它。
不过,我们的“目标”也就到此为止了。不记得谁说过自己打算考入什么样的大学。对于大学,大家都所知有限。老师们大都没有读过本科,某位老师总挂在嘴边的一个得意门生,考到了江南某所师范大学,以至于我当时以为这所大学相当出众。一位读过中专的邻居则告诉我,北大、清华、南开、复旦是最有名的学校。《泰坦尼克号》是我知道的第一部好莱坞电影,因为刚分来的语文老师眉飞色舞地谈论过那艘大船。她在电影院欣赏过,而那时我们没人见过影院。当时也还没有网络,假如那年高考作文题是关于一个什么流行现象——只要不是杰克和露丝的爱情,我们一定死得很惨。
(二)
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认为这样的学校在批量制造“高考机器”,就像他们批评毛坦厂中学那样。但我绝不认为自己是“高考机器”。我们没有机器咬定目标不放松的劲头,课业压力不重,毕竟没人有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机会。我当然偷看过武侠小说,违反规定在午休时间打过球,还写过诗和小说,那是最不花钱的爱好。
事实上,我想起高中生涯,一直觉得过得很愉快。
对我们来说,真正的天花板在于,那真是一个小地方,一个农业区,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经济条件总是有限的,这很大程度上限定了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质量。我们的父母和老师都没考过大学,或者高考落过榜,但他们努力想把我们送到大学里去。当我后来见识到“读书无用论”,我意识到这份努力是令人尊敬的。
读大学前我没见过电脑,大学的电脑课上,我真的像个傻瓜一样不知道怎么开机。有一段时间为了打字跟上节奏,我在脑子里幻想出一个键盘,日常每说一句话,“你好”“怎么回事”,就用手指指指点点,对着桌子或者空气打出“nihao”“zenmehuishi”。因为这个习惯,现在我打字的速度跟速录师没有太大差别。
还可以举的例子是外语。大一时我鼓起勇气向一位和善的英语老师诉过苦,告诉她我听不懂课上在说什么。一位高年级学生负责听课后对我给出评语,记得她的意见是“英语带有明显的口音”。
不过,小地方自有它的优点。它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空间里,让比较单纯的学生更容易做到心无旁骛。我一定是受益于此。
那时,一位学长喜欢在半夜熄灯后用功,毕业时他的床下翻出一大堆废旧电池。我有个同学也是这么做的,他被窝里的手电筒灯光和他的近视镜片一样让人印象最深,但他最后落榜了。还有一些同学是复读生,有人复读了好些年。
我不知从哪里读到一个故事,是说天津的一名考生,家境贫寒,父亲重症,母亲为了供他上学吃尽了苦头,为了省钱专门去批发那种压碎了的方便面来吃。他很争气地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去了北京大学。
直到2018年,我才知道那是一碗“毒鸡汤”。那人如今是北大的一名数学家,成绩是真的,但关于他家境的事情大都是写手编的。他澄清说,那个故事“连我自己看了也会很感动”,可它是假的。虽然他一遍一遍澄清,但人们仍倾向于喝下那碗苦情的毒鸡汤。
这是一个高考优胜者20多年历经的魔幻现实。而当初我记住这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格外励志,而是好奇哪里能买到压碎了的方便面。方便面,手电筒,以及班主任贴在国旗侧畔的独门表格,都没有对懵懂单纯的我起到“励志”作用。我一直是学校的第一名,在那张表格上的目标设定为“市第一”——我高考时确实考了那个县级市的第一名,但不认为表格有什么魔力。
我的高考并没有特殊的记忆。它很快过去了,跟每场考试一样,只不过这一次,班主任不再需要制作表格。它的使命结束了。
(三)
高考并没有结束。
有一年,我去吉林报道揭露一起举国震惊的高考作弊丑闻,感到特别沮丧,没想到有这样明目张胆的事情。
在大街上跟一个考生聊天,小姑娘大大方方地告诉我:“我就是那种——高考移民。”她来自东北另一省份,承认家里给造了假户籍和学籍,到那里高考是因为“可以作弊”。
高考的游戏规则是以学业成绩来衡量上升机会——这也是它多年来最受认可之处,而维持其公正性的前提是对规则的遵守。我曾以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让我沮丧的是,也许一直都不一样。
跟毛坦厂中学一样,我当年的中学接收了一些外来的学生,来自城市,希望在乡下中学磨练后回去高考。也有人尝试做高考移民,最常听说的目的地是东北,以至于我当时一直以为东北高考容易。后来才知道,东北比山东“容易”,在全国绝对不是“容易”的地区。
6月4日晚上,毛坦厂镇,一名复读的同学仍在自习。前一天学校已经放假。赵迪摄
可我依然觉得自己的高考很容易,跟一个北京姑娘聊这个话题,她说了一句,“别在北京人面前谈高考容易”。
我明白她的意思。北京人高考确实“容易”,京津沪这种城市的高录取率摆在那儿,竞争的惨烈程度跟高考大省不可同日而语。
这位姑娘的同班同学全都进了“985”学校。我跟她同一年读大学,班里60多个同学里,达到本科投档线的是个位数。而在我读过的初中里,只有成绩最好的几个学生考上了高中。现在,我上过的第一所小学,上过的初中和高中,都随着“教育资源的调整”,被取消了。连县中也在衰落,在有些地方,全县没有一名考生达到重点大学投档线。而在大城市最有名的那些中学里,最好的学生好几年前就不参加国内高考了。
外地人在北京人面前谈高考,总是有点愤愤不平。不少人觉得北京人考分低,自己的成绩在本地虽然上不了什么名校,但到北京的话,“考个北大清华很容易”。从录取率来说,在北京考个大学不难,可你要跟北京家长说高考容易,他们一定会拿眼睛“白”你,因为大家的竞争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
本来,省际之间简单比较录取分数线,也没什么科学性。一则高考试题并不统一,就算都采用统一试卷,只要阅卷分省进行,标准不一致,分数线的比较意义就会大打折扣。更何况,人们常常是拿不同年份、不同省份的分数线任意比较,即使在同一省份,同样690分,两个年份的690分,全省排名可能大相径庭,录取机会当然不同。
高考成绩受教育环境影响很大。人都是这样,只要置身于某一个环境,就会尽量适应这个环境的规则,在有限的条件下求得最优解,哪怕并不一定喜欢那种环境。衡水中学的一位河北省高考“状元”后来回忆,他常常看到媒体对于衡中的批评,但不会细看,因为“知道会说些什么”。他还说:“虽然我也不太赞同那种模式,但如果我以后的孩子只能在河北高考,我也还是会选择衡中的。”
你看,都是求最优解而已。
北京和上海这类发达地区,由于教育资源充裕,学校师资、理念和硬件都优于其他地区,学生家境及父母受教育程度也都领先,教育质量领先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即使刨除其他条件,只谈师资,一所中学的教师都没有大学学历,而另一所中学讲课的全是名校博士,哪一所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高不言而喻。
由于较早开展素质教育,北京学生在应试的准备上无法跟“高考工厂”比较。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应试能力就不可以训练。假如真的像不少人所期待的那样,全国一张试卷统一录取,北京这类地区也转入应试模式,结果如何还真的很难说。
你到各个名牌大学教务处去转一转,看看学业成绩排名就会知道,北京那些所谓“低分”考生,入大学后的表现并不差。两院院士是学术发展的最高点,根据60年内两院院士的信息来看,无论按籍贯还是出生地,京沪两地都在十分靠前的位置。
反倒是一些“高分”学生,入了大学后可能出现不适应。我读大学时,一名来自山村的“神童”就很传奇。他先是未成年时就被保送入校,但痴迷游戏,直到被劝退。他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参加高考,又以全市数一数二的成绩考了回来。但最后,因为同样的原因,他又退学了。
两进两出的“神童”说明,在一场长跑中,起点决定不了终点。必须承认,起跑线的不公平是存在的,影响因素有个人天赋,也有客观环境。有时候脱去中学的校服,人们就会看到,同学间早已分野,只是被校服遮盖了。很多事情,高考前已经决定了。现状很难短期改变,优质资源就是僧多粥少,从入学、求职到就医,其他资源又何尝不是?
信奉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将命运寄托在一场考试上,跟信奉“范进中举”没什么区别。其实高考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弊端。对普通人来说,高考之后,人生的竞争还有太多。说句“鸡汤”话:每一天都是在为明天积累机会,高考改变不了命运,相反是人生的一次次选择改变了命运。
所以,我能够理解毛坦厂中学,能够理解那个北京姑娘,但是无法理解那些为了孩子理直气壮要求隔壁停用抽水马桶的人。归根结底,一次考试考得不好,心态就要崩了,就要寻死觅活吗?
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调侃说:“不要年纪轻轻就觉得自己到了人生低谷,你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