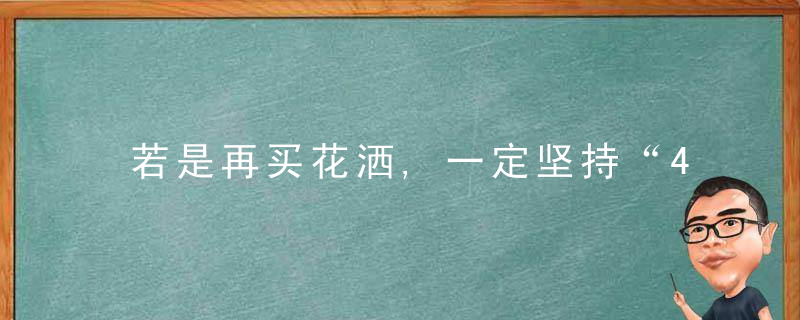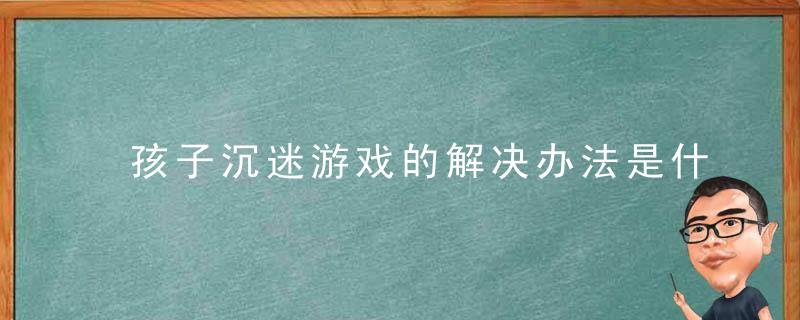关于“堕落”“颓废”——与罗昼先生交流三点意见

认真拜读了罗昼先生上月发表在价值中国网的《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两帖。先引罗昼先生在《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一文中用在年轻人身上的批评语句:
“他们一旦离开了中学校园,甩掉了书本,便渐渐地和中国优秀的文化远了。”
“有的干脆在中学时期脑子里就丝毫不见中国文化的烙印。”
“他们忙于炒作那些原本不值得炒作或根本就不是什么东西的网络‘文学’。”
“他们还忙于通过QQ和对方视频见面乃至同城一夜情、异地交欢等等。”
“他们对一切正常人的生活习惯、交流礼节似乎都因为看不惯而格格不入。”
“他们在自己的网页中、博客里热衷于谈论女性器官和性欲发泄。”
“他们自称‘狼友’,并以‘狼友’为荣。”
“也更有一些女人,一到网上就脱去平时端庄、文雅、秀气、稳重的外衣,顿时变得让人不敢相认,‘色’得更胜过那些自称为‘狼友’的男人!”
“这是什么文化啊!这根本算不得文化,纯粹是性乱和堕落!”
“他们将这种崇尚变成了一种崇拜,只是自己不知道,这样的崇拜该有多么地颓废!”
“他们甚至已经不会使用真正的国语来写点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人的精神也由此产生变态。”
“他们在单位、学校、人前是一套,而到了网上则是另外一套。甚至在网上更显得生龙活虎、不可一世。”
“中国‘垮掉的一代’的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可以组成一个小国。”
“他们的这个小国里,大概不要道德,不要良知,不要真情,不要法律。”
“他们要的大概只是偷拍、偷窥、乱伦、乱交、乱性和自以为是的推崇。”
罗昼先生在文章的最后说:“究竟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改变这一现状呢?”有感于罗先生担忧和求解的恳切,特写三点意见与罗先生交流——
第一,“立场”问题
罗先生上述批评、定性的话语,显然是站在与这些年轻人对立的立场上、至少是站在这个群体的情感和观念之外不高兴地看着他们来说的。站在这个“对立”和“之外”的立场上说话,会产生两个不良的后果。
首先是难以理解他们。我们世俗之人都是情绪和观念的动物,容易立足一己一地、依着本能情绪和固有观念看问题。如果本能地、先入为主地和某个群体对立起来,就会把他们看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就会忽视他们潜在的优点。例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有个在云南服役的山东士兵很“坏”,坏到有次竟把一个盛着饭菜的大碗朝炊事员脸上盖过去,他经常不守纪律,训练偷懒,还喜欢弄恶作剧。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没希望、不可救药了,若不是接着爆发的战争,他可能就被开除军籍回老家了。但是在接着发生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却表现无比英勇,立了赫赫战功。例如有次他负责往山上送水,在枪林弹雨中手臂被打断,依然用另一只手抱着水桶往山上跑;跑到战壕里的时候,腿也被打断了,但他出色、圆满地完成了送水任务。据说在美国军队里,军官特别会使用有各种优点和缺点的人,不像我们这样死板、机械、片面和“严格”地要求,因此战斗力很强。前年我听到一个和罗先生一样对年轻人很不满意的领导人说,他对现在的年轻人很失望,如果大陆和台湾打起仗来要招志愿兵,不知道会有几个敢自愿报名上战场的!我当时说真要到那个时候,英勇无畏、冲锋陷阵的还是这些平时不被看“好”的年轻人,而不是我们这些道貌岸然、满口仁义的谦谦君子。
总之我们看人要全面一些好,不要把人看得一无是处。如果我们站到年轻人当中去,便会发现他们很好相处,有很多优点,了解不少异域文化,而且很有乐趣,尤其是他们充满生命活力的奇思妙想,可以激发人的想象能力和创造灵感;并不是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走马观花、只看表面现象和怀着固有观念道听途说、凭一面之词所感受和想象的那样“坏”和不可救药。
其次,我们以对立的眼光看待后人,他们中间就会出现更多真正的坏人。年轻人年轻气盛,逆反心理比较强,我们每个成年人年轻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和他们对立,就会像夫妻对立那样,你进一寸,他进一尺,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就要闹翻天、闹离婚。由于世俗之人都是情绪和观念的动物,在矛盾对立中,即便你有真理在手,对方也会完全把它看成谬误,最后就一不做二不休,彻彻底底地对立起来,真正的坏人也就成批出现了。所以有些坏人甚至罪犯,根本上是由我们的对立情绪和观念制造出来的,例如前几年的恶性杀人犯张军、马加爵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各层各类人故意制造的对立情绪和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培育犯罪的土壤。我想如果我们全中国的成年人,都表明前引罗先生那套语言所包含的对立态度,中国的坏人、罪犯不知要增长好多倍啊!“文革”时期有一句口头禅,叫“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如果我们这一代人都持罗先生的观点,那就真会把“接班人”都送给“资产阶级”了。
我们对待年轻人,应该要做一件不费举手之劳、而只需要放下架子就能做到的事情——尊重他们。做到尊重年轻人这一点,关键是要改掉我们成年人故意制造鸿沟和对立的一些本能做法,去掉一些固有僵化的观念,和年轻人站在一个立场上和战壕里,主动地先去理解和关心他们。年轻人还处在事业、人生的起点阶段,他们缺少社会地位和尊重。我们帮助、引导、感化他们最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要平等地对待和尊重他们。迄今为止世俗社会最系统、最完整的知识都是关于等级的知识,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完美的典章制度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等级森严的体制规范,无不把从娘肚皮里生下的行走动物分为三六九等人,把自由的土地划为三六九等圈,每一等人都有他所不能进去的那一等圈,若进去了就叫“破坏秩序”、“破坏礼仪”、“破坏文明”。我们不就是拥有这般“知识”的“知识分子”吗?
我们若是坚定地站在这个“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就必然会把年轻人看得一无是处。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革宗教,就是要耶稣基督平等地走向平民,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是基督教造就了美国人的平等观念。中国虽然是个世俗国家,但主流意识依然倡导平等观念,关键是我们要用实际行动去打破等级界限。只要社会中的一群人把另一群人当成平等者看待,我们的社会就会多一份友爱与和平。我们应该用实际行动去关心和帮助年轻人,不要把他们往不好的人群里赶,不要轻易、白白地把他们送到“资产阶级”的怀抱里。不要让年轻人感觉去过“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很容易,只要依着本性去做就行,而发扬“无产阶级道德风尚”很艰难,简直难于上青天。如果你的要求太过于违背人性,人们是做不到的,做不到他就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假做,这便是造成人格分裂、造成任何一个世俗中国人都是两个人和社会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
关于道德,我们应该体现在我们做人的行为上去感染年轻人,而不要随便把“堕落”、“颓废”这些词语挂在口头上去刺激和伤害他们。罗先生认为现在中国变坏的年轻人有一个“小国”人口那样多,把他们和美国“颓废”、“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可是美国真正存在过所谓“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吗?为什么美国这个“颓废的一代”、“垮掉的一代”会造就出人类开天辟地的现代信息社会?现任总统布什也是属于当年“垮掉的一代”啊,他是个花花公子,还会吸毒,但是他最终没有“垮掉”。一个没有超人信仰的民族,用德行去评价一个超人信仰根深蒂固的民族,真是有点“乌鸦嘲笑孔雀的丑陋”那样滑稽啊。口头上的道德永远是没有力量的,再说道德也是人类习成的观念,而且是变化的。这么多人喜欢“一夜情”之类,说明那是一种令人醉心和愉快的事情,为什么它不可以像人们“见面握手”一样,成为另一种德行和人的权利呢?只要不是妨碍、伤害他人和犯法的事情,就没有必要给它戴上“堕落”、“颓废”的帽子,并且我们应该尽量给予权利人作为的权利和自由,这样一个文明和谐的人际关系才会产生。
第二,“文化”问题
罗昼先生提到文化问题,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文化精神的感化是教育年轻人最好的办法。但是在这个自由开放和日益国际化的信息社会里,能够感化年轻人的文化必须达到两个标准:一是你这个文化,不要让人越没有文化越抛弃它;二是你这个文化,也不要让人越有文化越抛弃它。坦率地讲,中国目前的主流意识中还没有这种水准和资质的文化。许多国人,知识多了,吸收异样的文化多了,就越来越怀疑和背离自己的文化。十年前我有几个朋友,他(她)们都是大学教授,并且是研究国粹的学者,后来定居美国,就成为基督教徒了。就是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一种文化,能像基督教文化那样,使人越有知识、越有文化就越信仰它。那么拥有知识、文化较少的人呢,更不相信自己的文化,罗昼先生文中所抱怨的那些年轻人,就是一群背离中国主流文化的人。至于成人,绝大多数也不关心和信仰自己的主流文化,除非是出于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用的需要。北京有个研究文化问题的专家,在某地给三百多名公务员和教师侃侃而谈核心价值观,但是认真听讲的却没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在下边或窃窃私语、或接打手机、或讨论喝酒打麻将的事情。这个北京专家所传授的文化,以及罗昼先生所推崇的“优秀文化”,遭到年轻人抛弃,从逻辑上讲是完全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一种不能抵制和挽救“堕落”、“颓废”风气和纠正“年青人的文化观、价值观和崇拜的迷乱”的文化,只能说明它比“堕落”、“颓废”、“迷乱”的文化价值观更没有力量,或者比“堕落”、“颓废”的风气更加堕落、颓废,是一种真正衰败和腐朽的文化。前月拜读价值中国网上汤耀国先生采访方立天教授的文章《人文化解价值危机》,就让我浓浓地嗅到了这种文化无比衰败和腐朽的气息。我不敢相信,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竟是这样一种教导人的水平;但我敢相信,把国内这一类顶级学者全部集中起来,与贩卖法轮邪教的那个教主摆擂台,只以博取信众的多少为成败标准,那么这群顶级学者绝对是那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教主”的手下败将无疑。
前晚和定居美国的好友、原清华大学教师吴丽红女士电话交谈,她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基督教故事:有个犯杀人罪的年轻人被带进法庭受审,突然看见审判官是他的父亲。他不知道他的父亲该如何判决,如果判他无罪则违背法律规则,判有罪则违背慈爱亲情。但是他的父亲是上帝的化身,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和审判难题,他的父亲宣判说:“现在根据法律要判你死刑,但这个死刑由我来承担。”这个案例若是放在一个世俗重视亲情的人治社会里,就会徇私枉法,放在一个世俗法治社会里,则会依法绝情;而在一个基督教的法治社会里,就能做到法律与亲情、公正与慈爱的兼顾统一,前提是上帝教人真正地忏悔自己。在人与人的关系里边,没有一种心态和关系比忏悔自己更符合天意和让人心悦诚服。而忏悔自己,正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罗昼先生有一段话问得非常好:“是我们的教育还不到位,是我们的规则还不到位,是我们的社会还不到位,是我们的心灵还不到位。倘若我们的一切都达到了标准,我们的年青人还会这样吗?”(《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所有这些“不到位”尤其“心灵还不到位”,都是我们不能当好父母、当好法官、当好教育者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父母、法官、教育者缺乏超人信仰,缺乏那个基督徒法官来自神灵和沁入骨髓的人格力量,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多半是一种失败的教育,而我们生养、教育的孩子,也多半是罗先生所指责的那种“年轻人”。
在世俗社会里,法官被认为是公道正义的最后防线。可是我们的不少法官,他下班脱掉制服,可以是酒鬼、赌徒甚至嫖客,没有一点超人信仰的人格力量;因此人们遇到官司都要找关系走后门,而不相信法官法律。在这样的法治文化中,你要我们的年轻人如何不做罗先生所说的那种“年轻人”?当我们的受教育者“离开了中学校园,甩掉了书本”,步入社会看到极不真实的“真实”之后,自然“便渐渐地和中国优秀的文化远了”。缺乏超人信仰的人格力量,正是“有的干脆在中学时期脑子里就丝毫不见中国文化的烙印”的根本原因。至今让我上大学的儿子最能记住“烙印”的中学老师,是一位教英语口语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这位老师有八个孩子,最后一个孩子是捡回来抚养的被中国父母抛弃在路上的瞎眼女孩,十口之家住在一套没有装修的普通房子里,吃饭前要在胸前画十字,说不能浪费上帝赐予的食品。八个孩子去学生食堂买饭,走在路上都是排成一队,年龄最小的走在最前头,年龄最大的走在最后头,到食堂里边也是排队等候,从来不乱规矩。这些孩子离开美国优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被带到贫困的贵州山区,可他们从不怨天尤人,而是规规矩矩、有情有爱地生活,我想这就是有一种超人信仰做了精神支撑的缘故。在一个拥有超人信仰的社会里,即使法律、法官冤枉了他,他也不会去报复社会当真正的坏人,因为神还在保护他;而没有这个全能、全爱、全权的“神”,就更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了。
要“打造”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听取并真心接受的文化,我以为必须透彻地研究四书五经、佛经、圣经、古兰经这些人类文明的最高经典,吸收人类文化的最高成果才能成就。一种文化要让越没有文化的人和越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接受,它必须能够脱离世俗,包含超人信仰的核心价值。而这个,如前所说,就正是目前《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
第三,“真实”问题
我元月28日在罗昼先生《堕落的文化,颓废的崇拜》一文后回帖说:“其实这一代人比较真实。”接着罗先生写了《什么是真实——兼与陈嘉珉先生商榷》一帖。罗先生说:“什么是真实?真实就是跟客观事物相符合。真实的人生就是与人类的总体感情相融洽,与人类的总体行为准则相顺应,而不是违背人类美好的感情和行为准则。”“真实的人生是敢于向问题挑战,是敢于向苦难挑战,是敢于向命运挑战,而决非颓废甚至于反动,决非游戏人生、游戏社会、游戏人性。”
我想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必要“唯心”地把“真实”的定义修改为道德口号上的“希望”或“希望的真实”。我理解世俗年轻人的“真实”,是智性弱化而表现出了更多的本性。世俗人生的内容和意义是折腾,没有信仰、不能沟通与超人力量交流的人,是在超人力量植入体内的自尊、虚荣、忌妒、憎恨、发泄、报复、自私、贪财、贪吃、贪生、怕死、好色、性欲等“折腾液”的作用下身不由己地折腾。我所谓世俗的“真实”,就是上述“折腾液”作用的本色表现。
那么年轻人的真实好不好呢?我认为真实比较好。年轻人表现得比较真实,极少伪装,我们要教化或者对付他们就比较容易。要他们克制欲望、不做错事,办法有两个:一是培育智性,二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植入超人信仰。智性是什么?智性就是知晓功利上的厉害关系而理智处世的人生智慧。例如“我要暴露本性就会吃亏,不能升官、发财等等;因此要检点自己,把本性掩盖起来,合适的时间、场合才发泄一下”,这就叫智性。有了智性,人就会发明和习惯一套世俗人生的折腾技术,这样人就生活在艺术中了,就美了。
至于在年轻人头脑中植入超人信仰,使其言行既有为得体又不失真诚,目前中国还没有达到如此水准和资质的文化,前边说过这正是《中国主体文化的致命缺陷》(愚作)。在一个没有超人力量(造物主)启示的世俗文化中,人们虚伪做作、尔虞我诈、堕落颓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可能罗先生关心的是:要一个什么样的世俗文化,才能挽救这些“堕落”的人群。而我的看法是:一个民族的主体文化,必须含有超人的信仰和敬畏,才能长久克服人的精神危机,从根本上拯救人的灵魂;唯物主义的世俗文化,丝毫不具备拯救精神危机的功能价值。
还有一种真实——网上经常暴露的医患关系、官民关系、师生关系问题,还有和罗先生所说年轻人问题相关的道德滑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真实的吗?未必吧。其一,了解这些问题不能局限于记者采访,而要调查研究。结果调查研究下来,却事有其因,实有非实,并非全真。其二,说现象必须要有统计,不能随便使用“我们”、“你们”、“他们”、“人民”、“群众”这些整体、全体性概念,必须用统计数据来说明个别与普遍现象。你在机关、工厂、医院、学校和社会上,真的看到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现象吗?你要摸着良心来说话,同时必须使用数据来说话。你设想把全国的各省市、自治区都看成没有互联网沟通的单个信息面,那么四川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贵州就是零;打破这个信息单元,把全国作为一个信息面,那么四川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贵州就是一。你把这个二进制关系搞明白了,就可以看到问题性质的真与假。比如台湾目前还是作为一个单独信息面,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面积是台湾的265倍,台湾一年发生一个恶性杀人案件可能没有什么,而大陆一年发生60个恶性杀人案件还得了吗?发生10个都要被媒体吵翻天了。所以真实的真实与信息传播面成反比。
罗先生那样说,而我这样说,说的可能完全是两码事了。那就权当是白说,“对牛弹琴”一曲吧,哈哈。
(2008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