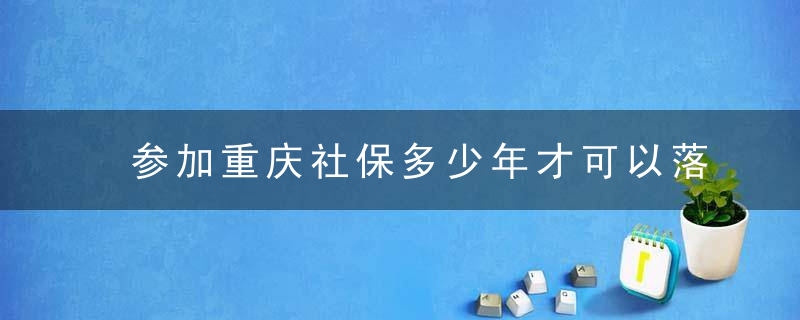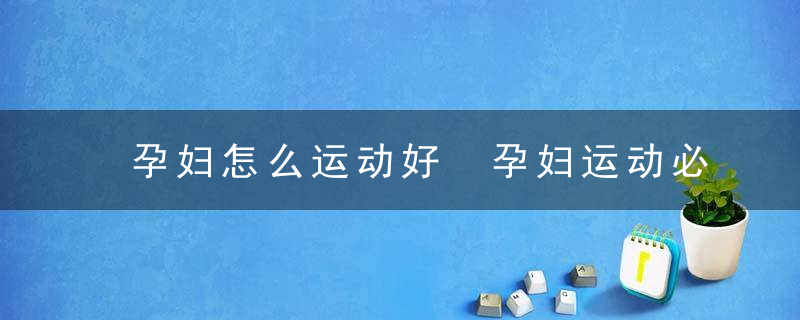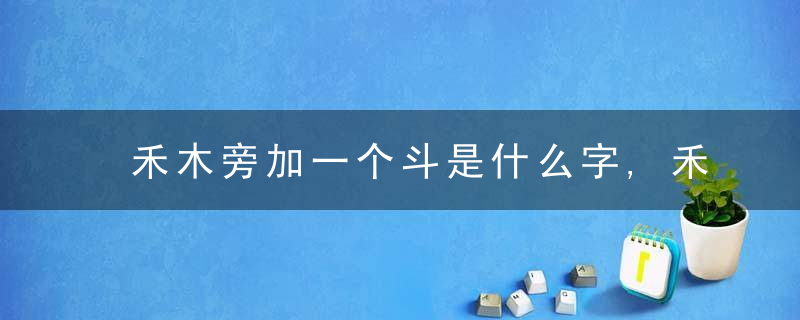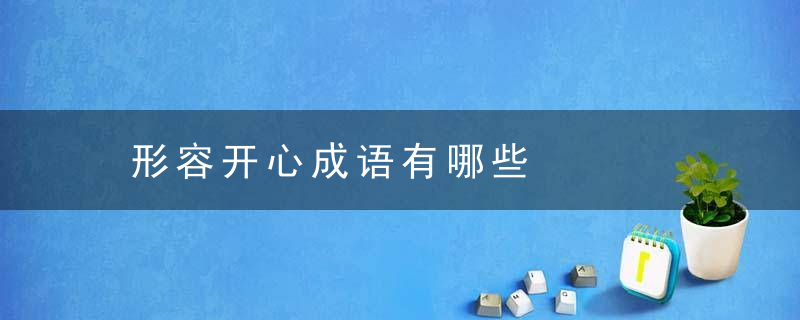回家,为何是至死不渝的信仰

最爱君曾经做过7年记者、采访过6个春运,印象中最深刻的,是有一年在广东惠州火车北站,采访一位老家河南的六十多岁的农民工大叔。
那天,他席地坐在火车站广场上等火车,旁边放着他大包小包的行李;我蹲在地上跟他聊天,那位大叔突然说了一句:
“我老母亲八十多岁了,父母在那里,那里才是我的家。”
那一刻,最爱君突然感觉心里猛地一颤,近十年过去了,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唯独对于他的这句话,最爱君却一直铭刻在心里。
是的,这一生,我们不都是要走在回家的路上么?还有什么,能比父亲母亲和故乡更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讲,关于回家的故事。
纵观历史、人生,回家的路,是如此漫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此后,随着内地的光复和接收工作的展开,重庆朝天门码头,无数因为抗战西迁的人们,汹涌着来到长江边上,渴望踏上那无比欢欣的归乡之路。
此前,大后方的人们并未想到胜利会在突然间到来,所以大后方的民众,仍然在以各种高价囤积着各种物品,然而,突如其来的胜利,使得物价奇迹般地降了下来,而最为紧俏昂贵的商品,变成了:车票、船票和飞机票。
那时候,在经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无数跟随国民西迁的人们,充满了对故乡和新生活的热烈渴望,人们挤破头,托着各种关系,付出比原价高出许多倍的价钱,还不一定能搞来一张薄薄的返乡的票。
面对蜂拥着、急盼着从重庆返乡的人们,以及暴跌的物价,一位从内地西迁到重庆的小商铺老板几乎哭了出来:
“1000万元本钱要保得300万,就费劲得很了。说不定辛苦七八年的结果,怕是一家的路费都筹不出。双手空空,即便能回去,逾海茫茫,如何生计?”
▲1945重庆朝天门码头,无数军民回归故乡的原点。
那时候,历经八年抗战,大后方的民众几乎全部赤贫如洗,尽管如此,无数的人们还是汹涌着,渴望踏上返乡的道路。
著名作家叶圣陶,在他的《东归江行日记》中,记述了他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坐船返乡的情境:
“上午,船仍不开,船主与棹夫议工价,摊钞票若干叠于船头·····结果,每一棹夫得工价二万八千元,到宜昌。十一时后,解缆撑篙,自此与重庆别矣。”
在艰难困苦中压抑了多年的情绪,随着胜利的信息传来,随着返乡的步伐前进,开始热烈奔放出来。
著名演员、作家凤子,也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仍然混乱不堪的上海,尽管百废待兴,然而凤子却难以压抑回到故土的情感,她在《良友》杂志上发文,讲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我像一个同风浪搏斗的舵手,经历了八年岁月的漂流,船身被风雨吹打得已非旧日面目。我顾不及拂去身上的尘土,顾不及换掉破陋的行装,我跑向大街,跑遍每条小巷····”
故乡,尽管饱经沧桑,然而,它却如此紧密地,链接着我们的生命和灵魂。
伴随着胜利的喜悦,从九一八事变后,就辗转内地秘密抗战的东北人齐世英,却感觉到了巨大的痛苦。
他本是辽宁铁岭大地主出身的公子哥,年轻时到德国留学,1931年后,他开始组织流亡到内地的东北人进行秘密抗战;1937年抗战爆发后,齐世英带着自己的两个妹夫石志洪、张酿涛一起到重庆参与抗战,然而,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妹妹,却由于要照顾一大家子人,而被迫滞留在了沦陷区的北平(北京)。
八年抗战中,齐世英的老母亲因病去世,他却因为西迁抗战而无法送终;到达重庆后,他的两位妹夫先后染病去世,为此,尽管知道民族大义为重,然而他心中对两位滞留北平的妹妹,却始终怀着强烈的愧疚感:
“如果不是我带着两位妹夫到了重庆参加抗战,大后方缺医少药,或许他们也不致于死去;是我害苦了两位妹妹,让他们成了寡妇。”
所以,当抗战的喜讯传来,想到在北平去世后一直无法安葬、停灵在寺庙的母亲,和业已沦为寡妇的两位妹妹,齐世英忍不住泪水纵横,不知道回家,该如何面对她们?
▲家破人亡的齐世英,在抗战结束后,开始了痛苦的返乡之旅。
而在晋察冀边区参与抗战的作家孙犁,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终于回到了阔别七年之久的故乡:河北安平。
一年前的1944年,他从家人辗转寄来的家书中获知,他的大儿子不幸夭折,老父亲身体也很不好,他于是赶紧给家里回了封信,没想到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如今抗战胜利,心急如焚的他穿着草鞋,以每日步行百里急行军的速度,爬山涉水十几天急匆匆赶回家,孙犁后来回忆说,他归心似箭,临近故乡时,几乎接近疲惫极限的他,经常感觉自己的身体像是要漂浮起来。
终于,在一个黄昏,他步行到了故乡的小村庄,孙犁后来回忆说:
他走到家门口时,老父亲刚好要去关掩外院的柴门,看见儿子孙犁,他的老父亲呆愣了一会,然后转过身去,忍不住老泪纵横、不停地抹起眼泪;进屋后,妻子抱来孙犁的小儿子,对这位从来没见过父亲的孩子说:“这就是你爹!”
那一刻,孙犁泪流满面。
尽管国破家亡、物是人非,然而这故乡的路,如此沉重,却又让人如此魂牵梦萦。
这一生,我们的心,又何尝不是,一直走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只有家,才是我们:永恒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