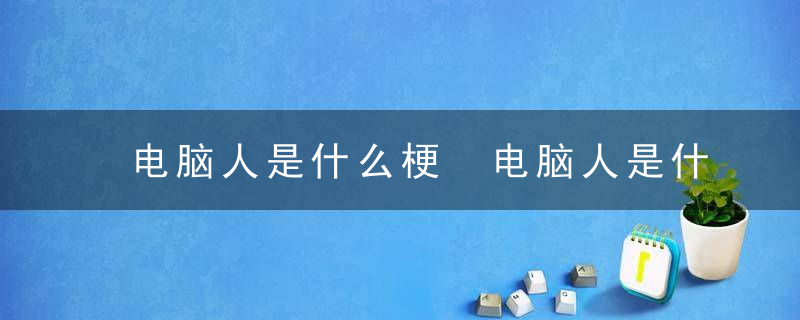吕楠

在吕楠的三个摄影系列中,最打动观众的应该是拍“精神病人”的那个系列。这一系列是吕楠在上世纪90年代初时拍的。
为了拍摄这组图片,他在全国38家精神病院来回穿梭。他说,甚至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也成了精神病人。从摄影史的角度看,可以从吕楠的这一组照片中看到法国马格兰图片社的某些影子。
吕楠表示,正是因为发现了国内外一些摄影家没有走完的路,他才坚定地走了下去。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吕楠花了数年时间,走访了几十家精神病院,面对一万余精神病人,最后才完成了这一堪称中国当代摄影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系列。在这一系列中,吕楠不仅用镜头真实记录了中国的另类群体,那些精神病人令人震惊的特殊生存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整个社会对于农村精神病人的进一步关注。
关于精神病院的照片是最真实的,我们无法想象出这个世界里面的生活,他以最真实的镜头,向我们展示了,并且强调的是 被遗忘的“人”。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的用手护住头,那个病人却相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此后,在吕楠的心目中,再也没有精神病这一概念,在他眼里,精神病人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喜怒哀乐,也有正常人的感情。”-----《南方周末》
王建国,40岁,患病已超过20年。他唯一的依靠是81岁的母亲。 家庭 四川 1990
谢致梅(右)一家四口,妻子(左)及二个孩子都是精神病患者。照片是他死去的儿子,而躺在医院破屋里的女儿谢群英已奄奄一息。 家庭 四川 1990
陶世茂,22岁,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寒假回家首次发病,杀死母亲,打伤父亲(左)。恐惧的家人把他关进石头房。每天为他送饭的是最疼他的85岁的奶奶。 家庭 云南 1990 精神病院 陕西 1990 精神病院 贵州 1990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 家庭 贵州 1990
贾文英,39岁,她的丈夫二个月前去世。现在,她和女儿以乞讨为生。 家庭 贵州 1990
唐明季,45岁,丈夫于九年前去世。家里的门窗已被她取下用于取暧做饭。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家庭 北京 1989
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为室友画画。 精神病院 黑龙江 1989
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
摄影·志:
从1989年开始,吕楠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他恢宏如史诗般的“三部曲”:《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在路上-中国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三个系列作品。这三部作品“仿佛象征了人类今天的精神状况,象征了吕楠期望的人类伟大精神的复归”(栗宪庭语)。 15年,吕楠如苦行僧一般生活、工作和学习,他坚信“好东西是在沉默中完成的”。1989年到1990年,吕楠跨越十多个省市拍摄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以全景方式关注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不仅是医院,吕楠还拍摄了家庭中,以及流浪中的病人。在吕楠的照片中,这些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重新变成多种多样的,活生生的,有着所有人都具备有的喜怒哀乐、爱恋和亲情的正常“人”。
此前,这组照片从未在国内完整的发表过,但它仍然引起巨大反响,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照片经过各种途径流传,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中国摄影师。
附:
观《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有感
刘海锋
无聊之余,看到吕楠的摄影作品三部曲,从《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到《在路上——中国天主教》,最后到《《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所谓的三部曲,作者的本意大约还是在抽象化当代国人的精神现状以及最终救赎。
对我而言,因为对佛教有亲近感,自然疏远“天主教”;由于长期在西藏,“四季”对我自然不会有震撼。所以让我手指长久停在鼠标上忘记点动下一张的还是《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照片中,这些精神病人从被社会妖魔化了的概念形象中复活,脱离了所谓的概念暴力、理论教条和惯性思维,重新还原成多种多样的、活生生的、有着所有人都具备的喜怒哀乐的“人”。
记得最早比较系统的接触精神病,是在成都时翻福柯那本《疯癫与文明》。从他写中世纪如何将麻风病人关起来探讨15世纪愚人船的思想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再到他探讨疯颠是如何被看做一种女人引起的病,再到疯颠被看做是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潮,疯癫被看做是一种精神病。福柯的文字带来的抽象思维快感,自然不必赘述。当初一直困惑我的是,为什么“疯癫”的成型史最终是在“文明”的演化史下大张旗鼓的?这一过程中,社会最微观的个体本身的处境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这无非就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以我的观点看,在哲学层面的抽象主要就体现为世俗化、理性化、自由化的特征。人的最终的价值追求就是自由,为了自由,“人”必须从“神”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在社会形态层面就是世俗化,在人的精神层面就是理性化,只有这样,现代性的追求才能完整的实现。但同时,由于促进“现代性”到来的动力是市场经济下资本主导一切的逻辑,这天然又是一个使整个社会不断分化,人与人之间不断异化的过程,为了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动态中寻在静态,在陌生中寻找熟悉,由此逼着作为“现代性”核心的“理性”必须进行裂变,抽空了“理性”中不确定的、动态的、陌生的“价值”和“意义”,使得原本该是人们不断充实提高并发展的过程,脱变成了一部“实质合理性”臣服于“工具合理性”的历史,最终使得微观的个体对“自由”追求的目的流产为“意义的丧失”和“自由的丧失”悖论。而社会思潮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治理模式的演化,或者说治理模式在新的社会形态下需要新的思潮更新。至于它们到底谁拉扯谁,谁利用谁,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关心的是更新之后社会个体的现状和救赎。
从主流的社会价值来看,所谓的主流,永远都是宏伟壮观,理直气壮,道貌岸然,一种隆重而安全的形式感和包围感,除此无它。但如果深入到内层,关乎到个体,就必然会涉及自身与所处世界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反叛、情爱、性、阴暗、私密、边缘,以及死亡;呈现出一种完全截然相反的自我存在,或困顿、挣扎、多面、脆弱、暴力;或唯美、真实、充盈、尊严、安详。
这样一来,就必然与所谓的“理性”主流众叛亲离,就必然越过社会价值观、是非观、道德伦理、常规秩序,在尖锐边缘挣扎、呐喊、困顿。同时,快速行进的时代,挟带亢奋和焦躁,如同浪潮席卷一切,吞噬一起,消散一切。这个时候,个人的坚持和游离,必然成为社会的“精神污染”,拒绝跟随集体意志和意愿的人,必然会被孤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遭到“工具理性”包装起来的暴力机器对你进行温水煮青蛙式的隔离、改造、甚至监禁,迫害,抑或让你在剥离了一切“现代性”的时空里生不如死。
这个时候,值得反思的就是“现代性”本身了。“现代性”从启蒙开始,自然会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的“洞穴寓言”。按照西方理解,启蒙就是走出蒙昧的洞穴,直面真实的世界,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用“人”取代“神”,构建“理性”的现代社会,体现在制度架构上,就是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呈现在实质内层上,就是不断的对外扩张和资源占有。但由于“现代性”内部自身无法克服的悖论,走出“洞穴”后的人们发现,政客与学者的联盟只不过将自己从一个“自然的洞穴”带入了另一个“人造的洞穴”,自以为看到了阳光,其实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刺眼的日光灯。而且这个“人造的洞穴”比以前那个“自然洞穴”可能更加危险,因为在科学和技术武装下的统治者,在市场分化逻辑下,形成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人们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同时,更在原子化和碎片化,面对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机器,社会的底层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苍白和无力,更难受的是,以往处于“鸿蒙”状态下的人们意识不到这点,而经过“启蒙”浇灌后的人虽然能深刻体会到这些,但是却只能眼睁睁的直面梦想的破灭,无处下手、无法挽回、无能为力。
在这种主流下,时代的表现就是剧烈、势力、冲动、炙热。快马加鞭,横冲直闯。它不是无聊,而是贫乏。这种贫乏,不是缺失物质和科技,而是与富足和强势的对照关系相互映衬,让人麻木不仁的活着而已。贫乏,最后成了一种信仰的缺失,在内心缺少公正有力的支持,得以支撑人公正有力、充盈丰沛的诗意化生活。
在这种主流下,更多的是假话、空话、大话、复制跟风流行话,以及讥讽、戏谑、掩盖,或者言不由衷、粗鲁侮辱、暴力干涉。在这种抽空价值、感性、品质的“工具理性”裹挟下,我们被“话语”和“工具”的媾和随意的捉弄、游戏、摆布、欺哄,人渐渐失去自主行动的意志和自由。最终只能在市场的分化下,自以为满足的跟风去贴标签和搞斗争。一边高声谩骂着,一边悄然涉足着。要想结束这种人格分裂,你必须先深入并玩弄这种分裂,让更多人参与其中,当你的炮灰。即使我们保持镇定,冷淡自处,但在内心无可否认,这辈子经历了这么多,怎么什么都回忆不起?是不能回忆,还是不愿回忆?终其一生,不过是充满浮生若梦的感慨,抑或人生如戏的回叹。
在这种主流下,宗教、诗歌、山水、理想,这些原本可以提供不同形式的信仰给人们,让人们知性的、恬淡的、丰富的、谦逊的、有所敬畏的走完一生光景的载体,在强时代的意识形态塑造过程中,被拆解了,被操纵了,被解构了,个体的观念、质量、取向、模式随之被组装、改造、整合,事物背后真正的力量被低估、质疑、扭曲、抛弃……
怎么救赎?我没有答案!现在我只能说,很多时候,我们对时代的态度,本质是对生的感悟,它更多的来自于我们如何直面所谓的“精神疾病”,直面自身的死亡。穿透了这个内核,人基本上不会再关心任何幻化出来的,生的各种形式和妄想。人的生命若无超越的机会,最终就是一种无解。到最后,渐渐什么都说不出来。不想说。说不明白。说不究竟。没有结果。没有审定。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只能朝向自己的终点,趋近它。或者说,即使是死亡,也无法停止我们需找最终超越并救赎的机会。这就是一种抵达。
我能做的,也就是在抵达的过程中,尽量增加生命的密度和质感,充分感受并温熙饱满的去践行当下每一刻,做一个走过很多路途但又处变不惊的人,眼神有机警和敏锐,更有朴质和淡然。手里持有的,眼里盛荣的,心里充盈的,只属于当下如游丝一抹笃定而确实的存在感,为欢乐而存在,为丰足为存在,为生命本身而存在。此刻,舍去浮世,明月清风,遗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