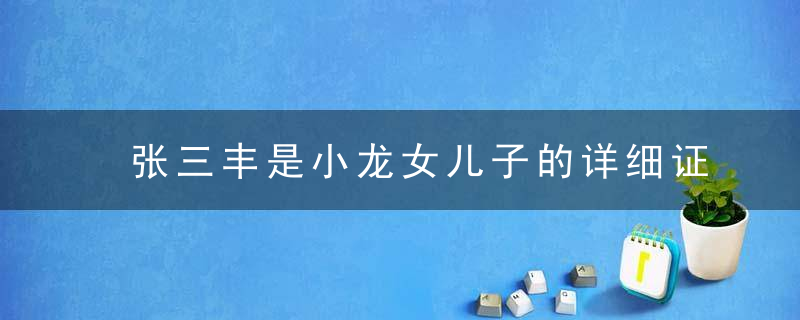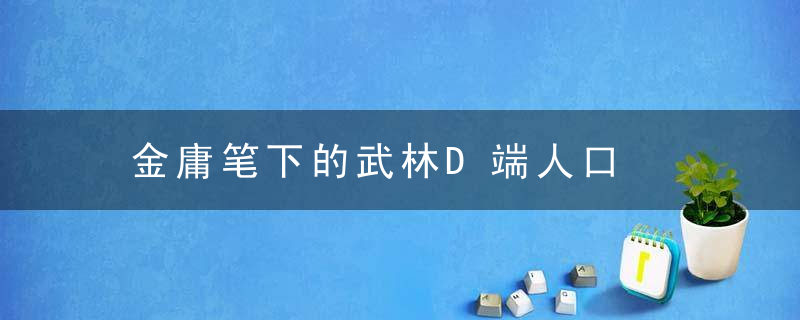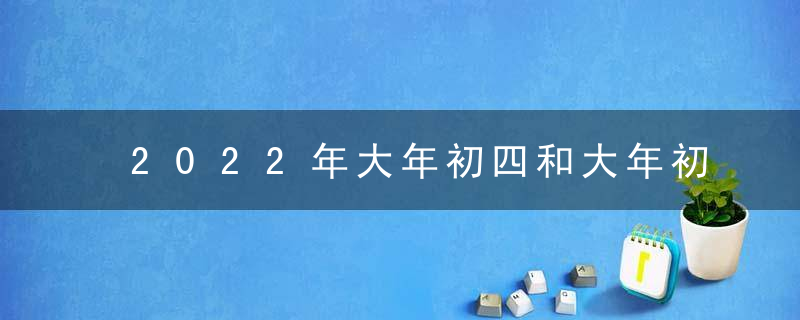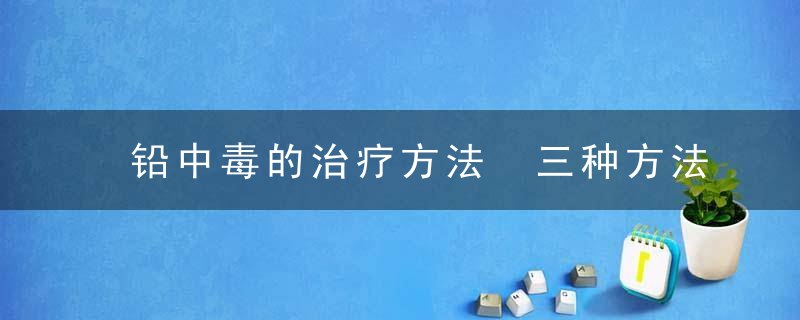“君”,金庸笔下一个最美好的称呼

文/六神磊磊
一
天涯思君不可忘。
杨过对于郭襄,是“君”。
君这个字,可以说是金庸小说里,女孩子对男士的最美好、也最意味深长的称呼。
不是“卿”,也不是“郎”。郭襄不是“天涯思卿不可忘”,也不是“天涯思郎不可忘”。那样的话,显得太腻歪、太熟稔了,都不准确。
“郎”是小龙女叫的:“小龙女书嘱夫君杨郎,珍重万千,务求相聚。”郭襄和杨过远不到那个地步。
他们连手都只牵过一次,郭襄主动的,杨过还找机会一指远方“你看那里……”,把手抽脱了。
相比之下,“君”没有那么亲昵,显得更堂皇敞亮一些,关系没有那么亲近。
把心上人称为“君”的时候,是隔着一层距离的,是退后了几步的,带着一点拘谨、一点不那么熟悉的味道。
甚至,带着一点无法亲近的苦涩。
二
“君”字,还隐含有一层评价和欣赏的意思。
金庸的笔下,女孩子称对方为“君”,总包含着一层对伊人气质风采的褒奖。在她们眼里,那个人多半人品出众、风姿不俗。
任盈盈初次相识令狐冲,隔着帘子叫他“令狐少君”。
这是含有褒贬之意的——不但是“君”,而且是“少君”;不但一表人材、风姿佳伟,而且还很潇洒年轻。
任盈盈明显是心动了,有一种李清照说的“暖日晴风初破冻”的味道。
如果改称“令狐少侠”,那就读不出有这个味道了。
程英对杨过也是这样。
当时,杨过大战金轮法王,重伤昏迷。程英把他抢回茅屋,裹好了伤,精心收拾停当,自己的心却乱了。
她背着杨过,坐在窗边,在纸上反反复复写着《诗经》里的八个字: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既然见到了这男子,怎么我还会不快活?
这里用的是“君子”,而不是“伊人”。伊人对应的只有单纯的思念,“君子”里还有褒奖、欣赏和爱慕。
可之前说了,“君”这个字眼,又是略带隔膜的,是不熟悉的。
任盈盈和令狐冲,程英和杨过,当时都不熟悉。两人单独相对的时候,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尴尬。
程英的一句“既见君子”,更还画出了见之心喜,却又求而不得,只能叹息远观的心情。
三
同样地,赵敏也曾经给张无忌写过一张手条,称他叫“君”。
那时也是认识不久,姑娘已经有意思了,男的却还懵懂无觉。赵敏提笔写的是:
“金盒夹层,灵膏久藏;珠花中空,内有药方。二物早呈君之左右,何劳忧之深也?”
你看这又是一个含义深长的“君”:
欣赏,乃至爱慕,但还不很熟悉;保持着距离感,但又希望有所突破;带着一点调侃,又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试探。
如果说,对于郭襄和程英,是一种无法亲近的苦涩,那么对于赵敏,则是一种殷殷期待、对美好事物即将发生的憧憬。
也正为此,梦姑寻找梦郎,那一章的回目词就叫“酒罢问君三语”。
忐忑不安,小心翼翼,但又期待美好即将发生。
四
除了这些之外,“君”还有另一个用法。
正因为它的隔膜感、它天然的距离感,“君”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个决绝、疏离、沉重的字眼。
比如甘宝宝写给段正淳的信:
“伤心苦候,万念俱灰。然是儿不能无父,十六年前朝思暮盼,只待君来。”
可是盼又盼不到,终于“迫不得已,于乙卯年六月归于钟氏。”
意思很明白,我始终等不到你,钟灵不能没有父亲,只好嫁了。这一个“君”字,包含着千言万语。
从这一个字里,你能品出爱与恨交织,写信的人以漠然之笔触,写当年惊心动魄、柔肠寸断事,在这一不失尊重的称谓中,蕴含着一种划清界限的决绝。
如果改成“只盼郎来”、“只盼尔来”,都会丢失掉一大半的信息,甘宝宝的那种又爱慕又持重、又怨艾又决绝的感觉就失去了。
五
不要以为只有男女之间才能“君”来“君”去。
金庸的笔下,还有一个基情满满的“君”。那是大蒙古国师金轮法王写给大侠郭靖的:
古人言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悠悠我心,思君良深。
这是挑衅,是战书,但又假中带真,惺惺相惜。
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分裂的法王:一方面,既生我,何必又生你?另一方面,幸好这世上还有你。没了你的亢龙有悔,老衲到哪里去找一个人来对掌。
猛一看是:准备受死;仔细一品是:我想靖靖。
这就是金庸的笔力,也是中国文字的魅力。简简单单一个字里面,居然有这么多奥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