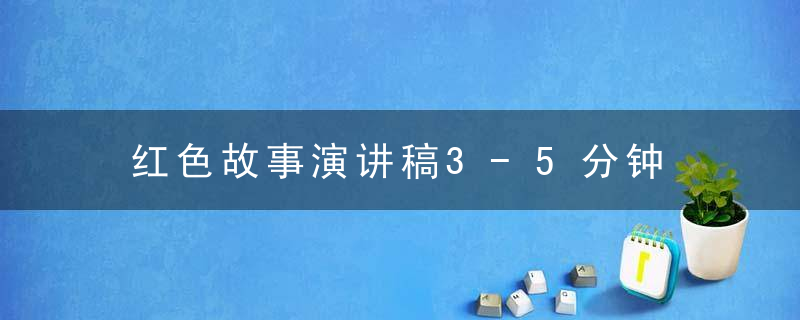鲁迅《一件小事》的哲学阐释思路

与《呐喊》中的其它作品相比,首次发表于1919年12月的《一件小事》是一篇同样影响深远却又十分独特的小说。《一件小事》的深刻内涵并未寄寓在情节的跌宕起伏及人物关系的幽微变化之中,而是以颇具自传性的“我”记忆中的一个单独事件为导引,显现出围绕事件、自我、怀疑等主题建构的知识分子心路,并与鲁迅的心灵史和生活史形成应答。单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看,《一件小事》并不是当代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围绕其文学史价值、社会文化内涵、叙事策略和文化转译等议题,研究者从未停止论述和探讨。[1]更由于《一件小事》长期位列中小学语文教材及读本的重点篇目,并反复被大学现代文学史教材提及,其社会接受效应的广度和深度自不待言。[2]现有研究成果论及《一件小事》中的事件时,或以事件始末解读知识分子的认同转变,或注重由修辞层面获取小说创作技法,或关注叙述人“我”与鲁迅的辩证关系并解读其自传意味,分别呈现了各自的理论视角和创造力。本文的意图是由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有关“事件”的哲学论述谈起,尝试对《一件小事》进行哲学层面的阐释,以期待为大学文学史课程中知名作品的解释环节提供一种可能的参照。
一、事件与“我” 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事件(event)则通常“指一种产生或发生(happeningor occurring),这种产生或发生并不固守与某物的关联性,而只发生于某一特定的时间间隙中的某处。”[3]而巴迪欧阐述的事件概念构成了巴迪欧意义上的真理概念及主体概念的基础,不仅推动了对哲学本体问题的再阐释,也启发了有关人之存在的思考。巴迪欧认为:“为了开启真理进程,必须要发生一些事。目前已有的——知识的情境——不能生产任何东西,除了重复。对于真理,要确认其新奇,必须有所补充。它无法预料、不能计算。它超越了自身。我称其为事件。在它的新奇中,真理显现了,因为事件的补充打破了这种重复。”[4]也就是说,巴迪欧所谓的事件并非指代所有发生的事情,而是那些打破重复、超越自身并显现真理的事情。巴迪欧认为事件代表了非连续性和断裂,它打破了任何可想象的当下并且与过去相割裂。[5]它敞开了主体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事件的发生成为了存在得以在世呈现的良机,‘存在’也因而转化成‘作为事件的存在’。”[6]在如上思路的引导下,《一件小事》的文本可以视作对某一影响深远却难以归类的偶发事件的叙述,其中他人的行动与“我”既有的观念模式之间的断裂性推动了个体的自我更新。 从逻辑和文体意义上来看,这篇小说中的“我”虽并非作者鲁迅本人,但其作为鲁迅的“精神自传”,烛照出“我”与作者相重合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7]于是,将鲁迅文集中自述性的文字与《一件小事》之类具有自传特征的小说文本相对比,以此阐释小说的意义,就成为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方式。“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迹,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老实说,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8]这句小说原文时常被评论者与另一段《〈自选集〉自述》的文字相互参照:“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9]这两段时常被用来对照的文字中,都提到了“事件”:前者指代辛亥革命之后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们中的大部分令“我”失望和厌恶;后者则侧重指鲁迅有限的个人经验世界中的个别事件,鲁迅对它们的有限性表达了态度。这两段关于“事件”的表述,可以共同导引出如下的叙事线索和作者心态:首先,辛亥革命后一再重复的政治闹剧(尤其是复辟帝制)显现出内在意义的缺乏,此类政治“事件”在本文看来并不是巴迪欧意义上的事件,而是主要提供了关于现实的“知识”;其次,失望和颓唐是自我(无论当时的鲁迅,还是《一件小事》中的“我”)对历史及社会变迁的情感应对策略,它是个体的自我保护本能在心态上的显现,与针对他人的怀疑相共生,并导致了一种“有意的”遗忘;再次,针对他人的怀疑有可能与自我怀疑相交织,它使得“多疑”不仅作为作家性格层面上的征候始终存在,而且能够转化为文学写作的心理推动力[10];最后,那些“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政治“事件”推动了鲁迅的心态变化,但他在自我怀疑中又察觉到自身经历的人物与知识的有限性,“提笔”(写作)成为了应对那些令他失望的政治“事件”的“文学事件”。这些内容构成了理解《一件小事》及其承载的心理变化的背景。 与小说中的偶发事件相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历史“事件”在重复中一再显现出进步与倒退、共和与复辟、革新与守旧之间的纠结和缠绕,无论在社会现实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均形成了具有一定荒诞性的面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写下有关重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著名论述:“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11]对于小说中的“我”这类原本对社会革新抱有一定期待的人而言,表面上宏大实则滑稽的“笑剧”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一再出现令人失望乃至暴躁,这便是“我”的“坏脾气”。与之相比,小说里着重书写的那件小事却是较缺乏戏剧性的,它是一个并不包含跌宕起伏的戏剧性情节转折却又对个体发生深远影响的事件。它不包含“好人遭遇厄运”的古典悲剧式突转,相反,“突转”发生在作为旁观者的“我”的精神世界里——由于车夫对偶发事件的应对超出了我的经验和惯常选择,因此才引起了人生的新“发现”——巴迪欧意义上的断裂。它发生在“我”人生中途的迷茫之际,发生在居所至S门的路上,处于一个无人旁观和见证的偶然时刻。小说以车夫及老女人的动作和身体姿态勾勒出事件的经过,再围绕责任、语言、判断等问题具体展开不同行动/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向“我”启示了人生的可能性。齐泽克曾评价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观点说:“……在巴迪欧看来,事件是一种被转化为必然性的偶然性(偶然的相遇或发生),也就是说,事件产生出一种普遍原则,这种原则呼唤着对于新秩序的忠诚与努力。”[12]以此观之,小说中的“一件小事”对“我”而言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启示,而写作《一件小事》对于鲁迅而言则是一种确认希望的尝试与过程。[13] 二、事件中的“技术” 小说从“我”的“越来越看不起人”写到对他人价值的再理解,勾勒出一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他超越了自身有关历史和人生的知识,走在通往人生领域的“真理”的道路上。按照巴迪欧的论述,真理并不是那些普遍通用于各种情境、场合,并与科学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认识”。“一个真理包含下面的悖论:它既是新事物,因此也是罕见和例外的,然而,仅就它是真理的存在而言,它也是最稳定的,从本体论上说,最接近于事物的初始状态。”[14]他区分了真理和知识:“真理是难以觉察的,它不会落到百科全书的任何限定词下。它在知识里打洞。”[15]由于“一件小事”中车夫的举动在“我”看来既罕见又出乎意料,超出了“我”对他人以及人性原本的认知,洞穿并动摇了“我”当时自以为完备且透彻的人生知识,因此也参与重组了“如今的我”对自我与人生的叙述。同样,“如今的我”因对一件小事的不断回忆而获得的勇气和希望既是“崭新的”勇气和希望,也可以看成是他曾经对社会革新抱有的那种原初希望的延续。 如果说“知识”是巴迪欧意义上的真理致力于超越的对象,那么自我技术就是人通向真理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米歇尔·福柯曾将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并推动了人们的自我认知的技术划分为四种形式,包括生产技术、符号系统技术、支配技术和自我技术。生产技术“使我们能够生产、转换或操控事物”,符号系统技术“使我们能够运用符号、意义、象征物,或者意指活动”,支配技术“决定个体的行为,并使他们屈从于某种特定的目的或支配权”,自我技术“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16]《一件小事》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生产技术,被“我”所淡忘的“子曰诗云”可以归入符号系统技术,令他增长坏脾气的“文治武力”,则同时包含了符号系统技术和支配技术。与此相比,“我”的自我质疑和自我解剖,则可纳入“自我技术”的框架。小说中“我”的自我质疑带有浓厚的鲁迅自指意味,这也令《一件小事》成为兼具美学价值和作家传记价值的文本。小说不仅借助“我”的心理描写呈现了鲁迅式的针对他人的怀疑,还呈现了一位怀疑者对自身尤其是其悲观态度的“自反式”怀疑。怀疑某种程度上既是个体意志力存在的证明,也代表了个体意志在选择上的无能或无力。它既是“我”之个体意识的显现,又代表着个体意识本身的动摇,对应了一种人生过渡时期的心灵状态。 作为“我”的精神转变发生的必要条件的“他人”,并非仅指车夫,而且理应包括那位可疑的老女人。如果一件小事是小说描述的一次世俗生活试炼,“当时的我”精神世界中设想的“讹诈”或“骗局”就是一种怀疑他人的心态的集中显现,这与“越来越看不起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叙述人声音背后的鲁迅的多疑心态,也借助“讹诈”事件得以显现。关于《一件小事》的现有研究成果中,已有一些研究者提到老女人有可能是一名因生计所迫而实施讹诈的人,但多数论著并未就这个问题展开进一步的分析。为了勘探小说文本意义的丰富性,这一可能性也有加以推演的必要。周作人曾回忆《一件小事》的创作背景说:“在当时这类事情的确常有,特别是老太婆,这样的来寻事讹钱,这是过去社会遗迹,后来也渐渐少有了。”[17]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我”的怀疑未必是毫无凭据的想象,而是旧北京现实生活经验所推动的判断,他最初的思维过程也表现为经验世界的的延展。“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这种判断既是一种自我防御性的标志,也是个人经验形成的“认知模式”的表达。利用受伤的假象进行欺诈,是一种社会领域中的恶行,它的关键之点是利用了他人的善意或畏惧心理以谋取私人利益。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讹诈的实施者必然会动用一套以“审时度势”和“控制自我身体”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小说中并未明言但却极有可能存在的这种讹诈“套路”,恰与“我”所鄙视的政治事件所包含的权力或话语运作套路具有相似性。它们都包含了表演性、反复操演和重复的套路特征,以及身体的控制技术。小说中“我”所看到的老女人的动作——“从马路上横截过来”和“慢慢倒地”都可能是这种讹诈活动的环节。“我”判断老女人在“装腔作势”,是在对他人的怀疑中表达了一种固执存在的对“他人之恶”的态度。在此,想象中的“恶行”成为了一种具有过渡性的叙事因素。 小说中的这起“交通事故”,其实没有造成真正的纠纷。从情节来看,小说并未明言车夫在没有路人见证的情况下自愿承担了这一事件的全部责任,只是讲他没有对那个在“我”看来有讹诈嫌疑的女人置之不理,而是主动搀扶她一起去巡警分驻所谋求裁断。“搀扶”是车夫协助老女人走路的方式,显露了车夫对老女人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而非怀疑)。本文认为,在“我”的理解中,这种毫不犹豫地谋求裁断的自觉和直面事件本身的态度,是他人对“我”的一种人生提示。[18]对于“我”而言,“纠纷”不仅存在于他偶遇的事件之中,也存在于他的心理世界之内。瓦尔特·比梅尔认为,人在文学中表达了其“世界关联”,其中涵盖了“人对其同类的理解”、“人对自身的理解”和“人对非人的存在者和超越人的神性之物的理解”。[19]《一件小事》中的怀疑可视作个人用以理解同类和自身的一种充满动摇和矛盾性的手段。作为理解的怀疑,最终的旨归是人与他人的共存,《一件小事》将这个重大的人生主题纳入了偶发的生活事件。“风全住了,路上还很静。我一路走着,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搁起,这一大把铜元又是什么意思,奖他么?我还能裁判车夫么?我不能回答自己。”这句话不仅提及怀疑的对象由他人转为了自我,而且以“自身无法回应这种自我质疑”的状态使思考得以延续。一大把铜元是社会意义上的“礼物”,它并不等同于作为黄包车雇主的“我”需要支付的车费,而可视作一种“回馈”,因为车夫的行为对于“我”而言不啻为一份伦理的馈赠。馈赠的实施既是由于车夫的行为对“我”的伦理感召力,也源于“我”内心潜在的伦理之善。[20]“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车夫的背影虽不能说直接代表了鲁迅所关注和尊重的劳工阶层,但确实是一个指涉着他人的象征物,同时代表了一种原有的知识的“反转”。在这个意义上,《一件小事》借助“怀疑的技术”推动了一个知识分子围绕一个事件,从外部认识转向自我认识的过程。[21] 三、事件的记忆 “但有一件小事,却于我有意义,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使我至今忘记不得。”个体挥之不去的记忆保留着这件偶发事件,同时也将其意义与历史“事件”相对照,并诉诸于从“当时的我”到“如今的我”的人生意义创造。“事件与意义的关系应该是交互的:事件使意义有一个现实的、存在的基础,意义使事件拥有结构,具有可理解性,于是‘文本’成为了可理解的、开放的,为不同的解释留下空间。”[22]从“记忆”这个叙事及文化主题来看,《一件小事》以另一种方式重复了《呐喊〈自序〉》的主旨,构成了作家写作缘由和动因的注脚。狄尔泰曾这样描述历史研究者针对历史事件的书写策略:“只有通过某种不是再现特定的事件,而是再现这个事件所具有的各种联系系统和发展阶段的记忆,对各种事件的过程进行重构,人们才有可能理解历史上的生活。”[23]但《一件小事》的小说书写策略恰好相反,它并未记录鲁迅能够把握到的20世纪初的“当代史”重大事件。“我”铭记在心的偶发事件及其理解,超越了那些重大历史“事件”,获得了源自个体记忆的特殊价值。也正凭借作家的书写和作品的传播,事件之于个体的价值得到了提示,因而有机会成为公共生活的议题——讨论的主题不但包括知识分子或劳工问题,还应当包括“老女人”式的边缘个体及其生活策略。巴迪欧认为:“我们说事件在本体上是集体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其为潜在地召唤出群体提供了媒介。”[24]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件小事》乃至小说集《呐喊》的书写,都不是单纯的文学事件,它们借助印刷媒介的传播成为了小说家参与社会、历史乃至政治进程的特殊方式——作家的社会行动。 小说中的“我”通过铭记车夫的背影而肯定了他人的价值,也则通过赋予事件一个名称(“一件小事”)而留住了关于它的记忆,使它不至于彻底消逝。“一件小事”是小说中叙述人赋予事件的名字,小说的标题《一件小事》则是鲁迅本人赋予小说的名字。巴迪欧认为:“主体并不先于事件存在,这是因为正是借助命名并抓住了事件的残渣,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主体。”[25]“我”因此进入了致力于自我建构(“立人”)的“我”——一个自我更新中的社会个体。“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熬了苦痛”代表与一件小事相关的记忆时常引发回忆和自省,这个过程如同实施“自我技术”并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一样混合着痛苦和不安,是一次又一次直面真实人生和自我裁断的残酷过程。 在这件被“我”铭刻于心的小事的内与外,个体记忆被具体化为不同的形态。齐泽克曾在论述事件的多样性时,将人审视世界的认知框架划分为四个方面:已知的已知(Known Knowns)、已知的未知(Knownunknowns)、未知的未知(unknown unknowns)和未知的已知(unknown knowns)。它们分别对应了“我们知道自己已经知晓的东西”、“我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那些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和“我们不知道自己已然知晓的东西”。[26]《一件小事》的文本中,“已知的已知”提示了“我”对那些表面上宏大实则充满陈旧套路的国家大事的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当时存在的一种实施讹诈的套路的认识。“已知的未知”则约略指代“一件小事”发生之前,“我”对于人生和社会之希望所在的迷惘——由于“我”看不到更多的希望,因而身陷“越来越看不起人”和“坏脾气”的漩涡。而处于自我怀疑状态之中的“我”,则能把握另一种“已知的未知”——围绕“一大把铜元”的自我反思及其导致的“我不能回答自己”的状态即可归入此类。齐泽克所说的“未知的已知”是涉及潜意识的一个方面,代表潜伏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的隐秘情结,在《一件小事》里可以概括“我”心灵深处对他人(尤其是劳工阶层民众)的理解与同情,但这些倾向性出于自我对历史、政治变革和他人的防御性而被隐藏起来了。“未知的未知”则能够标明“我”与作者鲁迅之间的一个差异之处,它代表着小说中不被“我”觉察的未知之物,也就是“我”一直忽视但却围绕“一件小事”得以彰显的东西——他人的实践,以及他人的日常生活选择所蕴含的真知灼见。这是区分小说中的“我”与小说的作者鲁迅的一个关键之点。鲁迅创作道路上为人生问题进行的思考,本身即意味着洞悉和开掘那些表面上不属己的事物与事件。正如汪晖所说,“鲁迅那种把一切与己无关的、客观的世界看做是和自己有着内在联系的事物的独特的艺术才能和叙事方式是他的最有力和深沉之处。”[27]他无处不在的怀疑精神解剖了他密切关注的,维系着自我与他人、历史与现实、已知与未知的社会关系及心理关系。而小说并未表明“我”知晓了这些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一件小事》映射着鲁迅反思自身与他人,自身与历史之关系的思考,并成为这些思考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一次铭刻。 注释: [1]截止至2016年底,中国知网上以《一件小事》为标题词的国内学术论文共有68篇,其中《名作欣赏》杂志总计刊载10篇。最早一篇发表于1986年,最近一篇发表于2015年。 [2]论及《一件小事》的文学史著述,如北京大学等九院校《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一件小事》“像小品散文”。(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孙中田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一件小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把人力车工人作为正面主人公加以歌颂的作品。”(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203页。)陈安湖、黄曼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在《一件小事》中,鲁迅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了城市人力车夫,写出了他们深厚的阶级友爱,鲜明的是非观念和朴实、婚后、坚韧的性格;并且从对比中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私和对劳动人民的冷漠情绪。小说中的‘我’并不就是鲁迅,但也确是表现了鲁迅严于解剖自己,以劳动人民为榜样改造自己的精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页。)黄曼君、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称《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世俗眼光中的渺小者的灵魂同样可以高大”。(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 [3]刘欣《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载《外国文学》2016年第2期。 [4] Alain Badiou:Infinite Thought,translatedand ed by Oliver Feltham and Justin Clemens, London New York:Continuum,2004,p.62. 转引自艾士薇《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5]转引自[加拿大]布鲁诺·莱萨德《“末日降临!”:希区柯克〈群鸟〉中事件与身体的悖论》,张也奇译,载《电影艺术》2013年第1期。作为与巴迪欧的事件观有别的观点,吉尔·德勒兹认为:事件是从一个状态向另一状态的过渡,它代表了连续性和突现,是源于生成之突现的连续形式。 [6]高宣扬《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7]汪晖认为,《一件小事》的叙述人与作者“相对同一”。引自汪晖《反抗绝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45页。 [8]本文中《一件小事》的原文均引自《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1-483页。 [9]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0]有关鲁迅“多疑”主题的研究,可参见刘春勇《多疑鲁迅——鲁迅世界中主题生成困境之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一卷),北京: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1页。 [1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高宣扬也总结巴迪欧的观点说:“事件作为事件,其关键属性,就是它的突发性显现,甚至就是它突然显现的那一瞬间,……它是以其突发性显现作为其存在的依据,一起毫无理由地贸然显现而确定其独特身份,也以此显示其无可征服的威力,展现其时空方面的唯一性。”参见高宣扬《论巴迪欧的“事件哲学”》,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13]现有研究成果中,有研究者认为《一件小事》的主要情节直接来自鲁迅的亲身经历。这些论述经常引用的文献是:《〈一件小事〉真有其事》,载《语文战线》1982年第9期。 [14] [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收入陈永国主编《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1页。 [15]转引自艾士薇《阿兰·巴迪欧的“非美学”思想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16] [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编《福柯文集》(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54页。 [17]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0页。 [18]刘学军《不可误读鲁迅的〈一件小事〉》,《名作欣赏》2015年第33期。作者认为车夫自觉的选择代表了深入骨髓的精神奴役创伤。 [19] [德]瓦尔特·比梅尔《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72页。 [20]此类来自他人的伦理馈赠同样出现在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之中,父亲作为“他人”的价值是由“我”对其背影的注视和铭刻而获得承认的,《一件小事》也是如此。参见张一玮、党文亭《父亲的脸:关于〈背影〉的哲学解读》,载《名作欣赏》2016年第7期。《背影》可与《一件小事》相参照的原文段落为:“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 [21]汪晖论及鲁迅小说中主题精神历史的客观呈现这一问题时,曾将其创作的第一人称小说分为三类。其中第二类作品是“通过第一人称在叙述非己的故事时,对自我与叙事对象的关系进行反省,从而将主体的精神历程在故事的客观叙述中呈现出来——实际上,这种叙事模式本身便是鲁迅独特的思维方法和人生哲学的体现:客观的现实对于‘我’而言不是外在的、与己无关的东西;不是可以漠然对待、不以为意的东西,因为,只要‘我’失去自身与现实的相关性的认识,‘我’也就失去了自身力图独立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的可能性,从而成为造成悲剧的现实秩序中的一个角色,成为旧世界的‘同谋’。这类小说包括《孔乙己》、《故乡》、《祝福》,在一定意义上还包括《一件小事》。”引自汪晖《反抗绝望》,第327-328页。 [22]刘欣《西方文论关键词:事件》。 [23] [德]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24] [法]阿兰·巴迪欧《元政治学概述》,蓝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8页。 [25] [法]巴迪欧《主体理论》,转引自蓝江《回归柏拉图:事件、主体和真理——阿兰·巴迪欧哲学简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6]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0-12页。齐泽克是在分析拉斯姆菲尔德有关伊拉克问题的讲话时提出“未知的已知”的,前三个方面均源出拉斯姆菲尔德的讲话。 [27]汪晖《反抗绝望》,第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