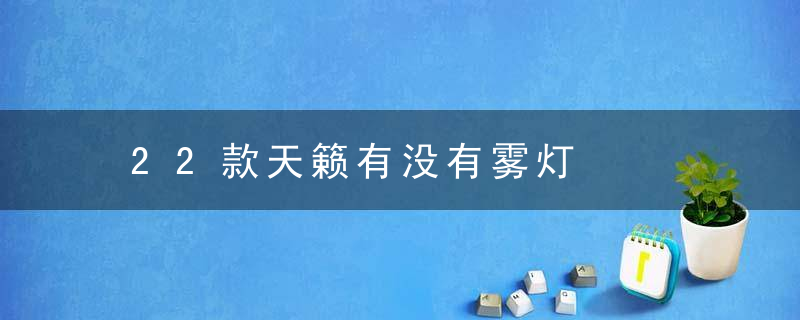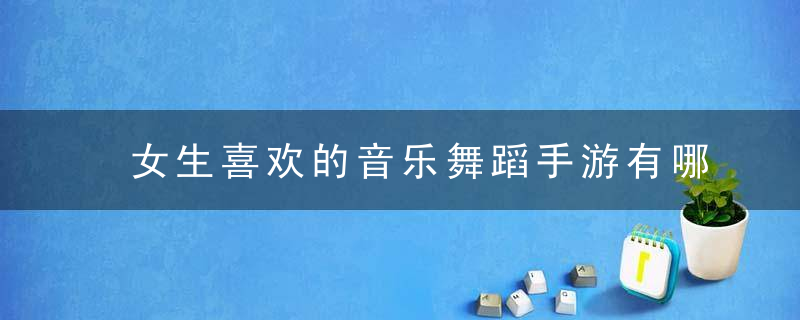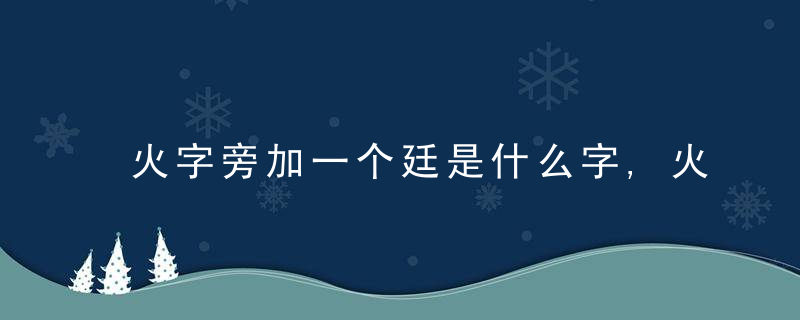何翔宇空白空间展览

Ana Finel Honigman
何翔宇用幽默的方式演示了跨文化的同化过程中伴随的艰难和挑战,让人们对这一过程有所了解,并能感同身受。全球化这一严肃的话题和它对那些被迫在不同国家之间漂泊的人们所带来的切身影响,在何翔宇巧妙而极具刺激性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的共鸣。例如,在他当前的视频作品系列中,来自柏林的被募集者用喜剧性的方式演绎出了人们在试图领会异国历史、使用另一种语言进行自如的交流,以及融入其它文化模式时所经历的困难。除了认知上的失调以外,何翔宇的作品还展示了迁移过程中充满人性与灵活性的一面。在这方面,居所的迁移将人们的创意、个性和好奇心转化为生存和交际的工具,甚至变成了结交新朋友的机遇。
在何翔宇的这组单频三画面录像系列中,每一幅画面的播放内容都是简单地以该视频于2016年的录制日期命名的。在录制前期,他在社交网站Faceboook上发布了一则试镜通告,随机邀请回复者参与并完成一系列即兴表演任务。这些的任务设计理念旨在展示人们在同化过程中所经历的挑战和后果。何翔宇以一名小组成员的身份加入到这些互不相识的参与者中,在相互给予鼓励、启发和评论的同时完成表演任务。他与其他参与者表演相同的动作,也被他们一视同仁地当作小组的一份子。
在《 五月十四日》拍摄的视频中,一组年轻男女围绕着木制餐桌玩剪刀石头布。赢了的人要到一根粘土制成的古典风格的圆柱上咬一口。最后,所有人一起上前咬下圆柱上的粘土,并将其吐到窗边的粘土堆上。随着这座经过嘴部啃咬后变得温暖而湿润的粘土堆逐渐增高,旁边的圆柱也在参与者的牙印下显得更加千疮百孔。一开始,他们打算像海狸一样啃穿这根圆柱。然而,当他们意识到粘土惊人的阻力后,他们改变了最初的野心而转为用肢体进行干预,以降低单凭嘴部获取粘土的难度,并增加单次获取的粘土量。虽然圆柱的表面还相对柔软,但是圆柱的中心已经在为期一个礼拜的制作过程中变得坚硬不堪。在每咬下一口粘土后,他们进行漱口,并用何翔宇提供的牙刷刷牙,但是粘土的残留物已开始在他们脸上结块,而他们本人也随着拍摄的进行而感到疲惫。在坚持了一个多小时以后,他们还是放弃了。对何翔宇来说,最后这根被他在视频完成后铸成青铜的圆柱,代表了西方文化在无数人深切的影响下变成某种新鲜、灵活而可塑的东西时所经历的缓慢而辛勤的转变。对那些刚刚抵达一个全新国度的人来说,以古典美学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传统是很难理解并改变的。然而,在这些传统的影响下,人们逐渐演变成了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混合体——正如《五月十四日》的参与者在那个看似可怕而坚硬的构造中留下自己的口腔记录和DNA的同时,他们本人也难免吞下并消化一些粘土颗粒。
在《七月十七日》,一些相同的参与者重新聚集在一起,与一些新成员共同完成一个不同的任务。这次的任务在扩张团队动力合作的同时需要参与者更直接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在一个由纸板搭成墙的房间里,参与者们以几个酒瓶为中心围坐在椅子或地板上,营造一种轻松而欢快的气氛。“文化”这一字样潦草书写于他们身后的纸板上。一位来自何翔宇工作室的组织者将这种布局称作“一个神秘的空间”,并用英文为在场的参与者讲解该任务的规则和过程。在他作完介绍以后,其中一位参与者发出一个简短的声音,而剩下的人则轮流模仿这种声音。这个声音的创造者在一轮结束以后再随机选择下一个声音的创造者。
随着表演的进行,参与者们保持着对他人的亲切感。他们不断地以充满好奇和支持的眼神望着对方,或友善地嬉笑,或无声地微笑。然而,几个参与者逐渐开始表现出竞争的心态,而其他人也跟着通过各自的参与推动表演的进行。其中一些明显热衷于自我表现的人抓住这个机会,用奇怪而浮夸的声音和哑剧式的动作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展示自己的独特之处。剩下的人则或多或少地表现得更加害羞。他们在坚持表演精神的同时有所保留。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发出的声音本身就具有暴露性。虽然人们不难设想这个游戏在进行中变得越来越具暗示性甚至粗俗,但是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表现出性的暗示。没有一个人发出性高潮的声音,或做出带有性含义的深呼吸。相反地,这些声音大多是吼叫、精疲力尽式的哀叹、愤怒的咆哮,或是某种动物之间的秘密语言。
当每个人发出声音的时候,他们看向右边的人,并将声音以顺时针的方向传递。这样的运转方式好比一段对话的传播,或许代表了某些日常口语词汇在重复和循环中扩散的特点,又或许证明了结构语言学中声音和其象征符号的组合实为随机配对的理论。《七月十七日》的参与者在表演中创作的声音甚至可被视为一门可辨识语言的一部分。在轮流的表演中,这些声音变成了表演者之间的暗语,并在这个团体内部得到理解和欣赏。虽然这些声音并不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人或物,正如人们没有以手中的杯子作为道具而将某种声音赋予一种饮品,但是他们的身体语言和对他人的回应其实正是联系建立的象征。这些指向元素让参与者将他人在房间里创造出的噪音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从而与他人产生关联。
总体来说,《七月十七日》展现了语言趋势是如何在最初建立的,又是如何在当今社会得到延续的。比如,人们经常能在全球各地的流行文化和特殊的表达方式中听到美国口音,就像因卡戴珊一家而众人皆知的“气泡音”。它代表了年轻女性发出的厌世、不满又粗粝的音调。这种气泡音已经代替了美国“山谷女孩”的“升调语势”,即每句话都以象征性的问号结尾。即使八十年代的青少年热捧这种升调语势,成年人却将它批判为迷惑、轻浮和过于随意。气泡音可被视为升调语势的反转,因为说话者可以让每句话的结尾变成愤怒的粗嘎而不是稚嫩的上扬。在《七月十七日》中,每一轮新的声音有时则是其创作者对先前声音的回应:阴郁而松懈的声音后紧接着欢快而活泼声音,粗犷的声音过后则是轻柔的声音。因为《七月十七日》的参与者被共同隔离在一个房间里开发并定制他们的语言,他们通过调整和模仿来互相影响。当自己的声音与先前声音产生联系时,他们在潜意识里的动机无论是为了辅助呼吸,还是为了将自己疏离于他人,这些声音最终囊括了先前所有声音的总和,以及当前发声者的个人印记。有些人可被视为他人的追随者,而有些人则致力于将自己区别于他人。
最后一部视频则是在8月27日录制的。出席了之前两个表演的一部分参与者又被请了回来,围成圆圈席地而坐。他们的任务是用参与者提供的具有科幻性、戏剧性的银色化妆品来装饰自己的脸。有些人将化妆品抹在脸颊和嘴唇上,其中一位漂亮的年轻女性则避开了自己的脸部和口红,而将她的头发涂满具有未来感的油彩。每个人的脚前摆放着装有蛋黄酱的瓶子——那种能在廉价食堂和美国高中找到的又大又黄的喷嘴瓶。
在《八月二十七日》中,参与者不再重复他人的声音,而是模仿他们邻座的面部表情。这个表情的创作者则决定谁的模仿最“差”,而剩下的成员则将他们的蛋黄酱挤到那个输家身上。无论是本能的选择还是预先的设计,他们全都将对方的脸和眼睛作为靶子。表演的终结则是当全员被刺鼻的黄色粘稠物覆盖、所有瓶子都倒空的时候。
从听觉到视觉的不同的交流模式有力地验证了文化沟通的流畅性不仅限于口头和书写的语言。据说,这种流畅性通常是无法在脱离了一个国家和其文化的语境下教授或习得的,因为深度的同化需要学习者认识并采用该文化的身体语言、面部表情和言谈举止。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会发现同一种面部表情在本国是合适而礼貌的,但在另一国则是奇怪、恼人而粗鲁的。微笑和大笑的问题尤其棘手,因为礼貌的大笑在某些文化里可因看似虚伪而令人讨厌。除了这些真正的冒犯以外,对言谈举止的熟悉和灵活使用可以将当地人与游客区别开来。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脸上的皱纹可以揭示他们的国籍,因为人类的皮肤在既定面部表情的决定下,会随着习惯性的肌肉动作而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离开了这些非口语的文化融合方式,语言将变得抽象而单调。在《八月二十七日》的背景下,一个无法成功模仿“当地”言谈举止的人招来了拒绝性的甚至近乎暴力的行为:人们试图用一种象征文化挪用和从众的物质将这个局外人覆盖。
蛋黄酱是象征文化转变的一个恰当符号,因为它总在刻板印象里被误认为是“无味的”,然而事实上,它能完全改变一道菜的味道和风格,同时包含了它自己扭曲的文化历程。虽然这种经过高度加工处理后的蛋乳剂通常与美国快餐联系在一起,蛋黄酱的起源其实在法国。何翔宇意于将蛋黄酱与古典大理石雕塑产生视觉引用上的呼应,从而在三部曲的最后一章和第一章中的圆柱之间建立联系。虽然蛋黄酱是欧洲的,并在比利时被用于“法式薯条”的标志性蘸料(这一事实让美国人感到震惊),同时在视觉上让人们联想到古典式的材料,将蛋黄酱加入多数食品中的做法确是美国的。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当蛋黄酱被加在寿司上的时候。这一潮流表明,在美国中西部城市的商场中售卖的寿司仅被用于同化而非培养美国的饮食文化。美国的文化挪用和食物的大量生产让人们将美国与《八月二十七日》中使用的大喷嘴瓶紧密相连。在参与者身上涂抹调味品这一行为表现了人们迫于服从西方标准的压力,虽然这部作品是在柏林拍摄的,这些参与者也属于从世界各地来到柏林的多元外国人群体。他们独特的个性让他们在这个城市扎根,也让他们自如地迁移。在这样的城市,一个象征着乏味的美式文化顺从的物质也许让人一开始觉得并不匹配,但是蛋黄酱也是一个文化重输的符号。当《八月二十七日》中的参与者被其他人用蛋黄酱惩罚,站在他们背后的其实是那群甘于服从的人。在拍摄的最后,无论他们在最初进入表演空间时的身份是什么,他们都平等地变成了一团团处理过的粘稠物。
何翔宇在之前的作品中也探索了脸部动作和表情是如何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又是如何将我们分隔开的。在他2015年的视频作品《乌龟、狮子和熊》中,他用高速摄影机拍摄了玻璃橱窗里的二十一个成年人(包括何翔宇本人,以及标题中的乌龟、狮子和熊),探索了打哈欠的神秘之处。这些人拥有不同的年龄、国籍和种族。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打哈欠。这种行为在他们之间或表现出像现实生活中那样的传染特征,或毫不相连,因为每个人的脸都被隔离在各自的玻璃橱窗里。他们的动作突显了这一频繁出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具有普世特点的神秘现象,以及这种现象或将人们疏远,或让人们感同身受的性质。当动物打哈欠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又无害又可爱。虽然一些食肉动物在打哈欠的时候露出他们的牙齿,这个动作本身代表了疲劳、舒适和信任,因为它是睡眠的前兆。据说,人们在看到他人做出张嘴吸氧这一举动时,会认为这是空气稀薄标志,所以也会相应地做同样的动作。无论这个理论成不成立,打哈欠通常是休息的许可。然而,在人类社会中,打哈欠在紧急情况下则成为了一种对权威傲慢的拒绝方式。对观众来说,在艺术作品的刺激下而打哈欠的动作打破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的障碍。这件视频装置为《八月二十七日》中参与者之间无声、纯肢体的交流奠定了概念上的基础。
通过在他的视频三部曲中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态,何翔宇对迁移和在异国同化时令人苦恼的过程表达了新的理解。在我们身处的全球化时代探讨同化和扩大文化身份的挑战是何翔宇在作品中惯用的话题,虽然他在过去作品中传递的语气比当前作品中的要更加黑暗和消极。他最有名的作品是2009至2011年创作的《可乐计划》。在这个大型多媒介作品中,他雇佣了十余位工人将127吨可口可乐在木材厂里煮了一年,并将这些令人作呕的残渣运用于多件作品中,探索可口可乐作为首个全球品牌之一的跨国普及性。在一个项目中,他将残渣变成墨水,绘出一组仿宋风格的山水画。作为这一作品系列的高潮,他创作了一个完全由可口可乐残渣组成的装置,看起来好似一片经核武器轰炸后焦黑的荒漠。在2015里昂双年展,大片的残渣也作为《可乐计划》雕塑的一部分展出。在这件作品中,这些化学物质看起来如死亡一般沉寂。材料本身的黑色否定了可乐在其品牌营销中对快乐和趣味的保证。相反地,它的颜色因为看起来似乎吸收了所有的光,而显得十分危险。在对可乐的熬炼过程中,何翔宇证明了可乐除了它给人的“感官刺激”以外,完全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对身体也没有任何益处。这个品牌横扫全球的饮食文化,通过创造一种超越当地口味和传统的共同体验,用其粘稠的、油性的液体将人们凝固在一起。虽然人们的个人经历显示,相同的汽水品牌在不同国家因当地气温或水源环境的不同,其口味也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给人带来的核心体验是一样的。它们为游客建立了一种感官的熟悉感,也为跨地域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可分享的共同点。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胶水,可乐跨越了文化和国家和边界,将全世界的人一起变成了其品牌虚假销售的受害者,因为它在宣传自己对身体有益的同时,促使人们从摄入健康物质转而饮用这个化学废料,从而危害了消费者身体。
这个关于价值的问题在何翔宇2012年的雕塑《200克黄金,62克蛋白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索。这件作品包含了一个纯金的蛋托和装在里面的一只普通鸡蛋,暗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此政策深刻地塑造了何翔宇这代人的价值观、焦虑感和身份认同感。同时,这件作品还影射了2012年发生的一则国际性丑闻:中国的食品生产商被曝在日常食品的制作系统中掺杂假鸡蛋。这些假鸡蛋被以冠以农场直销的名头,却实则包含树脂、石蜡和色素等有毒原料。科学家们警告当地消费者,这些假鸡蛋看起来又圆又白,看起来不切实际地完美,并缺少一种鸡蛋的气味。这些让人上当受骗的鸡蛋由艺术材料制成,却少了维持生命所需的有机成分。正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让父母不得不把孩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优等生,这些假鸡蛋消除并玷污了自然性的差异,反而将价值赋予一种衡量成功的错误手段。作为一种人工产品,假鸡蛋代表了人类在工业生产中极力追求完美的意识形态,否定鸡蛋作为一种“生命的动力燃料”维持并充实当下生存状态的价值。这只假鸡蛋下面的金蛋托看似华丽,却无法为身体提供任何养料,也不能让我们维持生命的延续和健康。正如演员沃尔特·赫斯顿在1948年的经典电影《浴血金沙》中所说:“金子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人们在寻找和获取它的过程中付出了劳动。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原因。因为金子本身除了做珠宝和金牙以外一无是处。”同样地,拒绝差异而崇尚完美的做法,也许可以让表面看起来赏心悦目,却破化并扼杀了生命更深层次的愉悦和潜力。
正如他当前视频系列所传达的理念,何翔宇在2012年至2016年间创作的《口腔计划——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聚焦于同化现象除从众性以外,独具探索性的本质。这一系列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和妻子从北京到匹兹堡的移居。居住在匹兹堡这个文化上相对隔绝的城市,何翔宇将大量的时间放在学习英语上,并开始觉察到自己口腔内部在适应这种全新而陌生的语言时感受到的差异。正如人们的第一语言通常被称为“母语”,他的嘴在说英语的时候更像是个陌生人。何翔宇在与心理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交流后发现,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调查研究证明了人们在说不同语言的时候,会彰显出自己个性中不同的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倾诉痛苦或表达强烈感情的时候所倾向于使用的语言,通常附属于那些具有更突出的移情式交流和感情意识的文化。如果被心理健康问题所折磨的人生活在一个在传统上将此问题污名化的文化中,如果他们能够在向心理治疗师敞开心胸的时候,使用一种与宽容而先进的治疗文化紧密相连的语言,也许会感到更加自如。
通过《口腔计划——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不是我们自己》中的水彩、综合材料绘画,何翔宇复制了他嘴里的凸起和凹槽,用这种切身的方式将触觉“转译”成视觉,让他能够在尝试陌生的表现形式时依然保留本真的自我。这组抽象作品用生理结构记录了他在自身特点里寻找那些能够被转译到另一种文化里的品质,和那些无法被转换到其它语境中的品质时,在身份认同上所经历的改变。
通过改变创作媒介,何翔宇在《口腔计划——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2013)中将核心探索延展为一系列由他的口腔模型制成的铜雕塑。这些雕塑表现了他用舌头触及口腔内部时的感觉。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种感官体验绘成画作,而是使用了一种不同的介质。当提到这种特殊媒介的时候,鲍栋把它称作“雕塑的蓝本”。这些雕塑陈列于一个铺有地毯的房间,墙面被涂成了口腔一般的粉红色。参观者可以通过触摸的方式感受这些凹形的雕塑表面,用手来替代舌头。与《五月十四日》中的模型相比,这个模型将我们在婴儿时期用嘴来感受并探索这个世界、却注定短暂的经历,交融于一种宝贵但不稀缺的金属,使它成为永久存在的艺术品。
1986年生于中国宽甸的何翔宇属于可以用全球身份来定义自己的那代人。当代艺术家尤其幸运地加入了国际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了文化的流浪者。何翔宇作品的核心之一就是这种跨国的身份,进而探索了在不断改变的外在环境中坚持自我的挑战和复杂性。在世界势正变得愈加分裂的时期,他的作品反映了每个人在与文化规范、风俗习惯和相悖于自己童年时期所受影响的简单交流形态之间的摩擦中成长和发展的潜力。
在何翔宇作品的核心,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意识:认为同化是并非人人皆有的特殊才能。这种才能不见得是意志和智慧的体现,但却是一种天赋。有些人天生就善于学习语言,能够像变色龙一样灵活穿梭于不同文化环境之间,然而有些人则在吸收全新特质的时候感到格外吃力。但是,当我们来到一个令人晕头转向且带有批判性的新环境中时候,他人都用当前的即时信息来对我们加以评判。当我们费力地与人沟通时,别人会认为我们理解和处理信息的过程过于缓慢。然而,真正的鸿沟不是理解,也不是批判性分析,而是表达。有些人认为通晓多种语言是超常智慧的象征,却忽略了说话内容这一真正的问题。在当今世界,人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生长和居住,使得有些人没有所谓单一的“母语”。他们也许精通多种词汇,却无法用某一种语言抒发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哲学性的基本思想。何翔宇并不怀疑语言学家的天赋,而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对那些无法流利进行多语言交流的人的价值批判。
作为一名艺术家,何翔宇表现出了灵活并熟练地运用多种媒介的显著能力。仅在《口腔计划——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中,他优雅地从绘画转换到雕塑和交互式装置。在这个转变中,他有策略地带领观众先用视觉直接地感受他的世界观,再深入到他的感官和见解。使用艺术手法的流利性与他学习语言的困难性形成了有力的呼应。在当前的视频三部曲中,他又在自己的创作词汇里加入了表演这一元素。他邀请参与者成为词汇的一部分,以传达他对同化的方法和效果的研究。在证明自己富有创造性且融会贯通的创作能力的同时,他探索了语言学局限性的引申和其重要之处,证明了我们几乎无法依赖于纯口头的表达方式来代表我们自己并塑造我们的身份。
在作品中,何翔宇还提出了一个问题:文化吸收的艰难是否标志着个体的正直性和严密性?当《七月十七日》和《八月二十七日》的参与者在无法复制“当地的”声音和面部表情的时候,他们究竟是在游戏里处于下风,还是在团队里贡献多元的成分?他们对既定交流模式不寻常且特立独行的重复方法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事实上,这些声音是否仅仅呈现了一种与常规不同的交流方式?这种差异性是否帮助他们进化或腐化既定的规则?如果新加入的人无法自如地进行交流,他们该如何对群体做出贡献?在融入新环境时受到的阻力是困难,还是在新世界中打开眼界的机会?“外国人”的身份又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对世界的贡献?通过强调这些问题,并将存在性意识应用于融入新文化环境的社会和形体过程中,同时认识到迁移在建立新家园方面的潜力与受到排外和拒绝的风险,何翔宇质疑了个体的本质和其适应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