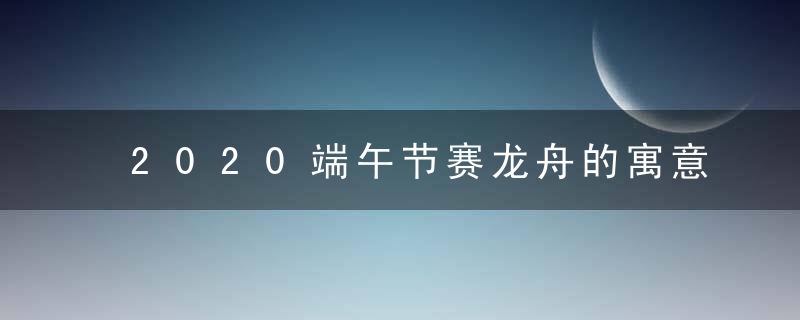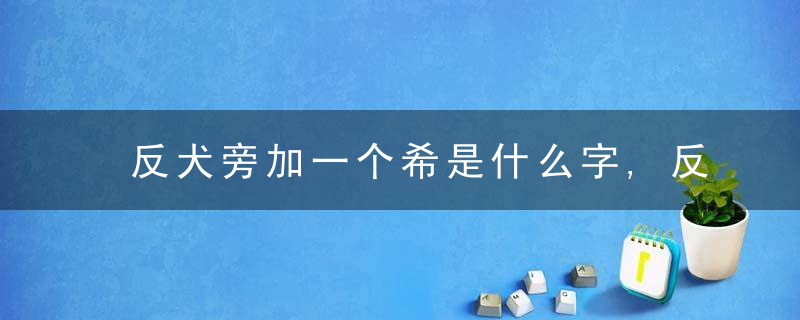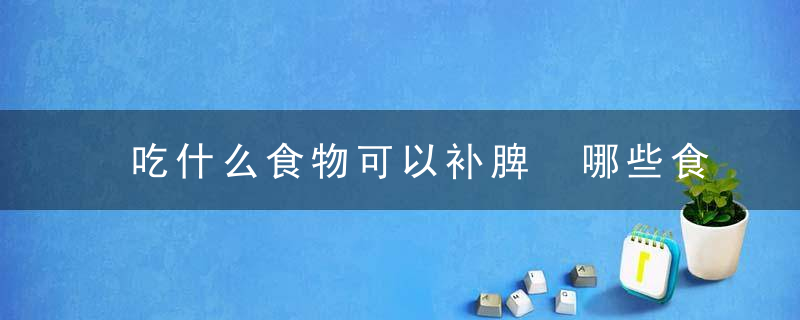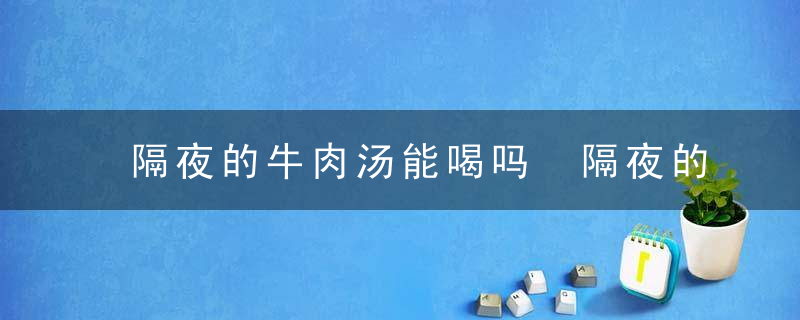端午起源与屈原无关 屈原与同性恋无关

摘要ID:ipress
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民间通常认为是纪念屈原,此外也有纪念介子推、伍子胥或曹娥女的说法。这四者都不是端午节的真正起源。
闻一多在《端午考》等文章中,考订辨析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端午起源与龙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古代吴越民族(一个龙图腾氏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始于人们为生存而与水患水怪的抗争。春秋时期,吴越之地初经开发,人们敬畏鱼虫水兽,遂断发文身,舟造龙形,并向水中掷以虫食,祈福消灾。这习俗渐从吴越之地溯江上延至荆楚流域,再北上至中原。
浦江清《谈端五节》同样认为端午起源与屈原无关,并称端午节应作“端五节”,他解释说:“端者,初也,端五便是初五,指的是五月初五。原来古人把数目看得神秘,这个日子有两重五,显见得奇巧不寻常的。所以五月五日,和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都算是一个节。那种奇巧的日子,古人对于他们有相当的忌讳。”
浦氏进一步分析说,正因忌讳五月五日之奇巧,民间遂以毒攻毒。划龙船闹锣鼓,是要炫示力量,以克服水怪;饮雄黄酒、焚苍术、插菖蒲,是辟瘴气;扎艾人、艾虎、艾剑则是祛魔;粽子也是辟邪的东西,主要靠捆绑粽子的五色丝线。汉人应劭《风俗通》就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
从端五开始,天气渐渐炎热,蛇虫百物活动起来,痢疾、疟疾、霍乱、伤寒等容易流行。古人缺乏现代医药知识,又恐慌疾病死亡,于是想到用草木药物来辟毒制鬼。
由此看来,端午起源可能与图腾崇拜有关,后来又加入了依靠草木药物辟邪祛病的成分,并非源于纪念屈原。
不过,端午起源虽与屈原无关,在后世却渐渐演为纪念屈原的节日。吃粽子与赛龙舟,都变成纪念屈原的专项活动。
据梁代吴均《续齐谐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于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并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上,以五彩丝转缚之,此物蛟龙所惮。’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树叶,皆汨罗遗风”。
另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端午……以菰叶裹黏米,谓之角黍……或云亦为屈原,恐蛟龙夺之,以五采线缠饭投水中,遂袭云。”
不止吃粽子,赛龙舟也从图腾崇拜,演变为对屈原的哀悼。
《荆楚岁时记》又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隋书·地理志》所记更详:“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櫂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皆然,而南郡尤甚”。
要言之,屈原与端午风俗有关,与端午起源无关。
有意思的是,每到端午,“屈原是同性恋”的话题就要被翻出来炒一次。我们只要搜下“屈原+同性恋”,就可看到此类奇谈怪论充斥坊间,满是洋洋得意的民科气息。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此为屈原辩诬,并非认为屈原若是同性恋就贬低了其人格或文学成就,同性恋本身不存在贬低屈原的问题,但就现存史料与文献而言,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表明屈原是同性恋。
较早怀疑屈原“娘炮”的,大约是1943年,游国恩在西南联大文史讲座作题为《楚辞中的女性问题》的演讲,指屈原“自比弃妇”。游氏后将演讲改为论文《楚辞女性中心说》,附于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书。
游国恩演讲不久后,1944年,孙次舟在《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第一次提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引起轩然大波。后人常称闻一多为孙次舟站台,其实我们若认真读闻一多那篇《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就会发现,闻一多只是部分同意孙次舟指屈原为文学弄臣的说法,而从未支持屈原是同性恋的说法。
时光流转,屈原是同性恋的论调再度流行,猎奇者有之,好翻案者有之,仆人眼中无英雄者有之,但这些论调,主要建立在臆测之上,缺乏证据。
我不打算就此问题繁琐考证,只简约说三点。
第一,同性恋在战国时确已盛行,并非社会禁忌,分桃、龙阳等典故也早为人熟知。古代中国对同性恋性行为较多宽容,较少制度性歧视,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古代中国没有宗教传统,不会从信仰层面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罪恶;
二是古代中国主流的儒家学说很少论述同性恋话题,也许认为它无足轻重,就是一种身体娱乐方式,不值得赞同也不值得反对;
三是中国古代同性恋性行为多发生在特权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前者对后者往往只有性的支配,而没有基于平等尊重的爱情发生。换言之,同性恋性行为在古代中国,往往只是特权阶层享受的一种性福利。特权阶层是规则的制定者,当然不会作茧自缚,去反对同性恋性行为。
这最后一点对屈原是否同性恋,甚为关键。
屈原是楚国贵族,为楚怀王左徒,地位仅次于最高官职令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可见屈原是当时贵族士人之领袖,所负国事甚重,不是所谓宫廷弄臣,更不是楚怀王的同性恋伙伴。
第二,屈原赋中的香草美人,只是比喻,决非爱情独白。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说,“中巧者猎其艳辞……童蒙者拾其香草”,拘泥于美人香草的人,只是抖机灵的小朋友,是Naive!
其实不必王逸与刘勰说,任何一个懂诗歌的人都知道,诗歌最怕索隐与附会。那些被当作屈原同性恋铁证的辞句,比如“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比如“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都很好解释。前者就像说领袖万岁一样,是一种有时代局限的忠君思想,可以说屈原愚忠,却看不出什么基情。后者则是屈原将政敌们,那些小丑样的腐败官吏比作爱造谣的长舌妇,这哪有同性恋嫌疑?
第三,《离骚》篇幅最大的一段,就是追求女人,正大光明、兴师动众地追女人。从听了女媭的一番责怪开始,他就上天入地的追求女人,不但追,而且追很多个,结果都没追到,还要“忽反顾而流涕”。
等到“灵氛吉占”之后,又再度飘扬过海,大张旗鼓地西行。去干什么?还是“求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屈原看成花痴,没追到女人就痛苦,就要投河。热烈追求女人,追求之后哀伤的失败,依然是比喻,指向一种幻灭的状态。
这就好比崔健唱的,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理想都破灭了,用《离骚》的本文则是:“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闺中与哲王是对立的关系,前者乃逃避现实的寄托,后者则是无法直面的残酷现实。
关于屈原的奇谈怪论,不止同性恋一端。我曾见一本怪书,是日本学者大宫真人写的《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该书考证说,屈原没有投河自杀,而是漂到日本九州一带,在那里写出《离骚》、《九歌》、《九章》。这书更像小说,而非学术著作。
我少时还读过一部书,讲的是杨贵妃没死,在马巍坡绞了个半死,又活过来了,也是漂流到日本,在那边进入宫廷,嫁给天皇,生了一大堆娃云云。
我厌恶这些奇谈怪论,因为我读屈原辞赋,为其优美的哀伤与理想主义的光芒深深打动。在《离骚》中,到处都是至美的句子,上天入地只有绝望的浪漫,活色生香全是高举的孤清。而他捍卫自己理想时,是那么孤独那么如怨如慕,却又那么坚定那么正道直行。
(傅抱石作品《屈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在犬儒成群、鸡汤风行的今世,屈原那种“宁赴湘流”也不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的人格力量,就更加令我尊崇与感怀。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太史公真是屈原的千古一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