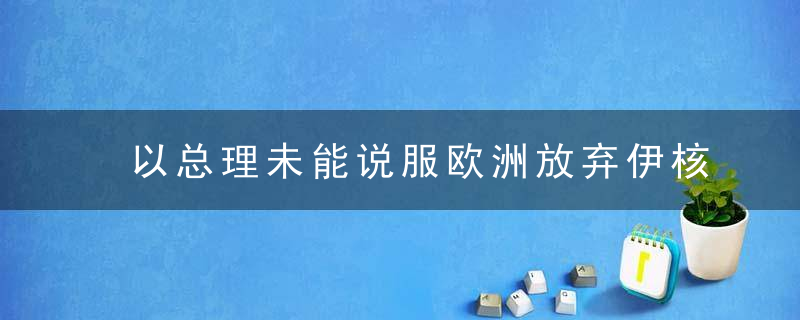为什么回国后我这么害怕变成“社会底层”

本文作者:孟常
从欧洲搬回来的第二年,我觉得自己得了抑郁症。
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听了我的“病情自述”后调侃道,不就是创业失败吗?少给自己加戏。
创业失败十之八九,实属平常,我回国前就做足了心理建设,自己也并非被国内的创业热潮撩得脑门一热就决定要回国。
我在欧洲住了四年,不长也不短。
在欧洲的日子几乎是完美的,但在搬离欧洲前的最后半年里,我迫切地想要摆脱那种致命的舒适和可能性的匮乏;与此同时,国内的活力和复杂让我向往——不是流行段子里所谓“CEO、敲钟、白富美”的诱惑,而是看到国内有想法的朋友都在积极发表自己对世界的见解、实践在某个领域的判断或经验。
那种一切流动着向前、复杂多变的时代氛围,欧洲没有。
经过理性地思考和分析,我带着几大箱行李回了国,开始新的冒险。
如今时隔两年后回望,我仍未后悔当初的决定,创业虽起伏跌宕,但我的确获得了在欧洲不可能经历的多元经验和复杂情绪。
那让我陷入焦虑、痛苦和不安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强烈的“陌生感”。
对这个充满活力和机会、却又价值单一和苍白的时代,我不能转过身去假装看不见,却也不能说服自己热情地起身拥抱它。
我卡住了。
回国后我变成了“少数派”
我一直自认为是在一个在价值观上“百毒不侵”的人。
经过十年间在不同国家、文化和群体里生活的经验,我已形成了对“我该如何生活”这个命题的基本观念和态度——彻底抛弃那种流水线式的“读书工作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的模式,过一种更主动、更开阔的生活,肩负起选择和行动的自由,也接受自由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当然,我并非对上述各项“人生活动”抱持偏见,而是不认同它成为强势的、默认的“出厂设置”,进而绑架个体的自主意志——好像活得跟别人不一样就是某种残缺或失败。
我在欧洲时,身边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的确都活得开阔而主动:他们自由地探索和发展自我,享受创造、体验和分享的乐趣,也不放弃寻求公共层面的价值和意义。
他们中有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30多岁的“中年人”,年龄只是数字,不存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的所谓规范,而婚姻亦只是选项,并非人生的“标配”,一切都不应偏离那个终极的召唤:我该如何度过这一生?
一切都是围绕“我”发生的,“我”可以自由地思考、决策、行动。
最重要的是,没人会来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你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冷暖自知。
可一回国,这种“边界”消失了,身边出跳出无数嗡嗡作响的声音试图占领你的头脑、争夺对你生活意义的阐释权。
“看看身边还有像你这么大还不结婚的吗?”
“你去过很多地方,有很多经历,但又有什么用呢?我告诉你,在国内你要实际点,你在外面这几年已经错过很多上车的机会了。”
“你已经30岁了,快被95后淘汰了。”
“你怎么还在做媒体这么没钱途的事情啊……”
这些声音往往来自熟悉的亲人、朋友和社交圈。
我在国内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自己是个“少数派”,被外界一次次置入“框架”中去审视和评判(judge),虽不至于说价值观动摇,却也在精神上跟外界反复地对照、拉扯与冲突中,耗费掉了大量的心力和激情。
但在欧洲,完全不存在“跟外界对抗”、“守住自我”这些防守环节,一切都是打开式的,不管你做37岁的单身青年还是文学女博士,没人有兴趣评判。
我有时候在想,中国主流社会里那股强大的同化力量,究竟是因为“少数派”恐惧跟别人不一样而主动地“自我改造”,还是“多数派”担心少数“漏网之鱼”会消解主流标准的绝对正确性?
人们一边担心跟别人不一样,也一边劝诫身边的人从众。
国内的价值系统太单一
去年年末,坐在香港能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的酒吧里,我向一个在上海做风投的朋友请教,究竟什么叫“再不上车就来不及了”?
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说就是像你这样:最该在北上广买房的时候出了国,又先后错过了互联网创业最火热的时机和今年的区块链。
像我这位朋友一样,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似乎默认,所有人都是喜欢这个时代并积极拥抱风口的;如果你没顺利“上车”,只能是你能力或运气差,不会有别的原因。
换言之,你怎么可能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呢?
这让我想到在香港生活的经历。世界著名的金融之都里,纽约和伦敦都具备相当程度的多元性,或许只有香港,会将现代金融业摆在在如此核心的位置,因而其从业者也自然是整座城市社交生活中的精英和焦点。
在香港从事金融业的大陆人,无一例外都家境优良、出身名校,举手投足间精致里透着聪明。虽有不少人表现得谦逊和理性,但大多数人都庆幸自己身处这个城市最中心、最赚钱的行业,并因而充满优越感。似乎如果你没做金融,就是能力不够,否则的话,就是你有更赚钱更好的选择。
就像前段时间在微博上,有大V发表了一番“理科沙文主义”的言论,引起争议。
他认为绝大多数选择文科的人并非出于兴趣,而是由于“数理化学不明白”,因此文理科本质上是“智商筛选”。理科就业率高于文科是正常的,诗词歌赋这种文人情怀在这个时代充当不了生产力。
姑且不论这番言论是否充满偏见和逻辑漏洞,它的确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主流社会根本性的实用主义和现世主义倾向,那就是了除了能够带来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实际事务,世间没有什么超越性的价值值得追求,如审美、情感、体验、意义。
这种绝对、单一的价值系统,否认个体有自我定位、自我阐释的权利。
如果你能够挣得十分,就不应该只要五分,不要问代价是什么,不要计较开不开心;只要你跟我们不一样,你就像个怪物,会活得很惨。
一个香港建筑师朋友告诉我,之前在内地工作时经常被当做“盖房子的”,在甲方爸爸面前毫无职业尊严,他感叹说内地似乎没有对“专业主义”的尊重,不同职业之间有贵贱之分。
我苦笑着告诉他,当我在国内说自己是做媒体的,就会被问是不是做号的?有多少流量?
而在欧洲的沙龙聚会上,大家通常对艺术家、作家、学者、设计师、记者等职业颇有好感,因为这些似乎是需要创造力、“不是谁都能干”的一个行当。
当然,酷到没朋友的是DJ,最酷的则是平时做上班族、周末做DJ打碟的那些家伙。
我在欧洲时常聚在一起的朋友遍布各个行业,有做设计的、管理仓库的、在酒吧调酒的、开纹身店的、做程序员的、在公司做行政的,当然还有做金融的和无所事事的,没人关心对方在各自行业里的成就、前景和收入,大家都随意地聚在一起分享时间、见闻和笑话。
其实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从事着我们看来很“平庸”的工作——我必须承认,最初中国社会把我训练出来的“本能”起了作用:
“她这么可爱,却只是一个特殊儿童的幼教……”
“他这么聪明风趣,可居然只负责管理仓库……”
“他硕士都读完了,却跑去处理国际学生的宿舍申请……“
可他们都幽默聪明,活得开阔自由。
更重要的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对他们正在从事的职业抱持着真挚的热情,都从中发现了无尽的价值和意义感——无论是利他、快乐、自由还是个人成长。
内心失衡,到底怪谁?
从数据来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中位数工资已经超过了东欧和除智利之外的拉美国家,接近了南欧国家。至少就我的个人观察而言,国内中产的收入已经超过、或至少不低于欧洲相应行业的工资水平了。
可当欧洲30岁上下的年轻人还在恋爱、换工作、旅行和探索自我时,国内的同龄人却终日活在焦虑和忧惧中,担心房子供不下去、换不了新车、孩子上不了名牌小学、职位有天被更年轻的世代或机器人取代。
在欧洲拿一两万(人民币)的月薪,无需依靠父母帮助,完全可以独自在城市里供一套小公寓居住(除了伦敦和巴黎)。但我的绝大多数欧洲朋友都没有买房,他们骑自行车或搭公共交通上下班,刚刚用上第一部智能手机,有些还在还学生贷款。
拿欧洲对比中国似乎不太公平。
一是平等主义在欧洲社会已经扎根,而对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说,或许正是过度的平等主义造就了欧洲今日的沉闷和平庸。
二是各自的发展阶段不同,中国仍处在高度发展的上升期,阶层流动的空间仍在,人们有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动力,而欧洲社会的固化或多或少消磨了年轻世代的“奋斗意志”。
朋友就笑我太不接地气了:纹身师和DJ?在国内这就是社会底层啊!
成为底层会怎样呢?会被歧视、侮辱和践踏。
在欧洲,你大可选择做一个快乐自由的普通人;但在国内,连所谓中产精英们都有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生怕脚下一滑掉落了阶层。
这种内心的失衡或许可归因于现实情境,但也不可逃避自身的责任。
欧洲人本能地从“我”出发,崇尚参差多态的幸福路径,而国人的意义和幸福感似乎都仰赖于外界的认证和比较——“我”不是目的,而是被审视的对象;“过得好”不是一种内心的感受,而是能否跟大多数人一样,最好还能形成碾压性的优势。
我一位远房亲戚,夫妻二人在上海有两套房、刚换了新车、小孩进了市中心的公立幼儿园,月费200块。可他们仍纠结而不安地活着,比如好友去美国生了第二胎,比如是否刚把孩子送进月费一万的国际幼儿园—— 已经跟孩子无关了,纯粹是成人世界的“明争暗比”。我过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比目光所及之处的“别人”好
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很多人付诸于生活的努力已被“异化”,忘记了停下来喘口气,想想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
在此地,你尽可能多地攫取资源和优势,就意味着多了一分安全感。所有人都尽力表现出对这个时代的狂热,不管那来自焦虑还是兴奋;少有人还在谈论价值、美感和公义,因为这些在时代的叙事里毫无意义。
这一切令人沮丧。
我没打算回避现实,也对这时代那些有开拓性的创新感到振奋。我只是对那种狂热而单调、裹挟着大多数不假思考往前奔跑的情绪和价值保持警惕。
一个多元社会的可爱之处在于年轻导演胡波们能自由地创作,企业家们也能全力地创新,这些价值和生活之间并无高下贵贱之分,都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不是一套价值彻底占据了其他价值生长和繁荣的空间。
我理解亲友的担心,他们担心我只凭喜好、不论未来的自由生活错过了时代的机会,而最终沦为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而那可以想见是悲惨的。
但说到底,你多少岁结婚、买没买房子、创业成没成功、信奉什么样的理念,如果轻易就被外界影响的话,说明也没什么好值得坚持的了。
所有对时代热潮冷眼旁观、抗拒单一而霸道的价值体系的人,其实都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无论是在30岁后仍然保持单身的姑娘、性少数群体,还是只想要自由而清醒地活着的人——他们寻求小共同体内部的安慰,不奢求改变潮水的方向,只力求站稳不被浪花卷走。
欧洲自然也有它的问题和困境。
我跟一个以色列好友聊过,欧洲年轻人缺少对生活痛苦和复杂性本质的接受和体认,对他们来说,如果你感到烦恼,没有什么是一场旅行、一次派对或一杯啤酒不能解决的。
而且,欧洲人也当然并非都是“行走的自由意志”,托尼 · 朱特就曾哀叹,这一代人中最杰出的头脑都想要投身于华尔街而非公共领域。
搬回欧洲就能够解决我的焦虑吗?
我清楚地知道,这只是有着时代特征的“围城”:有多少人咨询如何移居海外,就有多少海外的朋友在计划回国发展。
至于我,我已经放弃“上车”了,借用创业圈的一个术语,我有自己的“赛道”——非竞技性的那种。
毕竟真正重要的是,不管在哪里,都接受生活痛苦和复杂的存在本质,清醒而自由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