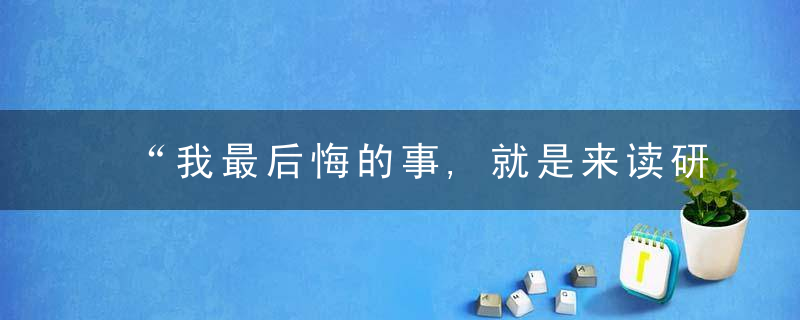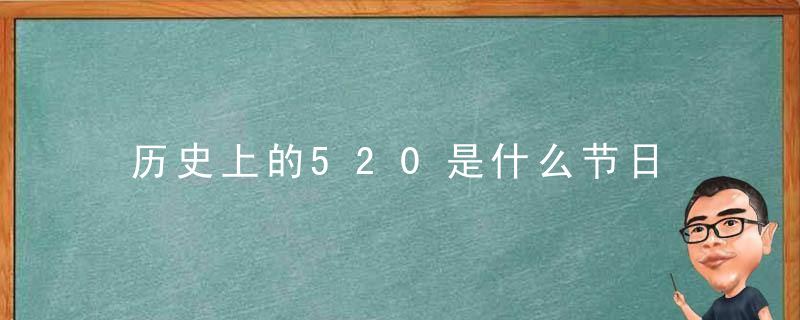八年来的回忆1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於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於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麽,对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於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於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於矫饰,而不是坦白的白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总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於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於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 汪先生的心境关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人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指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麽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於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後,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後,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後,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於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 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後,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确苦闷达於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於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後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覆,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後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於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後,没有说什麽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後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於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邢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於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於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後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後,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於後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後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 和平运动前後和我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麽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覆,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於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特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於何时。到後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於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和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麽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後,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於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万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麽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於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麽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麽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後我每天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後来汪先生税,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後,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渖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对於国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於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後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