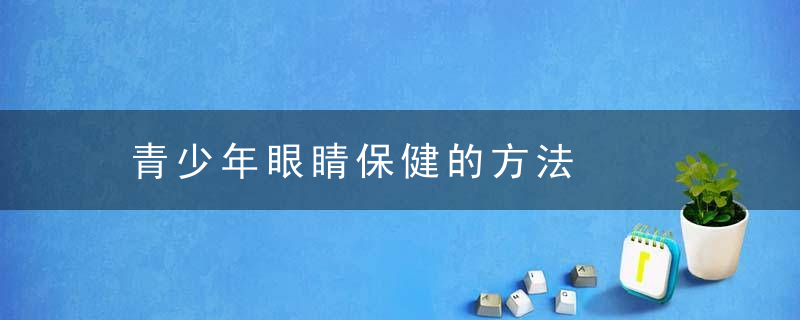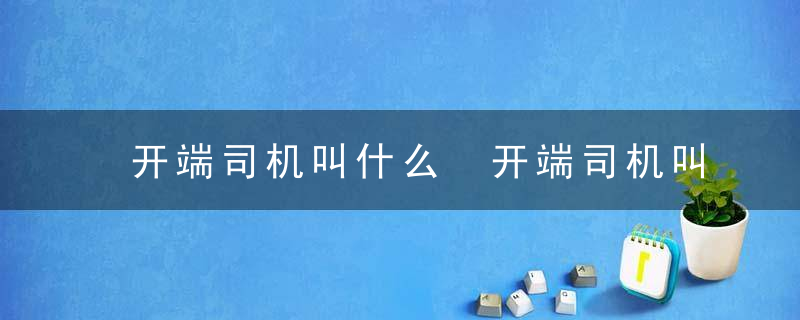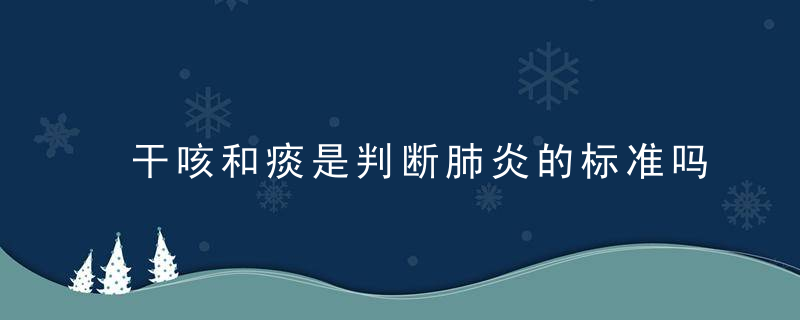凌晨三点的医院大厅, 你没有见过的人间

从北京回来后我一直在尝试各种行业,各种工作。从最开始要求和专业相符的工作,五险一金齐全,有双休;到后来的什么要求都没有,只要让我能活得下去。
人生就是让你本设想的一切都发生偏转,偏转后你所遇到一切的总和,就是你真正的人生。
每天西装革履地拿着微薄工资,穿行在被机械喧闹和化工异味包围的工厂之间,在精明的供应商和龟毛的领导之间左右逢源,然后习惯性地为所有人擦屁股。
长期的焦虑让我产生了幻听,时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骤然惊醒,醒来的时候耳边就像是听到海浪声般嘈杂,然后一夜无眠。
这种感觉就像是被琥珀黏上的苍蝇,越挣扎,那种束缚感就越强烈。
直到有一天凌晨惊醒后,我听到了急促的救护车声,鬼使神差间我起身下楼,朝着附近那家医院走去。
在那里,凌晨三点的医院大厅,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人间。
医院对面的街上永远有那么几家24小时营业的小吃店,在救护车开进去后没多久,就会有病人家属急匆匆赶过来。
等该来的人都到齐了,大家会在医院门口简单说一下情况,然后留下一两个人到24小时营业的店里去买个东西,只为占个位置睡觉,做好轮岗的准备,剩下的人则跟着医生去急诊室,随时准备待命。
与其说是小吃店,不如说是旅馆。
这是只有深夜才开的旅馆,也只给那些被命运捉弄的人。
老板给病人家属煮一碗面,然后站在旁边,听着家属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诉说病人的一生。
每到这个时候,家属都会说得很慢,仿佛生怕说快了,这个昨天还活生生在自己身旁的人就会离开。
有时话到一半,家属就会接到来自急症室那边的消息。
关于病人接下来所有的故事,往往都在这一通电话里了。
那天夜里我听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位72岁的尿毒症患者,自杀。
在深夜旅馆里坐着的,是陪伴他半世的夫人。
我虽然没有见过老先生,但从他夫人的描述中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他的模样。
老先生是位离休干部,一生要强,和夫人一起抚育一双儿女长大,在孙辈承欢膝下的时候,老先生被查出慢性肾炎。
从慢性肾炎到尿毒症,只有一年不到的时间。
总说人生无常,但我们说这四个字的时候都说不出命运的沉重感,而能说出沉重感的,大抵也不愿对命运开口了。
从三天一次透析,到后来一天隔一天的频率,老先生的手臂就像是蜂巢般排布着大量让人触目惊心的内瘘,每一个内瘘都是透析管刺入身体留下来的痕迹。
随着透析的时间越久,被药物清洗过的血管会逐渐萎缩,再也无法承担透析的功能,最后医生只能寻找新的部位做血管造瘘。
“好死不如赖活着,老先生这又是何必?”老板说着翻了翻热锅里沸腾的面条,在昏黄灯光下,大团大团的热气沸腾着弥散在半空中,模糊了所有人的视线。
“他很骄傲,他这辈子都很骄傲,所以他想再最后骄傲一次。”
老夫人的声音很平静,想必在与病魔对抗的这一年多时间里,她已经亲眼目睹了一个苍老却骄傲的战士是如何一步步被疾病摧垮的。
在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既渺小又伟大,他们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但却握着命运交给他们的这副烂牌,尽己所能地打出了最好的水平。
短暂的沉默很快被手机铃声打破,夫人坐在那里看了手机很久,半晌才接通了电话,嘈杂的声音断断续续,伴着压抑的哭声,在安静的深夜街头显得格外清晰。
“仔,和你姐好好哭一场,然后我们一起接你爸回家去。”
迟来的面才刚刚端上来,老夫人已经整理好了一切随身物品准备起身了。
“您面还没吃呢。”老板的声音越来越小,他看到老夫人有泪水在无声地流淌。
“谢谢您啦。”灯火辉煌的医院急症中心前,老夫人缓缓穿过少有人迹的凌晨街道,她的双手捂着嘴巴,最后在绿化带的阴影中缓缓坐了下来。
被路灯拉长的影子孤单单地落在地上,从此余生,再难成双。
因为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所以我很讨厌医院大楼里浓烈的消毒水的气味,但我还是走了进去,因为那里是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的人间。
凌晨三点的医院大厅里摆放着大量的床位,病床上的患者都是因为床位不足而不得不暂时安置在外的病人。
几乎所有的床位旁边都蜷缩着一到两个疲累到陷入麻木的家属,他们睁着眼睛靠在行李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充斥着问题,而每一个问题其实都得不到解答。
鸡汤文里说人生就是在坚定不移地追寻梦想,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人生就是见招拆招,哪有资格去追寻梦想,只想将眼下的生活安顿好。
命运没有因为现在是凌晨三点就暂时放过任何人,在急诊大厅里无时无刻没有急匆匆的担架穿行,无时无刻没有心急如焚的家属狂奔,所有人都为了两个字——救命。
第二个病人是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26岁,病情不明。
被发现的时候,年轻人的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了,从救护车上就开始有医生不间断地进行心肺复苏,但所有的医疗措施都已经失效了。
年轻人的身体正在一点点变冷,在明明人满为患的医院大厅里,我只能听到医生急促的喘息声,和家属极力克制的哭泣声。她应该是年轻人的母亲,一个极度悲伤,险些昏厥过去的中年女人。
“我们尽力了。”满头是汗的医生羞赧地站在那位母亲面前,他和那位母亲一样,拼了命想要救回年轻人的生命,但往往世间事难以如愿。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对医生最好的描述。
这一刻,大厅里听不到任何一丝声音,在场的所有人都用沉默来送别一个年轻的灵魂。
明明知道医院里最常见的便是生离死别,我们也总觉得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去接受每一场离别,但当离别真的来临时,我们还是猝不及防。
在送别自己的孩子后,那位母亲拨通了远在他乡的丈夫电话。
“喂,你回来吧,我想你了。儿子图个阖家幸福,但往往为了幸福,这个家总需要有人散落天涯。”
再见面时,已难相逢。
在没有遇到童童之前,我把这些年经历的所有折磨都当做是天意如此。
自己的运气很差,所以才会生活多磨难。
而在遇到童童之后我才发现,即便是像我这样屡战屡败的人,也有着别人梦寐以求,却永远也无法得到的东西。
童童是我遇到的第三个人,一个才3岁的白血病患者。
刚刚化疗结束后的童童陷入高烧引发的深度昏迷,伴随着血压的急剧上升,瘦小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起来。
“童童,童童……”
绝望的母亲声嘶力竭地跪在地上磕头,额头与冰冷地板撞击后发出来的咚咚闷响,在医院大厅里显得分外刺耳。
“妈妈不求你成名成家,妈妈只要你平安……”
以前总觉得健康长大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来到这里后才发现,自己能平安无事的长大成人真的很幸运。
因为未曾经历过苦难,所以才觉得生活多磨难,我们总觉得人生太难,其实着实幸运。
《寒风吹彻》里说:落在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到。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里,孤独地过冬。
天边已经渐渐泛白,深夜的人间即将隐去,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将带上伪装,为了家人,为了生计,为了自己,拼命生活。
虽然所有人都在强颜欢笑,但所有人都在奋力前行。
简书作者
- 梁思退 -
“ 不务正业的伪文青,艰难度日的日语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