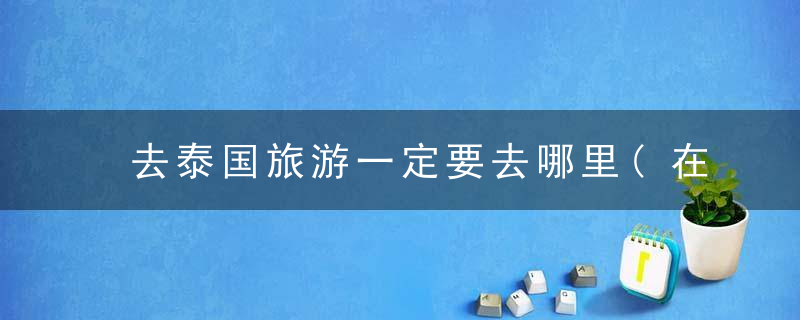我为什么怀念八十年代的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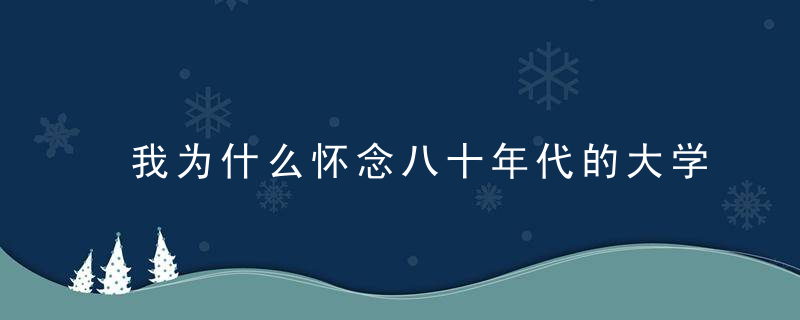
现在的大学里普遍存在的对学生过于关心并且过于宽容的现象,其实是让学生“返老还童”,把他们“幼稚化”了。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生
还有人说,我们生活的社会是个犹如全景敞视监狱那样的社会,因为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电梯里,举目可见的像麻雀一样密集像独眼的猫头鹰一样专注的探头随时提醒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我们已经变得比照相机的镜头还要透明。
我觉得他们说的都对,可我很想再补充一句,我们现在所生活的社会,还是一个呵护过度的社会。
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人都被过度的看顾,过度的保护,因而在失去自我的同时,也失去了犯错误的权利,这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弱不禁风,变得幼稚,软弱,变得奴性,甚至卑琐。 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让人深思。1
前一阵子,我所工作的大学的某个学院的老师发现有几个学生经常缺课,我本来以为只要找这些学生谈谈提醒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他们缺课是有合理的原因的,并且不违反学校规定就算了,如果是故意缺课并且违反了学校规定,那就按规定取消该生这门课的成绩就是。
大学生都是二十岁左右的成年人了,他们应该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一直觉得,大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不仅是上课考试这么简单,遵守学校的学习纪律乃至违反纪律后承担由此造成的处分,也就是自由的犯错误和自由的纠正自己的错误,也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学习,甚至是一种更重要的学习。但没想到负责的老师们却如临大敌,又是找这几个学生苦口婆心的谈话,又是动员他们的家长连线学生直接训话,同时也来做任课老师的工作,希望能够给予旷课的学生宽宥以不使其没有成绩等等,可谓呵护备至,不一而足。 但知道这个情况后,我却有点哭笑不得。一方面,我为本校的老师们对待学生的真心爱护感到钦佩,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们无意中也在某种程度上娇纵了这几个学生,让其得以堂而皇之的逃避自我应该担负的责任,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里普遍存在的这种对学生过于关心并且过于宽容的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让学生“返老还童”,把他们“幼稚化”了。
我记得很久以前读过一篇关于清华的陈岱孙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的轶事。一次,有个学生因为考试不及格,托陈先生的一个朋友写了封信,然后拿着这封求情信去找陈先生,试图让陈先生放他一马,给个及格分。谁知陈先生看也不看一句话不说就把这封信当着学生的面撕掉了。那个学生从陈先生的这一举动中,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不敢再纠缠,转身老老实实地离开了。
陈岱孙先生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神话,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同学们考试该不及格就不及格,该留级就留级,甚至该退学就退学。好像没有哪个同学不及格了,自己还敢去找老师理论,并且还有老师去为其代言,以让其通过的。2
现在,经常有学生以出国或工作为由,来向老师索取更高的分数,我自己就不止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息,每次我都感到很惊讶,难道你出国不是更应该好好学习吗?而且,你的考试成绩不好的责任为什么要老师来承担而不是自己承担呢? 这也许是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的大学的原因,尽管那时候的大学没有宏伟的教学楼和图书馆,也没有舒适的宿舍,更没有这么多对学生关怀备至的老师,可那个时候的大学把大学生当成大学生来看待的。学生在学业上出了问题,只要不是根本性的要死要活的问题,都是由学生自己独立承担的。那时绝大多数同学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微信,所以老师有什么事也不会去找家长,现在的大学,却把大学生当成了小学生,大学老师也动不动像对待小学生那样一有事就去找家长“告状”,很多家长也把大学当成一所呵护自己子女的幼儿园,却忘记了自己的孩子早该“断奶”了。 大学生们因此也真的变成了小学生,甚至变成了幼儿园里动辄流鼻涕拉大便都要哭着喊着让老师来给自己擤鼻子擦屁股的小孩。这也是让我感到多少有点不可理喻的一件事。 对于大学的教育,我很喜欢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杜威先生的教育思想。 1919年,胡适在《实验主义》这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位“教师的教师”对于学校的观点,那就是学校就是社会,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不仅是所谓的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开始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简单说来,教育即是生活,并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 也就是说,一个人念大学不是为了将来谋生学个本领那么简单,从踏进大学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开始“谋生”了。
3
当然,大学只是社会的缩影而已,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同样处于这种过度呵护的状态。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呵护过度的社会,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紧张不已,唯恐有什么变化和动静。而且如今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整个社会好像总是处在一种让人精神紧张的状态之中。 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忏悔录》里曾经讲过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段子。他有阵子因为生了个小病,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就开始狂读医书。可是他看着看着,逐渐开始怀疑乃至相信自己也得了医书上所描述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疾病: 我每读到一种疾病时,就认为这里说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研究了这门不幸的学问,我也会成为一个病人的。由于我在每一种病症中都发现和我的病相同的症状,我就认为自己什么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为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我觉得,从卢梭的这段话里可以找到我们当下的社会和大学的问题所在,那就是得了“治病癖”。其实学生也好,社会也好,本来是没有那么多病的,即使真的有什么小病,大多是不治疗也可以痊愈的小病,哪怕就是大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治疗一下就可以了。
卢梭
可是,现在我们的大学也好,老师也好,社会有关的管理部门也好,就像卢梭所说的那样,因为有点小病看了太多的医书而不知不觉得了“治病癖”。大家总是疑神疑鬼不说,本来没病的也会想出病来以至于生产出病来去治疗,以满足自己的“治病癖”。 这就像卢梭一样,他甚至怀疑自己的病的根源是源自心上长了一个肉瘤。最后,冷静下来后,他自己也对此感到荒诞不已。所以,我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并不在于大学生和社会,而在于我们的大学和社会的机制与文化得了卢梭说的“治病癖”。而我们的大学也好,社会也好,将来很有可能不是败坏于可能的疾病,倒是十有八九可能受损于过度治疗甚至是没病找病式的治疗,也就是卢梭所说的“治病癖”。
其实,之所以大学和社会会发展到这一步,问题还是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机制不相信人有自己抵抗疾病的能力和权利所致。我总觉得,一个人应该有生病的自由和生病后治疗的自由,甚至有不治疗的自由,真不需要防患于未然式的治疗,更不需要卢梭讲的“治病癖”式的治疗。4
一个人的健康成长,实际上是离不开疾病的,但不能因为怕得病就不让人生病,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治病癖”就让健康的人胡乱吃药。因为不得病没有抵抗力,反而更容易得更大的病,以至于很有可能有病时一命呜呼。胡乱给人吃药,更是可能把没病的人“治死”。 鲁迅1925年在自己的随笔《看镜有感》里谈到,中国的文化在汉唐时代因为心胸开阔,魄力雄健,非常“闳放”。所以,高度自信,是勇于吸收和接纳国外的文化的,比如铜镜上的装饰花纹就有很多就直接采自海外的动植物,如汉代装饰有洋马和蒲桃的“海马葡萄镜”等。可到了宋以后,因为国力衰颓,开始谨小慎微,怯于吸收海外及异族的文化,铜镜上各种“藻饰”就少多了。因此,他特别谈到不同时代的人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像汉唐那样国家强悍时对外来的东西是“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的,可是当国家沦落比如像宋以后那样没有自信的时候,就有点病态了。 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彷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他更是把这种对于外来文化的态度比做人对于食物的态度: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我想,国家如此,文化如此,学生也如此。反过来,学生如此,文化如此,国家也会如此。而显然,一个人也好,一种文化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没有一个好胃口,没有一个开放的好胃口,没有真正的自信,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活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