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

EYEONHISTORY
《明皇试马图》 (唐)韩干
大唐开元二年(714年),海内安宁。
春天在北方边境击败了突厥入寇,盛夏季节西天竺国又遣使来献方物。
在遥远的南方海滨,安南市舶使周庆立和波斯僧广造奇巧,想进献给皇帝以赞颂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当时即位才三年、正励精图治的唐玄宗却拒绝接受。
这一看起来平静的一年,却可能标志着一个重大的转移:中国的对外交通正在逐渐转向海洋。
周庆立就是中国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关官员,在他之后,一个繁荣的海外贸易体系已渐渐成形。
从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对外格局是在此前历史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自张骞通西域以来,中国对外交通的重心长期是面向西域的陆路。
尤其在西晋覆亡之后的五胡乱华时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着不同的语言,沿着黄沙迷漫的丝绸之路跋涉而来,其结果不仅促成商品贸易的交流,外来文化(尤其佛教)还给中国文化开辟出全新局面。
与之相比,当时尚未全面开发的南方在三国孙吴时期才开始发展海外交通,受国力和技术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并,南方在对外开放程度上仍与北方相去甚远。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于北方豪族,定都长安也使他们无疑更着重放眼内陆亚洲;作为陆路丝绸之路终点的长安由此成为当时一座国际性大都市。
那时输入的外来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担这一交流职能的则主要是中亚的粟特胡商。
粟特人不仅经商,由他们带来的美术、音乐等艺术也深深影响了唐人,盛唐时代也是粟特商人两三百年来在中国活动所达到的顶点。
唐三彩中的坐在骆驼上的胡人,杜甫有诗云:“胡儿掣骆驼。”
但一种新的趋势也在此时逐渐浮现:南方的海外贸易小传统已经开始复兴。
当时闽粤一带仍被普遍视为遥远的蛮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则天时期,广州已是南海边一个重要的国际商港:
“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旧唐书·王方庆传》)这里说的“昆仑”,就是东南亚一带熟习水性的土著。
到天宝九年(750年)鉴真途经广州时,已看到广州海面上“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唐大和尚东征传》)。
因此,开元四年(716年)韶关人张九龄奏请开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岭新路,以充分利用岭南对海外交通的优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赡江淮之求。”(张九龄《开大庾岭路记》)
虽然其中不无文学夸张的语气,但此路辟通为“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后,确实极大地促进了岭南与中原的联系,重塑了岭南的商路。
由此北江开始日渐繁忙,而以前通往广西的商路逐渐废弃(叶显恩等《广东航运史》),这又推动了海外贸易的发展。
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客使图》。右边的三位使节,也许分别来自东罗马、新罗、中国东北部。
文献中最早可见的中国海关官员,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即开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庆立。
中唐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虽然著作的时代略晚,但也可见安南和广州长期是南海边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乱(755-763年)加速了这一从西域到南海的转移过程。
说来讽刺,安史之乱的两个起事者安禄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统,但正是他们不成功的叛乱终结了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
在长期动荡之下,驻守西域的唐军内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鹘和吐蕃势力之手,中原势力从此绝迹于中亚长达一千年之久;
而没有了帝国维护陆路交通的安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渐不复当年盛况,更不必说由于叛乱者的种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后也遭到了中原汉人的敌视和歧视。
江淮以南的南方当时并未受战火波及,由于北方藩镇割据,唐朝越发依靠南方在财力和人力上的供给以支撑摇摇欲坠的帝国结构。
敦煌壁画《盛唐海船图》。海上贸易在唐朝被称为“市舶”,盛唐时的渔船,其桅、帆、篙俱全,但船体并不大。
在安史之乱结束的广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广州设立市舶提举司,掌征收外贸商税、检查来往船只、收购专卖品。
之所以设在广州,原因也很简单:自秦汉以来的数百年里,广州一直是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正如长安和洛阳是陆路丝绸之路的终点。
当时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面远比现在开阔,广州是一座海滨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达中国的第一个港口。唐朝继续以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态度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收并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唐以后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宝石、白鹦鹉等陆续从海路输入,甚至奴隶的来源也出现了转移。
早先是粟特人口贩子转运的胡人妇女,而现在则出现了南洋来的皮肤黝黑且熟识水性的昆仑奴,他们成为唐传奇中新的角色。
从8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样经历了一个“南方化”的过程:
来自南方的各种文化因素(如饮茶习俗)开始扩散和弥漫到全国,而南方的闽粤航海传统自此得以全面兴盛,逐渐取代西域通道而成为此后一千多年里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改变了中国的外贸结构和文化取向,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海外贸易网络的形成
市舶提举司在763年的正式设立标志着一个海洋中国的兴起,这本身也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已成长到不容忽视的程度。
唐代广州的海路贸易,分东西两道,东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则是向西南到东南亚、印度、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
原先承担驮运各种珍奇贩运到长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鹘等中亚的胡商,而8世纪中叶以后到广州等地从事贸易的外商则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
据说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曼苏尔(745-775年在位)曾说:“这是底格里斯河,从这里到中国没有任何障碍,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从海上运来。”
当时曾有大量来自西亚的穆斯林人口生活在广州,建造起怀圣寺、光塔(早先被称为“蕃塔”)。每年五六月间西南季风到广州时即有人登顶宣礼,并在夜间点灯(塔高达615尺),可以作为航道灯塔来导航,此后在几个世纪里都是海船从珠江口进入广州城时最高和最容易辨识的航标。
到德宗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锷任岭南节度史时,广州参与海外贸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发十余艇”,且“周以岁时,循环不绝”(《旧唐书·王锷传》)地加入到商贸活动中去。
当时经“广州通海夷道”来贸易的国家据说不下一百个——柳宗元曾记载:抵达广州的商人“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厦(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岭南节度飨军堂记》)。
晚唐时聚居在广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数量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当时广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为中国商货与阿拉伯货荟萃的地方”。
盛唐.阿拉伯商船在广州 冯少协画作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逐渐关闭,原本依靠转运贸易致富的中亚城市开始慢慢走向衰败。与之相反,在盛唐时还被视为蛮荒异域的东南亚一带,接过了中国与印度洋沿岸的贸易中转,许多港口因此而发展了起来。
广州远离任何一个统一政权都城的独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时代都保持开放而不影响国家根本政策。
这又使得南方的经济愈加获得发展,因为自唐宋时代起,这些面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长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兴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国内贸易为主。
在这个海外贸易网络中,中国人逐渐占据上风并成为主要的承担者。这与此前的陆路对外贸易截然不同:
陆路贸易的承担者通常是粟特、回鹘等胡商,因为从长安到中亚、拜占庭、欧洲的道路极为漫长,许多路段地形复杂且盗匪出没,是一种不断在中间商之间分段转运的贸易,不善控制骆驼及熟习多种语言的汉人很难从事这一贸易,因此往往是游牧民族居中联系并控制相关的商路。
海上贸易却对造船、驾驶技巧等技术能力提出较高要求,且海路相对安全——它只需要一系列和平开放的港口。
在早先的陆路对外贸易中几乎没什么知名的中国商人,更别说移民国外了,而海路贸易最终却使中国人深深介入东南亚的经济结构,以及数百万中国人“下南洋”。
商队在陆地行走速度较慢,骆驼所能驮的货物重量也远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抢劫的风险却远高于海上被海盗抢劫。
因此在火车发明之前,陆路商队运输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只有非常贵重的物品才能负担得起远程陆路运输的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昂贵的外国商品通常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将之视为一种身份象征,其经济意义微不足道。
黄埔商港 冯少协画作
但海路则不同,负载重的船只反而不易沉没,空船还需要用大量石头或瓷器等压舱,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货(兼有压舱和出售两重用途)也得以进行贸易交换,而这些是平民也可以消费的。
中唐以后闽粤商人将大量中国货物(瓷器、茶叶、丝绸等)运载到海外,并使东南亚等地的经济活动也为供应中国市场而组织起来,最终推动了区域性工业布局的形成。
此外,海外运输还对造船技术、航海技术等各方面提出了技术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关科技进步。
西方学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这一术语来描述中古时期这一交流网络的形成,异域货物、思想观念、文化力量等逐渐出现一个横跨各洲的联系。
那是一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中心——唐朝中国不仅是这个贸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还是其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
全球史学者Jerry Bentley认为,在全球性互动中,三种主要进程(大规模移民、帝国的建立和远程贸易)具有“超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疆界的重大意义”,不难看出,这三者在海洋中国的时代同时在进行。
失去的机会?
现在提起唐朝,人们常常将它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曾达到过的一个巅峰,而与之相连的则是一个外向、自信、开放、文化多元的形象。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唐朝在对外交流中的行为,塑造了今天人们所感知到的“盛唐气象”。
但“巅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达那个顶点之后,发现很难在那里长期停留,事实上唐朝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国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它不仅见证了辉煌、见证了变迁,也预示了此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成功与失败。
人们或许会遗憾:为何中国未能在一个国力强盛的时代,趁着转向南海的历史机遇,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
但事实上,如果说那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是一个必然会失去的机会。
唐代海路贸易确实催生了一个颇有希望的“海洋中国”,然而这种繁荣,与西欧海洋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而其背后运作机制则大异其趣。
荷兰画家紐荷夫笔下的十七世纪广州贸易盛况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在技术条件简陋的时代,是风险极高的行业。一旦有一批货物在海上沉没,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产。
因此古代诸文明中,无论是埃及、苏美尔、中国,最初都是神庙或宫廷垄断海外贸易——也只有这样财力雄厚的机构才能消费这些特殊商品。
在中国,自秦汉以降,皇帝一直竭力垄断对海外的贸易,早在西汉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购珠宝异物,所获利润也归皇帝的个人财库少府,而不列入国家税收。
现代人出于一种观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设立的提举市舶司视为中国最早的海关机构,但必须记住的是:它远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
唐代向海外贸易征收的市舶税,实际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说,海外贸易的繁荣,最终获得好处的仅是皇帝个人。
中国第一任海关官员周庆立之所以出现在《旧唐书·玄宗本纪》中,就是因为他和波斯人“广造奇巧,将以进内”——换言之,搜罗各种海外珍奇,想献给皇帝博取其欢心,以至于这种蛊惑皇帝的行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满。
位于广州五仙门的粤海常关办公楼,1931年改称为“粤海关民船管理处”。
研究海洋中国及东南亚贸易的史学家王赓武在《南海贸易与南洋华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任命”“往往独立于地方当局之外,并由宦官控制”。
这一内廷宦官主导海外贸易的传统一直沿袭到郑和时代都没有变化过。在这种情况下,海外贸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财库密切相关,却不能增加国家财政层面的财富。
这并不是一种企业行为和商品经济,从中是绝无可能萌生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更别说使整个国家向海洋国家转型了。
如果当时能向一个海洋国家转型,那必须有一个高度活跃的民间海外贸易为基础,并把整个国家当做一个贸易公司来经营(正如威尼斯、荷兰之所为),但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唐代的官方海外贸易毫无意义,它至少提高了远程贸易量,而这本身也标志着跨文化互动规模的增长。
但我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唐代的“开放”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它和历代一样严格限制内部居民流动:
行旅往来于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验官府签发的通行证,更不许居民私自出国(所以玄奘和鉴真两位大师按唐代法律都属于非法出境);它也屡次禁止民间参与海外贸易,只是闽粤一带天高皇帝远,这一禁令收效甚微。
唐开元20年石染典“过所”,相当于今天的护照。
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能得以逐渐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它们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边缘位置,这使得当地社会能打破官方垄断的企图,灵活地自我调整以加入到海洋贸易的活动中去,但代价则是他们的活动常常无法得到官方的支持。
这有点类似《东南亚贸易时代》中所提到的东南亚在17世纪的悲剧:
由于权力和贸易密不可分,统治者和大臣不容许一个拥有自己声音的、独立于宫廷之外的大商人阶层存在,加上西方列强的竞争和打击,遂使当地无法向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转型。
应该说,中国并不曾“失去”那个机会,因为它并不曾有过——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这一历史,则不失为中国人一个反思的契机。
12
唐代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
八世纪前中叶,唐朝与七十余个国家有外交往来。唐贞元年间,宰相贾耽在《海内华夷图》记录了几条主要的对外交通路线:
一、营州(今辽宁朝阳)入安东(今辽东)道;二、登州(今山东烟台)海行入高丽渤海;
三、夏州(今陕北横山)塞外通大同云中(今山西大同)道;
四、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入回鹘道;
五、安西入西域道;
六、安南(今越南河内)通天竺道;
七、广州通海夷道。
其中第七道“广州通海夷道”海洋航道始于广州,沿着传统的南中国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
如果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途经九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航期近百天,是八九世纪世界最长的远洋航线,也是东西方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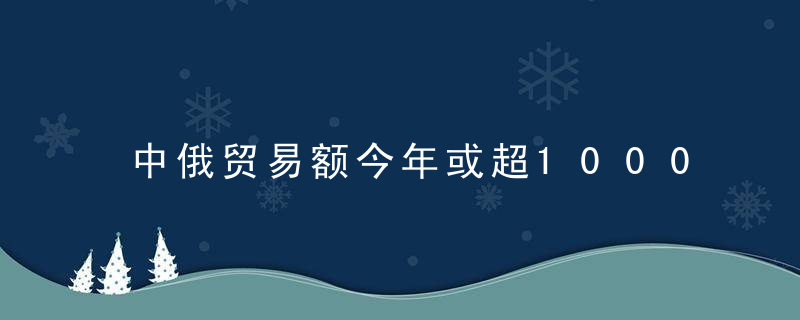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