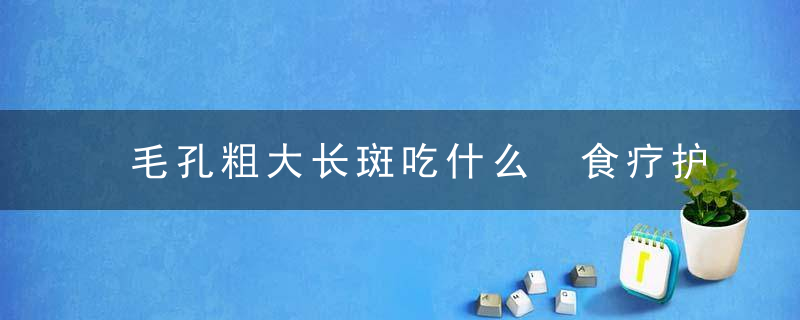论现实与想象在史蒂文斯诗歌中的互动

中国论文网 /4/view-10268349.htm
关键词:史蒂文斯诗歌;现实;想象;互动;最高虚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9)04-0069-03
美国20世纪著名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诗歌中的“现实一想象情结”一直令评论家们感到困惑。正如他自己在一封信中所说:“如何在想象的事物和真实的事物之间取得平衡……一直是令我烦恼的事情”。他所思索的想象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其实也是他对于诗人的使命和诗的功用的终极思考。在史蒂文斯生活的年代,自从尼采大胆宣称“上帝已死”以来,整个社会面临着巨大的信仰危机。人们不再相信任何绝对的权威,那么曾被雪莱满怀激情地颂扬为“未经承认的立法者”的诗人将往何处去?庞德提出“变新”的主张,他的尝试为现代诗歌做了有益的探索。艾略特发表诗作《荒原》,意在以现代生活的现实画面警醒世人。同为诗坛巨擘的史蒂文斯则坚定地相信“当宗教再也不能令人满意时,诗歌应该取代宗教的位置”。他相信在诸神缺失的时代,诗人应当使自己的想象成为众人的想象,成为照亮普罗大众的一线灯光。“简言之,诗人的作用是帮助人们生活。”。因此,他提出诗是“最高虚构”,即诗人运用想象对现实进行美感观照,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人们承认这是一种虚构,而且可以从中得到满足。同它比起来,最初的现实反而显得不真实。“最高”,表明了史蒂文斯对诗的绝对信心;“虚构”,又表明了这不同于初始现实,是想象加诸其上的现实。史蒂文斯自己说过:“我的目的是建构一种最高虚构……现实与想象的关系,相对于这个中心主题而言,只是边缘话题。”在史蒂文斯的整个诗歌体系中,最高虚构占据着中心位置,因此,我们应把他的现实一想象情结纳入“最高虚构”中考察。现实和想象作为“最高虚构”的两极,缺一不可。
史蒂文斯在《高调的女基督教徒》中第一次提出“诗是最高虚构”。诗中的说话者对女基督教徒信奉的宗教信念进行了诙谐的调侃。对于上帝的信念也不过是人创造的,那么诗人创造的诗作为最高虚构同样可信。当然,虔诚的基督教徒听了这话是会皱眉的,不过说话者不在乎。“最高虚构”一出场就被诗人赋予了与对上帝的信念同等的地位,这符合诗人对诗歌功用的期望。在《关于最高虚构的笔记》中,诗人继续阐发了作为最高虚构的诗歌的三个特点:它必须是抽象的;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提供愉悦。为了达到这三个目的,现实和想象在史蒂文斯的诗歌中似乎在不停地展开互动,正是由于它们的共同作用,“最高虚构”才能实现。
想象历来被视为诗人自由驰骋的天地。想象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卑微为崇高,化渺小为伟大。华兹华斯认为想象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1)赋予、抽出和修改的功能;(2)造形或改造的功能;(3)加重、联合、唤起和合并的功能。诗人的想象所及之处,生活中的平常事物即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新的形体、新的组合。史蒂文斯认同华兹华斯的观点,这一点从他的早期诗歌《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中可见一斑。诗人从多个角度对黑鸟这个想象的精灵进行观察:黑色代表夜晚、死亡、不祥,十三则是《圣经》中耶酥被出卖的日子,它们在西方都被视为禁忌。华莱士・史蒂文斯把黑色和十三并列,偏离了读者的预期,这首先就预示了作者崭新的视点,同时使这两样事物具有了新的含义。
在《观察黑鸟的十三种方式》中,诗人分别把黑鸟置于雪山、河流等背景中观察,运用想象的美感观照,使读者感到他看到的既不是现实中的黑鸟,但又确实是黑鸟可能具有的种种形态。在第一篇中,诗人把黑鸟从二十座雪山的背景中疏离出来,再把黑鸟的眼睛置于镜头前,黑与白、静与动、远与近,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幅对比鲜明的图画。英文中的“眼睛”与“我”同音,暗示着这既是黑鸟的视角,又是诗人自己的观察。第二篇中,诗人转而描写自己:“我有三种思想/像一棵树/栖着三只黑鸟。”。这是一幅超现实主义的画像,乍看上去,具有怪诞荒唐的特点。我们将它与《我叔叔的单孔眼睛》中第十篇比较:“……我是自由民,和众人一样。/我不知道什么银红、金朱的果实。/但我毕竟知道那棵/和我的心灵相似的树。/它高高地耸立着,枝头/常有鸟群飞来飞去。/鸟飞走后,枝头仍是树的枝头”,就可以知道诗人谈论的仍是想象与现实的关系。一棵树是单调的,没有黑鸟(想象)的栖息,树(我)最终是荒凉平瘠的,因为鸟具有传播树种的功能。三只黑色的鸟,还让人想到莎士比亚《麦科白》中荒原上的三个女巫,神秘、邪恶、诡魅,以及她们的咒语:“手携手,三姊妹,/沧海高山弹指地,/朝飞暮返任游戏。/姊三巡,妹三巡。/三三九转蛊方成。”这三只黑鸟,既可以是生命力的象征,也可能播下邪恶的种子。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诗人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的空间。
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世间最重要的关系,诗人的广角镜在第三篇里同样照射到了这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一个整体”,诗人说,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立即补充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一只黑鸟是一个整体。”这既是一种补充,也未尝不是对前面所说的话无意中的否定:有了黑鸟这个想象的精灵,男人和女人的世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完整。
第七篇中,诗人质问“哈达姆瘦弱的男人”:“你们为什么梦想金鸟/你们没看见黑鸟/在你们身边女人的脚下/走来走去?”金鸟明显地暗示着叶芝的《驶向拜占庭》中那只“使渴睡的皇帝清醒”的金鸟,它“栖息在一根金枝上,/为拜占庭的贵族淑女们/唱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歌”。叶芝在这首诗中歌颂的是艺术永恒不凋的美。华莱士・史蒂文斯觉得男人们只空想艺术的永恒境界,却错过了身边的黑鸟,忘了想象才是使现实永驻的条件。缺乏想象的男人是“瘦弱的”。
在本诗的终结篇中,诗人又把黑鸟带回雪景中,似乎经过一个轮回,季节又回到了冬天。但第一篇中诗人是在一片肃杀之中凸显黑鸟的生气,而此时黑鸟“栖在雪松枝上”,与雪、自然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如他另一名篇《雪人》中描写的:“听风的人,在雪地里聆听,/人与物化,凝视/乌有的虚无,实在的虚无。”黑鸟的美学观照,使诗人获得了一种纯粹的知识。黑鸟从与二十座雪山的对峙走向与雪的融合,而且“雪还会下个不停”,这说明在以多种方式证明了黑鸟的存在后,黑鸟与雪不再是对立关系,而在逐步走向整合。
诗人以十三种方式观察黑鸟,验证了第八篇中的“但我也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都与黑鸟有关”。黑鸟无处不在,无论是它“啼鸣时,/还是鸟鸣乍停之际”,都让人感到它的存在。华莱士・史蒂文斯曾说过,“诗的主题是诗”。在此诗中,黑 鸟作为想象的象征,本身便是通过奇异瑰丽的想象表现出来。黑鸟既是被观察者,又是观察者;它既是想象的化身,本身又需要被想象出来;它既是人类经验的观照对象,又是人类经验的集合体。不管怎样,作为想象的精灵,就算它飞出视线,也会在人心里泛起涟漪。
史蒂文斯虽然十分推崇想象的作用,但实J际上他对现实与想象关系的思考比这深入得多。一方面他大力弘扬想象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对想象的作用加以限制。他在书信中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想象来源于现实,一旦离开现实,它就不具备任何价值。”他有时被称为“想象的诗人”,有时又被称为“现实的诗人”,皆因他的诗歌中想象和现实互动频繁。他说:“有时我很长时间内主要信仰想象,然后,没有任何原由地,转而信仰现实,并且只信它。但这两样东西不停地在我面前出现,这正是我要的结果。”
想象与现实的关系,是他一直想研究、探讨的问题。有时想象似乎取得了无限的权利,有时似乎又在现实面前低下它高傲的头颅;有时想象是一个自足的系统,有时却又离不开现实。反映在他的诗歌作品中,想象和现实似乎在时刻不停地展开互动。
想象是“这想象的世界里/唯一的真实”,缺乏想象的人只是“行走的幽灵”,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这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十点钟的觉醒》里表达的主题。“那些房子里/有穿白睡衣的幽灵出没。/没有绿色的,/也没有紫色镶绿边的,/也没有绿色镶金边的,/也没有金色镶蓝边的。/没有一个是陌生的,穿着绣花锦袜/束着珠饰彩带。”在绿色、紫色、金色、蓝色、绣花锦袜和珠饰彩带的反衬下,“白睡衣”显得特别苍白、没有生气。史蒂文斯惯用否定语,其“没有”正衬出“有”的必要和紧迫。这些人过着平庸、苍白、拒绝陌生、没有任何惊奇的生活,只有老水手凭借想象的力量在平庸乏味的生活里找到了色彩与勇气:他梦见在“红色的天气里/捕捉老虎”。现实是残酷、痛苦、了无生气的,这在《没有负鼠,没有面包片,没有品尝者》中体现出来:“田野结冰。树叶干枯。/这束光中一片凄凉。/苍白的风中,残损花梗的胳膊/没有手。残损的枝干/没有腿,也没有头颅。/头颅中压抑的哭喊/不过是舌头的运动。”一月即将结束,但冬天仍未过去。虽然偶有雪花闪烁、落叶旋舞,但始终只能“吟诵着孤独的虚无,/寒风残忍的空洞”。在这样一片荒凉中,更突出想象的重要性。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另一首诗《单调的感觉》中写道:“而缺乏想象本身/需要被想象。”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前者强调现实的凋敝零败,后者则是对此作出的回答:“这一切/需要被想象,作为无法回避的认识,/作为一种必须,需要被询问。”想象是一种必须,一种需要,否则我们无法抵制现实的萧索。
但是,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想象并不是脱缰的野马,任由它肆意乱闯。想象的目的并不是要拔高现实,因为他深知,在他所处的时代,任何拔高、美化、虚饰现实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他看来,现实才是诗歌坚定的土壤,离开现实的想象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他接受现实的不完美,并忠实地表现这种不完美。在《城堡》中,诗人来到城堡,只见床铺空空,他发出了“真倒霉”的哀叹。“床铺空空”,正是空洞现实的剪影。诗人失望之余,尝试以魔法解脱,却只找到“苦涩的眼睛,冷冰冰的手掌”;试图在书本中得到慰藉,却只“照亮一两行冷酷的诗句”;他拉开窗帘,有的是“微风无边的孤寂”。他开始重新思考,现实中见到了意义和秩序:“真好,床铺空空,/窗帘整洁,一动不动。”从质询到肯定,从失望到赞美,诗人对于现实的态度有了本质的改变,正如他在《我们气候的诗》中所说“不完美是我们的天堂”,“我们自身本来就不那么完美”。英语中,“建在空中的城堡”指白日梦,“城堡建造者”即空想家。诗人以《城堡》为题,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想象恰恰需要建立在不完美的现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只能是空中的城堡。
因此,华莱士・史蒂文斯主张想象与现实是有机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想象赋予现实形体与秩序,但它不能完全替代或改变现实。在《坛子的轶事》中,“凌乱的荒野”影射现实世界,“圆形的坛子”则寓示艺术与想象。想象的美感观照使凌乱的荒野不再荒凉,“圆形的坛子”君临四界,给无序的荒野带来形式与秩序。但想象毕竟不能取代现实。即使在坛子所带来的圆满极乐中,诗人仍然冷静地想到“它不曾产生鸟雀或树丛,/与田纳西别的事物都不一样”。而在《两只梨的研究》中,诗人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这是“教育学小品。/梨子不是六弦琴,/裸女或瓶子”。诗人坚决摈弃任何浪漫主义的将梨子比做上述事物的可能性,说梨子就是梨子,“梨子不象任何别的事物”。然后诗人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画了一幅两只梨的静物画:“黄色的形体/由曲线构成。/鼓向梨顶。/泛着红光。”诗人选择使用平实的语言,而不是用瑰丽的比喻来描写两只梨子,甚至不错过“蓝色的斑点”、“干硬的叶子”、“绿布上的湿痕”。诗人眼中的梨子是不完美的现实,却也正是诗人的天堂,因为只要具备了“冬天的心灵”,就能够“领略松树的霜枝,/枝头白雪皑皑”。
史蒂文斯的众多作品中都留下了他对于想象和现实关系的思索,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的:“两种相反性质的事物似乎总是/相互依赖,如男人依偎着/女人,日依偎着夜,想象依偎着/现实”。但史蒂文斯并非职业诗人,他在一间保险公司任副总裁,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常有人对他商人和诗人的双重身份大呼惊奇,他自己倒是不以为然,觉得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晚年承认自己务实的一面承继于父亲,而想象的一面来自于母亲。这种家承渊源也许可以解释他的现实一想象情结的由来。
史蒂文斯晚年发表的《内心情人的最终独白》反映了他关于诗人使命的思想。在这首诗里,史蒂文斯把他钟情一生的诗歌比做“内心情人”,她也许只是一条刚够裹身的披巾,但也能产生“一点暖,一缕光,一点力”,使我们捕捉到秩序、整体和知识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是模糊的。这首诗和《桌上的星球》与《不是事物的概念而是事物本身》一起,是对他诗歌生涯的总结。在前一首诗里,史蒂文斯假借小精灵爱弥尔的语气:“爱弥尔很高兴,因为他已写完他的诗。/它们怀念过去的时光/或抒写他喜欢的东西。”在后一首诗里,诗人在冬天刚要过完的时候,听到一声“怯怯的啼鸣”。这啼鸣和他早期所写的松林里那只好斗公鸡的大贼大叫相比一点都不起眼,但在诗人看来,它传递了“关于现实的新知识”,改变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诗人以自己的秩序赋予了现实世界新的秩序,从这一点看,诗人应该为自己感到自豪。正是因了诗人的“超级虚构”,《星期天早晨》中的“她”才能在冥想中,以现实的召唤抵制了宗教的热情;而在《冰淇淋皇帝》中,现实战胜了死亡:“让是作似乎是的终曲。/唯一的皇帝是冰淇淋皇帝。”。在诗人所处的变幻莫测的时代,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