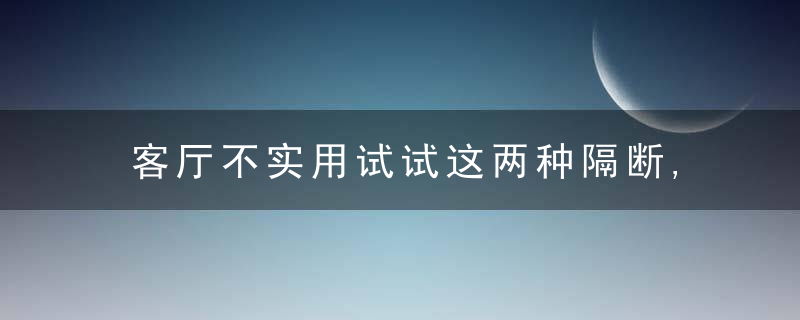有些亲戚为什么走着走着就没了

1/
俗话说:“亲戚三代,户族万年。”
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一个人的姓氏与根是背弃不了的,而有些亲戚走着走着就淡了,有些人交着交着就信杳无踪了。
2/
第一家走淡了的亲戚,是简门的姨妈家。姨妈姓戴,是我姥姥大姑子的女儿,妈妈叫她表姐,所以,正确的叫法,我们这些晚辈应该叫她表姨妈。当时年龄尚幼、口齿不清的二弟,更是叫她“野妈”,直到他长大成年后,人们还拿这做话柄笑话他。
我们那里走亲戚还有个别称,叫“走人家”。孩提时代,除了盼过节,就是能有机会和大人一起“走人家”,因为,那意味着有好吃的。
走简门的姨妈家,都是学龄前儿童时的记忆。一共去了几次,现在已没有明晰的印象了,只是记得和姥姥一起的那次。
记忆中的姥姥,是个慈善的老人,三年困难时期,响应国家号召,带着一双儿女(我的舅舅和妈妈)从镇上下放到我们村。结果,舅舅饿死了,姥姥只有跟着我们一家人生活,直到老死乡下,也没能再回到镇上。
简门属晏河乡,从黄围孜到简门得要趟过一条大沙河,所以,我们一般会选择在夏秋的水枯季节去。
因为有河相隔,所以去他们家走亲戚,也叫“到河那边儿”。
那时的感觉,从我们家到简门要穿过许多陌生的村庄、走很远的路,才能望见那片银白色的河沙滩。其实,那段距离并不遥远,也就七八华里的样子,可在儿时的脚下,却是难以超越的艰难。就如时间,此时已将我和简门阻隔得越来越遥远、模糊。
姨妈家就在那条大沙河边,屋后有竹园,左近就是在阳光照耀下白得耀眼的河沙滩,那些,都是我犯淘的胜地:竹林里的小鸟、细沙下的黑贝,还有姨父网网不落空的鱼虾……无一不是惊喜。
更大的惊喜,是来自大我许多岁的表姐。现在只记得姨妈家有两个表姐,具体叫什么名字,我是一点印象都没有的。感觉,她们并没把我当作男子汉,而是可以逗乐的玩偶。比如,她们洗澡时,大人们是一律要出门回避的,而我,却被她们留在院子里。她们洗澡用的是大大的木脚盆,倒入烧好的热水,就光着身子站进盆里,用毛巾往身上淋水……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么一丝不挂的女孩子,心中并无邪念。她们洗完后,又把我扔进她们洗过的脏水中,好一番折腾,弄得院子里到处都是水。
夜晚睡觉时,我也是和她们挤在一起睡的。睡不着觉时,就会在她们的肚子上爬来爬去的,表姐的皮肤是光滑而温暖的,那感觉,要比安静地躺在床单上舒服多了。
那年,我大概就是三四岁的样子,不知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难道,我真的是早熟晚醒型的男人?表姐们要是知道这点,打死也不会让我和她们同盆而沐、同榻而眠的。
后来,妈妈的姑妈去世了,两家人的走动也就越来越淡了。最后一次见到姨妈和表姐一家人,就是在妈妈的姑妈——我的姑姥姥的葬礼上。
3/
对于姑姥姥,我是没太多印象的,她以九十高龄去世,丧事办得像喜事一样,大家都是有说有笑地一起扎纸花、吊球。后来知道,寿高的人去世,是喜丧。
姑姥姥的家在戴榜,她除了有个嫁到简门的女儿,还有个生养了个儿子——我得叫他表舅舅。
小时候去表舅家,也都是和姥姥一起去的。因为,我亲舅早早就过世了,从血缘上来讲,她的这个姨侄就成了最亲的人了。
表舅妈很贤惠,每次我跟姥姥去她家里,她总会给我们留有许多好吃的。其实,那时农村穷,所谓好吃的,大多是鸡蛋、豆腐、挂面、油条啥的。但每次去表舅妈家,肉是会有的,有时是鸡子、有时是排骨、有时是老鸭,都是提前用土陶罐埋进灶窿的余烬里煨好的。开罐汤一定是倒给姥姥的,因为,开罐汤油大,香,觉得可以补补老人的身子。我不喝汤,只负责啃鸡腿或骨头。
另外,表舅妈家还有一样“小吃”吸引我,那就是她自己手腌的洋姜。
洋姜,又名菊芋、鬼子姜,是一种多年宿根性草本植物。其地下块茎富含淀粉、菊糖等果糖多聚物,可以食用,煮食或熬粥,腌制咸菜等。腌过的洋姜本来是一家人的下饭菜,但由于它富含糖分,入口脆甜,所以,每每成了我的零食。
表舅也是个很意思的人,他叫戴宏文,虽然是地道的农民,却有着一身书卷气——兴许,他是读过一些书的。所以,待我长大后,每次去他家,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计,坐下来,拧起他那根被摩挲得发亮的老烟枪,一边叭几口小烟,一边陪我聊聊人生啥的。
表舅老俩口健在的日子,每年我都会去他们家拜年。直到两位老人去世后,加之我工作去了外地,去往戴榜的这条路,也竖起来了。
表舅家有个儿子,我叫他义哥,也是一特殊人才,由于是独生子,从小倍受宠爱,家里一直供他上到高中。回乡后却悲催了,他不喜农桑之事,却对江湖充满向往。小时候感觉他像个话唠,每次相聚,话都被他一个人给说尽了。多年前我回老家时又碰到他一次,他竟然比以前更能说了,原来,这些年,他四处流浪,靠以给人算命为业,却也混了个小富即安的生活。
4/
小时候,路途最遥远的一家亲戚在万河。
万河只是豫南的一个普通小村庄,人们不会对它有什么特别感觉,如果,我告诉你从这个村子里走出来的一个人,你就会对它有些感性认识了——万河是原成都军区政委、万海峰上将的老家。
之所以和万河能搭上关系,主要是因为我的祖父。祖父是个旧式文人,做了大半辈子的墪师。在他的文墨生涯里,结交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就是万河的余竹泉先生。我没见过余先生,因为他仙逝得早,我只看到他和祖父之间的唱和诗,从中感受到两个人的惺惺相惜。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积累,即使是余先生仙逝多年,两家人仍如亲戚般走动。认真说起来,我们与万河,应该是朋亲。
余先生的儿子大名良将,我叫他余叔。余叔也稍通文墨,且学得一手木匠手艺,小日子过得还算平和。
有一年,我们家翻盖房子,余叔放下自家的农活,跑来我家一呆就是半个多月。因为他会木匠,大事小情,都是他在张罗。直到几间房子收拾停当,他才离开。
祖父健在时,每年都会去余叔家住上几天,一是上坟山上祭拜下老友,另外,也带上我们这些晚辈,以期将一份情谊传之久远。跟随祖父最多的,就是我这个长孙了。从我们家到万河得有二十多华里,每次都走得我腰酸腿软。中途,我们一般会拐进杨榜小学短暂休息,也给了那些年轻老师们向老先生请教的机会,这,也是祖父所乐于接受的。
祖父去世的前一年秋天,他还独自一人去了万河。那时,我在槐店中学教书,他竟又走了几十里乡路,来到我们学校。老家有种迷信的说法,人死前会“辞路”,就是到生前走过的地方再走走。没想到,一年后,祖父真就去世了。
祖父去世后,两家人的走动也就慢慢淡了。
年前,当年槐店中学的几个学生从老家来郑州办事,晚上相约一起小聚,竟然碰到了余叔的儿子克栋老弟。这真叫山不转水转,是亲都有缘。
5/
儿时常去的地方,还有个叫小姜湾的村子,只是,现在的记忆里,怎么也拼凑不出它的清晰形象来。打电话向父亲求证几次,才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曾经留有儿时模糊记忆的小村子。
简门往南两华里左右,就是小姜湾,同属晏河的程山村吧?
那里住有我曾经的亲人——我的姑奶。对于姑爷,我是没有一点印象了。姑奶比我祖父年长不少,记忆中,姑奶的牙不好,可能是因为缺钙吧,我能记起她的日子,她的牙齿也掉得差不多了。记得有年冬天,姑奶来我们家,她吃得最多的东西有三种:一是锅巴,得用灶火把锅巴炕得金黄酥脆,然后用捣蒜用的那种陶器把锅巴捣成细碎的面粉状,姑奶会就着茶水吃下;其二是红糖水泡油条,油条得要泡到软烂,她才能下咽;最让我感不解的是,蚌蚌粉,就是从家门前的池塘里捞出的河蚌,拿碳火烤焦了,然后再捣碎如锅巴粉样,就着温开水调成糊状咽下(后来才听说,那是补钙偏方)。
姑奶生养有几个儿子,我得叫他们表大爷(表叔)。因为姑奶一直和大表大爷住在一起,所以,去姜湾时,在大表大爷家待的时间会多些。对于姜湾的记忆,只是止于村子后面的小山。
今天给父亲打电话时才知道,那山叫狮子山,因为其状如狮子头(我想,那不会是高山,只是平畈上拱起的一处小丘陵而已)。虽然我们两家相隔不远,但两村的生活习性却是有些不同,表大爷家每年都会在狮子山下晒豆折。做法应该是,大米泡湿磨成浆,然后摊成薄饼,再切成面条状,在阳光下曝晒至干爽,可保存好几个月的那种。和现在的河粉相似吧。
每当秋收,狮子山下,各家各户都会晒几簸箕豆折。那时,我会和几个年龄相仿的老表在簸箕之间嬉戏追闹,
肉丝汤煮豆折,是姜湾表大爷一家留给我的最初美味。
二表大爷的命运比较坎坷,由于家里穷,从小落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瘸了。更不幸的是,小时外出讨饭时走丢了,结果被信阳平桥一户人家收养。人到中年,才寻到自己的家,可是口音却全变成平桥腔了。所以,对于二表大爷的记忆是最深的,不是因为他的人,而是因为他的口音。
只是,后来,几个表大爷相继去世,加之我早早离家,外出工作,和姜湾的老表们也就失去了联系。
听父亲说,他们现在也都离开故土,外出发展,混得还算风光。
6/
时间比仇人更残酷,它会无情地带去我们生命中的很多东西,甚至包括我们脆弱的生活本身。
虽然,曾经的亲戚们,就这样,走着就走没了,他们留给我记忆的温馨,却难消散。
你的生命中,肯定也会不少这样的亲戚,他们曾带给你许多温暖与甜蜜,可是,你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想起他们的音容吗?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聚散离合的过程,我碰到了你,你碰到了我,这些都是缘份。不管有没有血脉亲情,我们都是生命中的彼此。
在此,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大家都相互善待吧,因为,无论是亲情还是仇恨,都敌不过时间。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