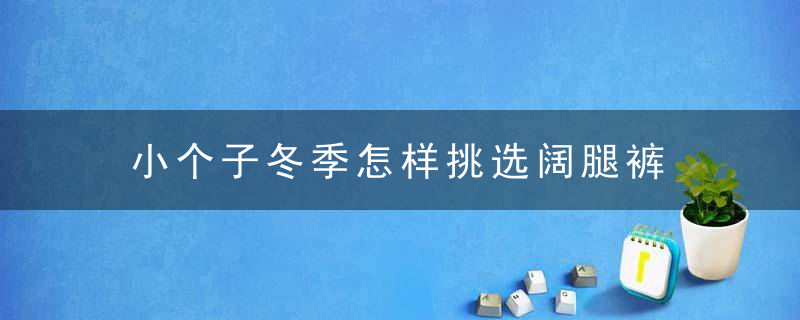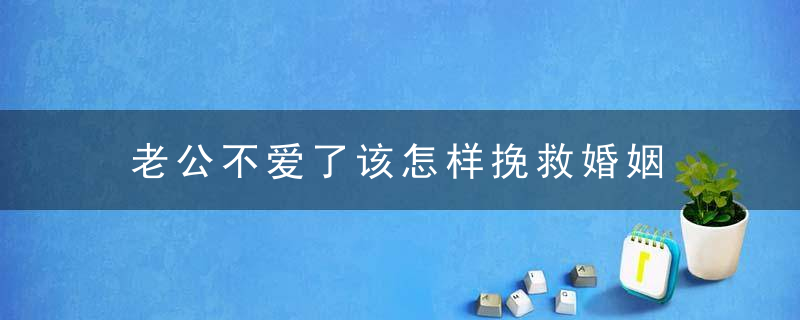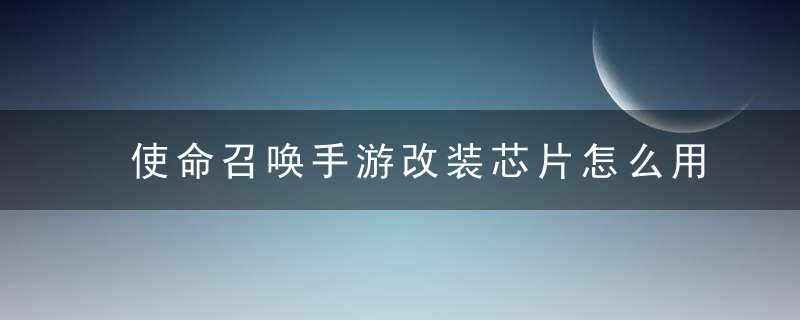组方用药里的奥秘!

大方者,非论多寡,论强大耳。方中味重者为大,味厚者为大,味补者为大,味攻者为大,岂用药之多为大乎。虽大方之中亦有用多者,而终不可谓多者即是大方也。有方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有宣剂、有通剂、补剂、泻剂、轻剂、重剂、滑剂、涩剂、燥剂、湿剂,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或疑大方不多用药,终难称为大方,不知大方之义,在用意之大,不尽在用药之多也。
按:陈氏组方用药的特点,后人评论说他善用大方,而且用量偏大。这源于他对七方、十剂的理解。七方,即大小缓急奇偶复。论十剂,他提出:有方必有剂,剂因方而制也。剂不同……剂各有义,知其义可以用药……陈氏说明了组方的特点,认为,七方是医家用药的方略,不可不讲。但他对七方内容的理解,颇有独到之处。他说如用补法,大意在用参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白术、茯苓之多以为臣使。如用攻,大意在用大黄之多以为君,而不在用厚朴、枳实之多以为臣使。推之寒热表散之药,都遵循这一原则,陈氏之意就在其中。
治病发狂如见鬼之祛狂至神丹方。方用人参一两,白术一两,半夏三钱,天南星三钱,附子一钱,大剂灌之。中风不语者,以人参一两,天南星三钱,生半夏三钱,生附子一个,名为三生饮,急灌之。解释说:方中妙在用人参至一两,始有力量。否则,少用反为痰邪所使,又安能助制附子以直荡群妖哉……三生饮妙在用生人参一两,同生附、半夏、南星祛邪荡涤之药,驾驭而攻之。譬如大将登坛,用虎贲之士,以扫荡群妖,必能活生人于杀人之中。
按:陈氏谓:此皆大方之类。因他对七方做如此理解,所以,七方之中皆有大方。可以看出,陈氏对《内经》七方的理解,不是以通常所理解的数的多少来分,而是根据组方之立意来分,更趋合理。后人多评论陈士铎用药量偏大,是不知陈氏所说的大方之义。今存有清末广陵温热派名医闵纯夫《石室秘录》节改本,作者虑其用药量重,均一一减其分两,已大失陈氏原意。相反,陈氏治病,乃因证设方,大小缓急,各得其宜而已。如《辨证录·凡例》中说:二师传铎之言与鄙人自采之方,分两有太多过重之处,虽因病立方,各合机宜,然而气禀有厚薄之分,生产有南北之异,宜临症加减,不可拘定方中,疑畏而不敢用也。是编方法,亲试者十之五,友朋亲串传诵者十之三,罔不立取奇验,故敢付梓告世。然犹恐药有多寡轻重,方有大小奇偶,又将生平异传诸方,备载于后,便世临病酌用也。
盖奇方者,单方也。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胜。
药味多,未免牵制,反不能单刀直入。凡脏腑之中,止有一经专病者,独取一味而多其分两,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白术一味以利腰脐之湿也,用当归一味以治血虚头晕也,用川芎一味以治头风也,用人参一味以救脱救绝也,用茯苓一味以止泻也,用菟丝子一味以止梦遗也,用杜仲一味以除腰疼也,用山栀子一味以定胁痛也,用甘草一味以解毒也,用大黄一味以攻坚也,用黄连一味以止呕也,用山茱萸一味以益精止肾泄也,用生地一味以止血也,用甘菊花一味以降胃火也,用薏仁一味以治脚气也,用山药一味以益精也,用肉苁蓉一味以通大便……以上皆以一味取胜,扩而充之,又在人意见耳。
按:陈氏不仅善用大方,也擅于用小方。他常用单味药或对药来治病,而且用量也是根据病情可大可小。他对奇方的解释说是用一味以出奇,而不必多味以取胜。药味多,未免牵制,反不能单刀直入。凡脏腑之中,止有一经专病者,独取一味而多其分两,用之直达于所病之处,自能攻坚而奏功如神也。
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二味合而成方者甚多,吾不能悉数,示以成方,不若商以新方也。人参与当归并用,可以治气血之虚。黄芪与白术同施,可以治脾胃之弱。人参与肉桂同投,可以治心肾之寒。人参与黄连合剂,可以治心胃。人参与川芎并下,则头痛顿除。人参与菟丝并煎,则遗精顿止。黄芪与川芎齐服,则气旺而血骤生。黄芪与茯苓相兼,则利水而不走气。黄芪与防风相制,则去风而不助胀。是皆新创之方,实可作偶之证。至于旧方,若参附之偶也,姜附之偶也,桂附之偶,术苓之偶,芪归之偶,归芎之偶,甘芍之偶,何莫非二味之合乎。临症裁用,存乎其人。
按:陈士铎对于偶方,他说:偶方者,重味也,乃二味相合而名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