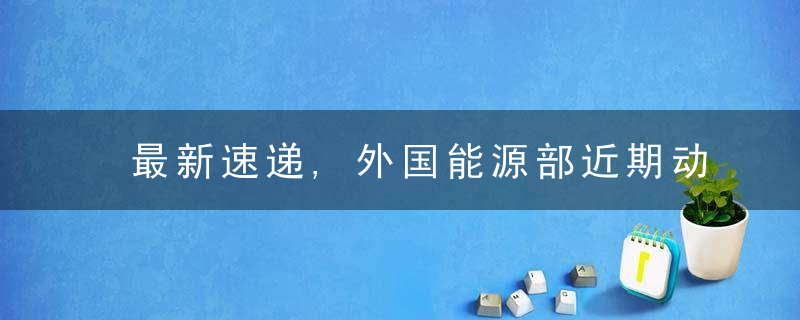疼痛与忧思(一):南渡北归思往事
:南渡北归.jpg)
-- 《南渡北归》关于“文革”的叙述与反思
作者:岳南
南渡北归思往事
2011年初,由中南博集天卷文化公司?湖南文艺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我耗时八年写就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南渡北归》之《南渡》﹑《北归》﹑《离别》三部曲,通篇近170万字。两年来,大陆已销售近四十万套,台湾的繁体字版也销售近十万套,随着读者面不断扩大,作品在两岸三地和国外华人圈引起了巨大反响,2011年《亚洲周刊》评选年度全球华文十大好书(非小说)被推为冠军,周刊说:二零一一年吸引读者眼球的中文好书,首推对复杂的现代史进行精心梳理﹑三大卷同时出版的《南渡北归》。两岸读书界对这套大书予以高度评价,称其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剧烈变迁的史诗巨著”。作者的感叹深沉而悲怆,也令人惊悚不已: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值得注意的是,洋洋洒洒“史诗”的作者岳南并非见证左祸浩劫﹑饱经沧桑的“过来人”,而是生于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新一代文化人。岳南等作家写出这一年的好书,展现出全球华人的软实力及不断“向上的力量”。
读者已经看到,《南渡北归》第一部之《南渡》,叙述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平津、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为保存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全力支持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和学子自平津、华北、华东沦陷区南渡西迁。一大批知识分子从此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流亡生活,先搬到长沙,后播迁昆明、蒙自、叙永、贵州,在敌机无休无止的轰炸中,学人们仍然挺起高傲的脊梁艰难办学、求学。与此同时,研究院各研究所也开始向西南之地流亡,而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济大学等科研教育机构,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最后流亡到川南重镇李庄落下脚来,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八年血与火交织的抗战,山河虽已破碎如风中飘絮,时局日愈艰难,但战时中国的教育和科研并未停歇,反而推向一种奇崛的高度,成为历史的标杆。这个高度和当时国民的战略思想密切相关。抗战开始后,有党国大员提出南迁的大学以办短期培训班为主,但胡适等有识之士竭力主张“战时教育须作平常看”,必须按部就班地把大学教育办下去,且把发展学术、延续文化、推动科学研究当作民族复兴、建国大业的宏伟蓝图来实施。历史向后人昭示的是,在日寇飞机轰炸之下,南渡学人心忧国难,将课堂搬到树林山沟,以延续文化的薪火。“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正是这种紧毅刚卓的信念,将西南联大打造成令后人仰之弥高的高等教育奇迹。而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瘐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为可歌可泣的伟大胜利。凯歌声中,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历史上第四次南渡的后的大回归。此为第二部书名之由来。
遥想当年,跟随丈夫梁思成领导的中国营造学社流亡到四川南溪李庄镇的古建筑学家林徽因在给美国友人费慰梅的信中曾经说过:“我们是在远离故土,在一个因形势所迫而不得不住下来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们曾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长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样。”
抗战胜利后,流亡的知识分子真的又回到了朝思梦想的家国故园。只是,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此时的社会已不是原来的社会,等待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的,不是欢欣与笑脸,而是内战阴云的笼罩与血肉横飞的战场硝烟。一个关于中国命运的大战业已开始,这批自由知识分子也在这个翻云覆雨的世纪大变局中,开始了新的一轮凶险莫测的人生之旅,其结果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大师,携家带口,同时带着他们的个人理想和主义,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傅斯年语)。而陈寅恪、叶企孙、饶毓泰、曾昭抡、吴宓等一批大师,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自杀,如向达、汪篯、俞大姻、陈梦家、傅乐焕、穆旦等等。也有一部分在“文革”中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如冯友兰、周一良等,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欲哭无泪、扼腕浩叹——这就是《北归》之后的第三部《离别》的大致脉络。
知识分子群体的哀歌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并不是我的发明和哗众取宠,实则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殷鉴不远,在夏之后,历史是一面镜子,书中的人物故事和大师们令人扼腕的人生遭际,打开了一扇被蓄意掩蔽的历史之门,向这个纷乱繁杂的世界再度唱出了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挽歌,刺耳的回声对后世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
与许多读者交流中,我发现大家为这部书感动和哀伤的并不是抗战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如何艰苦,如何在贫病交加中继续学术研究事业,恰恰是这批杰出的知识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中的一连串政治际遇,令人扼腕太息,并为失去的大师和这个民族在文化、学术上的衰微而深情一哭。
如上面提到的陈寅恪,通晓十几种外国文字,且有几种是已死掉的文字,年仅37岁就成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被学术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大师中的大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1957年“反右”之后的第二年就被学校当局点名批判,从些厄运连连,“文革”中更是惨遭荼毒。时陈寅恪已是膑足失明,造反派把其当作“牛鬼蛇神”从床上拖下来,强迫下跪背诵语录,倘若不能背诵或有一句背错,便遭一顿辱骂和铜头皮带抽打与棍棒敲头的惩罚。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出康乐园楼房进入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都已困难,偶有亲友躲开造反派的监视偷偷前来探视一下,躺在病榻上的陈寅恪说不出话,只是眼角有浑浊的泪水流出。1969年5月5日,陈寅恪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待”,陈氏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之语,终至泪尽泣血,造反派又弄来几个高音喇叭绑在陈氏的床头对其进行喊话批斗。双目失明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当即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对此作过沉痛的回忆:“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到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元亮虚留命,灵均久失魂。人生终有死,遗恨塞乾坤。”此为陈寅恪死前留给这个世界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这个扭曲的社会和人心发出的怒吼。
1958年陈寅恪被批判后,他有一个任教北大、名叫汪篯的弟子也受到牵连遭到了来自同一战壕号称“革命战友”的批判与围殴。“文革”爆发后,因为贴在家门的一张大字报与造反派发生争执,继之受到羞辱。当天夜里,独居一室的汪氏打开家中备藏的杀虫剂“敌敌畏”喝了下去。未久,“敌敌畏”药性发作,在家中号叫并且以头撞击墙壁。邻居于慌恐中前来施救,当众人把门撞开时,发现他早已气绝身亡。……这一天是1966年6月11日,汪篯50岁,此为北京大学第一个在“文革”中自杀的教授。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任导师的时候有一个弟子叫刘盼遂,学问很好,号称书痴,“文革”爆发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住在西单一个不大的独院。红卫后抄家时,刘氏亲眼目睹自己耗尽大半生心血收藏的数万册古籍焚于院中,在跪地恳求红卫兵灭火并把残余送图书馆收藏无效后,满含悲愤的热泪扑向火海,欲与典籍同归于尽,红卫兵见状,将刘氏拉出,一顿拳脚加棍棒打得唵唵一息,拖到一个水缸前,头上脚下强压进水缸,窒息而死。刘夫人当天外出买菜回来,看到丈夫在火中“涅槃”,悲愤交集,欲与红卫兵理论,结果被红卫兵打翻在地,抬起来头下脚上与刘盼遂按到了同一个水缸窒息而死。令人吃惊的是,参与殴打并将刘氏夫妇倒栽葱式强行插入水缸的竟有小学生,而刘氏的儿子开始见父母有生命危险,便跑到北师大学校当局请求解围,却无一人出面表示同情和前往制止红卫兵的暴行。
1966年6月18日,北大校园内发生了著名的“六一八”事件。只见红卫兵疯狂地冲到中文系办公室抓捕党支部书记程贤策,程闻风而逃,慌忙中竟冲进了女厕所。正在如厕的一位女职员先惊后醒,提着裤腰带冲到门口企图阻止,最后程贤策还是被红卫兵从厕所揪出来反扭胳膊,送到一间小黑屋“化装打扮”后押上“斗鬼台”批斗,直斗到面如死灰昏倒台下。这一天,与程贤策一起揍斗的北大教授有60多人,许多人在批斗中遭到了毒打。第二天,程贤策一手拿着一瓶烈酒,一手拿着一瓶“敌敌畏”毒药出了北大校门一直西去。下午,有人在香山一棵树下发现了程的尸体,程双手搂住小树底部,满脸透着死前的痛苦,身边不远处倒放着一个“敌敌畏”毒药瓶。
原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是赵萝蕤,另有俞大絪、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三位教师,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部进入北大西语系任教授。1957年,胡稼贻与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分子”,俞大絪、赵萝蕤两位女教授的丈夫曾昭抡、陈梦家被划为“右派分子”。 “文革”开始后,吴兴华被划入“劳改队”并遭到红卫兵殴打和抄家。1966年8月3日,在校内烈日下“劳改”时,口渴难耐,遂向监工的红卫兵讨水喝。几个监工为惩罚他的要求,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对待,当天夜里吴兴华被妻子拉回家不久即断了气。红卫兵坚持说他是以自杀对抗“文革”,要打成“现行反革命”,且不顾吴妻反对,把尸体拉到医院破腹验尸,证明死于急性病毒性痢疾。剖开的尸体尚未缝合,又被强制拉到火化厂火化。吴兴华生于1921年,死时年仅45岁。吴的遗孀和两个小女儿被扫地出门,只得到海淀镇上觅得一间民房栖身度日。
吴兴华罹难三个星期后的1966年8月24日夜,俞大絪白天挨斗后于旁晚被放回家独自躺在床上呻吟,未久,另一伙红卫兵又冲进房来揪着俞的头发拖于床下,继之将头往墙上乱撞,让其交待罪行。俞氏据理力争,红卫兵索性把这位年过关百的女教授按倒在地,披光上身,用铜头皮带抽打,直打得俞大絪满地乱滚,哀号不绝,昏死过去,红卫兵才将其家中东西查抄,装上卡车拉走。当晚,从昏死中醒来的俞大絪再也无法忍受如此的污辱,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此为北京大学自杀的第一位女教授。
俞大絪的丈夫曾昭抡乃曾国藩重孙、著名化学家,曾任北大教务长、高教部副部长等要职,1957年因“六教授事件”被打成右派并遭革职,翌年转入武汉大学化学系“政治上改造,工作上使用”。夫人俞大絪的死讯传到武汉,已患癌症的曾昭抡当场昏倒。“文革”开始后,曾昭抡受到学校造反派批斗与数次皮带抽打,1967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而死后的曾昭抡无人收尸,学校当局任其在单身宿舍床上变质腐烂。多亏曾氏一侄子从外地赶来探望叔父,看到如此悲惨一幕,从校外找了一辆平板车,含泪将曾昭抡的尸体运到火葬场火化,尔后将骨灰抛于长江。
在曾昭抡死前的1964年12月22日,他的妹妹、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女考古学家、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因不堪政治重压于南京郊外灵谷塔一跃而下,结束了年仅55岁的生命。
当然,抗战中流亡西南,胜利后回归故园,“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高校教授绝不是这几个,大家所知的吴晗因一出《海瑞罢官》的京剧成为十年“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人,吴晗死的时候,头发被批斗者拔光了,牙齿打掉了,屎拉在裤子里死一间小黑屋。而他的妻子袁震早于半年前被折磨批斗致死,他的女儿小彦在被捕入狱后跳楼自杀。
与吴晗并称为一代才子的诗人、古文字与青铜器专家陈梦家,由清华大学调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被打成右派,“文革”爆发,因不堪造反派的批斗与污辱,决心“不能再让人当猴耍了!”,于1966年8月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又于9月3日在仅供容身的一间小黑屋里自缢身亡。这一年,陈梦家55岁。
就在陈梦家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再度抄了陈氏的家,并在院内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同时把赵的头发剃去半边,成为所谓的“阴阳头”后,又被造反派拉往北京大学校园,遭到更加酷烈的批斗和殴打,而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最威猛凶狠,反复掌赵氏耳光的一人,竟是赵萝蕤亲自教过并让其留校做助教的年轻女性。经过这一场身心折磨和人格污辱,赵的心灵受到重大打击,精神分裂症加剧。
与陈梦家并列为“四大右派”之一的北大教授向达,“文革”中被造反派押往昌平太平庄劳动,晚上寝室门被从外锁死,夜间如厕一概不准。向达患严重肾病,全身浮肿,尿液不能排出,痛得满地打滚儿。但监工的红卫兵仍不准送医院救治,只押回校内“劳改”,1966年11月24日,一代史学巨匠向达在极度的痛苦中被尿憋死,终年66岁。
此时的北京大学被关押和劳改的“反动学术权威”达五百多人。每天晚上,北大校园内十几个审讯室同时挑灯夜战,开始“审讯工作”。除原有的工作组,陆续进驻北大的造反派们组成一个个联合审讯班子,将提审对象拉进审讯室先是一顿耳光加拳脚伺候,而后开始审问,此为“敬酒”。几句话之后,开始动刑,主要刑具是用橡皮包着的二尺左右拇指般粗细的铜棍,据说这种东西远比皮鞭打下去扎实,伤其筋骨而又不伤皮肤。打的时候,常常是剥光衣服,不论男女,此为“罚酒”。如此反复折磨、蹂躏,许多“反动学术权威”决定以自杀的方式早日解脱,这种想法像传染病一样在燕园流行开来,跳楼和上吊者成倍地增多,有几幢教学楼成为鬼气迷蒙的人间地狱,在校的女学生晚上都不敢靠近。几个月内,就有24位著名教授自杀,而自杀的方式各不相同,据北大教授季羡林晚年回忆说:“他们有的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粉身碎骨而死;有的到铁道上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当时两位教授投未名湖自尽。湖水是并不深的。他们是怎样淹死的呢?现在想来,莫非是他们志在必死,在水深只达到腰部的水中,把自己的头硬埋入水里生生地憋死的吗?差不多同时,一位哲学系姓方的教授用刮胡刀切断了自己的动脉,血流如注,无论怎样抢救也无济于事,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痛苦地死去。”
据研究者统计,当年知识分子自杀的方式,除了上吊、服毒、割腕等自残手段外,跳湖、跳河成为一大颇具时髦的特色,其惨烈之状尤以风暴中心北京大学为甚。1968年8月,北大图书馆系讲师、党员许世华在北大附近的西苑投水自杀;10月16日晚,北京大学教务长崔雄昆从校内28楼出走,次日晨,被发现死在校内红湖游泳池内。校工宣队对外公布说:“经法医检查,是投水炸肺自杀。”
1966年10月,早就由二级教授降为六级的胡稼贻,在校园“劳改”时突然瘫痪。妻子把他送到北医三院,医院索要北大的公函才予治病。系中给医院的公函上写的是:“该人是我系右派分子,请给予一般治疗。”医院见函深知肚明,给了几个药片便打发走人,胡氏病情越来越重,在1968年1月撒手人寰。
这段疯狂岁月所酝成的人性丧失和人类悲剧,正如邓小平女儿毛毛所作的描述:“北京大学,这所中国最著名的学府,竟然变成了法西斯的集中营,变成了血腥暴徒们施虐的场所。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人被冤、被屈、被整、被迫害,不知有多少人在武斗、批斗、刑讯中致残、致死。一位教师不堪受侮辱被虐待,自觉生不如死,竟然一次不成二次,二次不成三次,三次不成四次,跳楼、服药、割腕、卧轨、触电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反复自杀。一位反对聂元梓的学生,被用钉子钉穿膝盖骨、用竹签刺进十指指甲缝、用钳子钳断手的指骨,还把人装进麻袋中从楼梯上往下踢,被毒刑拷打得奄奄一息。原北大校、校长陆平被用钢丝缠捆着两只手的大拇指,吊在天花板上逼供刑讯,让其承认是‘假党员’、‘叛徒’。著名哲学家冯定也被逼得三次自杀。以上这些,仅是例举。‘文革’期间,在北大,武斗中打死三人,教职员工和学生被迫害致死六十余人,其中包括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等诸多享有盛誉的一级教授。”
毛毛所说的饶毓泰,就是与叶企孙并称“双雄”,或“双子星座”的中国物理学奠基人、开山老祖、恐龙级学术权威饶树人,他于1968年10月16日在北大燕南园41号家中自缢身亡。而与其并列的叶企孙自1949年始成为清华大学的一把手,后被降职调往北大任物理教师。1968年因他的学生熊大缜参与C.C.特务的离奇冤案被捕入狱,1969年年底,在专案组审查无果的情况下,叶企孙被放出监狱,由北大红卫兵组织对其实行“隔离审查”。叶企孙出了监狱又步入地狱,从此落入红卫兵手中,经受更严酷的煎熬。经过一阵乱拳加乱棍的摔打锤炼,叶企孙病情再度加重,前列腺肥大,小便失禁,两腿肿胀难以站立。偶尔走动,腰弯成九十度,似一根弯曲的枯木在风雨中摇晃。再后来,叶的神经彻底崩溃,成了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
此时,叶企孙每月只能领50元工资,吃饭穿衣皆不能足,生活凄惨。当看管的红卫兵稍微放松一点,叶本能地溜出来在中关村一带的小摊上讨吃讨喝儿,嘴里不住地咕囔着别人很难听懂的话语。当时中科院有几个研究所已迁往北大校园所在的中关村一带,不少与叶熟悉的朋友见到了下列一幕惨不忍睹的情景:叶企孙头发花白,弓着背,整个身子呈九十度直角状,穿着一双破棉鞋,踯躅街头,间或踽踽前行。有时来到一家店铺小摊,或买或向摊主伸手索要一二个明显带有虫咬疤痕的小苹果,过走边津津津有味地啃着,碰到教授模样或学生打扮的人,便伸出一只枯干的手,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一二角而已!望者无不为之潸然。延至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凄惨地离开了人世。1999年9月18日,、、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共有23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勋章”。分别是:
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钱三强、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郭永怀。
其中叶企孙在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主政和任教期间培养的学生如下:
王淦昌,1929届。
赵九章,1933届。
彭桓武,1935届。
钱三强、王大珩,1936届。
陈芳允,1938届。
屠守锷,1940届清华航空系。
邓稼先、朱光亚,1945届。
叶企孙学生之学生:
周光召、程开甲;钱骥;于敏。
另有两位院士级著名物理学家:
张宗燧,1934届、胡宁1938届。
blog.sina/s/blog_4e3308af0102eamk.html